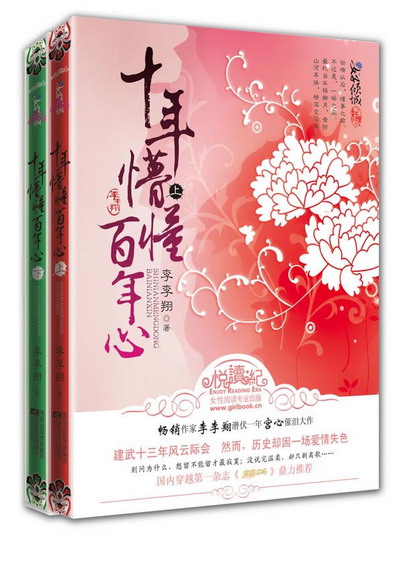十年之爱恨纠缠-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季然,季然……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眼前舞动的大掌晃来晃去,企图引起我的注意,结果它也真引起了我的注意,脑开始工作,正常工作。
刚刚白茫茫的一片随着大脑的正常运转开始慢慢消散,周遭一切开始正常,我看见了晃动并不是我以为那样厉害的大手,我看见一脸平静等着我答案的杨振晨,我甚至能清楚看见他身后的墙纸花样。
他生气了吗?不,他应该很平静才是,生气的人不是应该眼冒火花吗?他没有!他是清醒的吧?不,他应该也和我一样突然失去了意识,不然他应该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知道他说出口的话代表什么。
“你要结婚了!”我找回声音,低低吐出五个字——让我受伤很重的五个字。
有时候还真希望我能自动屏蔽或忘记一些事情,比如他要结婚的事,比如他恨我的事,在比如我们曾经的所有。看了多年小说,主人公只要出车祸,泰半是要失去记忆的,失去记忆后,他(她)会很痛苦,因为没有过去,因为一片空白。每每看到这样的桥段,我总在想,失去记忆需要如此痛苦吗?就算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人多半也是不太记得小时候,特别是三岁以前的事情,少了三年的记忆也没见大家怎样痛哭流涕,怎么撕心裂肺啊,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当然只限于有时候,如若真让我失去了过往,我还真拿不准自己会是高兴还是痛苦,因为没有发现,因为不切实际,想想也就过去了。
想的事情可以过去,可我此时面前的这道坎好像很难逾越。
两人对望,我在他的眼里看见自己的影子。
“那和你成为我的人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难道他不知道,若我答应了,他的行为叫婚外情,我的位子是第三者。难道他没看过《回家的诱惑》?不知道当第三者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吗?难道他忘记了他最痛恨的就是第三者吗?不,也许他没有忘记,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我当初的借口当成报复我的手段。他的怨恨我想偿还,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如果还债是建立在伤害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基础上,我不要,特别是另一人还是我认识的人,还是对我很好的女子。
“我不能伤害吴经理。”吴元元一直叫我季姐姐,我不应该背后捅她一刀,一个女人的幸福依靠就是家庭,我不能。若是真当了她婚姻的第三者,偿还了欠杨振晨的债,同时又欠下她的债。我这辈子也就掉了进一个恶性循环,没完没了,地狱之门离我也就不远了。
“都说了不关她的事,你不用拿她当挡箭牌。我还是那句话,同意,时间一到我们就两清,谁也不欠谁;还有我想孙未应该很有兴趣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吧!”他的表情一派轻松,好像在说“今天天气真不错。”
“你!你调查我!”他是怎么知道孙未的?我不会天真的以为一场商业晚宴就能让他说出上面的话,在商言商,他每天需要面对的客户与合作伙伴何其多,不会简单因为我为孙未挡酒就调查我们,若是调查了应该也就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可听他的话明显不知道。自从上次碰面后,我和孙未就时常联系,他需要安心,我需要他为我保守秘密。
“哼,需要调查?你打电话说情话可很是大方。”他抱着双臂,睨视我。
是了,有几回孙未来电话刚好碰上他在场,我也没太忌讳,直接接了。孙未说过,若是他的电话响过三声我没有接,他可以不遵守承诺。我们之间的承诺很简单,若是我违反他开出的条件,就必须随时终止和杨振晨的牵扯,乖乖回家。那时,我还不能回家,我还想偿还对杨的亏欠,我更不能让他和杨有接触,于是每每电话来了,也只好认分。从前因他的事情和家里闹得沸沸扬扬,不欢而散,多年后再相遇,我没说,遇到孙未后就更不可能让杨出现在我的家人面前。两边都是我想爱的人,两边又是见面次数有限的仇人,也许说仇人有些过分,但在我爸妈心中,杨应该就是仇人,只因他抢走了他们最宠爱的女儿。终于明白丈夫面对媳妇和亲妈时为什么会如此为难了。
心痛到不知痛原来是这样的感觉。我轻轻点头,比起让他骚扰我的家人,伤害我的亲人,我选择了伤害吴元元。也许我可以将对她的伤害降到最低,也许我可以在她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安然离开,办法都是人想的,我需要时间。
“我同意,但时间不能一年,我只有半年,可以吧?”这是我最低的要求,也是最后的要求。我承诺过孙未,一年后我会回家,会给挚爱之人一个交代。离约定之日算来最多只有半年了,不能再多,我也怕时间长了自己会离不开。承诺这个东西真不是可以随便说的。
他好像在思考。我等着,咬着唇。突然眼前一黑,俊颜无限放大,唇上冰冰冷冷,我被吻了。他没有深入,只是静静停在我的唇上,不动不语。好久好久以后,他放开了我。
“这是签字盖章,不准反悔。”
我苦笑,现实太残酷,你们根本没有给过我反悔的机会。
☆、第五十七章权利最终是拿来失去的
刘文婚礼温馨美好,人不多,每一个人都是至亲,能在至亲的祝福和见证中走近婚姻的殿堂,也是一种人生幸事。我也曾想过举办这样的婚礼,只是一切都没了可能。没有约定前,是我不想结,觉得不是心中那个人,结了也没意义,与其没有基础的生活在一起,不如省了麻烦。现在是结不了了,谁想和一个做过别人情妇的人结婚?杨振晨你比我更狠,你在我后半生的路上直接扔下一块巨石,阻断了后面的路。
人就是奇怪的动物,已经做好了不结婚的打算,已经自动切断了自己的后路,可当别人说出同样意思的话的时候,人就会觉得不舒服,觉得是对自己的侮辱。也许是因为人都有种怪逻辑,宁肯自我了断,也不命丧他人,额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论。原来我也是自我中心严重之人。
流年不利,也只有这四个字能形容我目前的现状。刘文被她的新婚丈夫打包寄去巴厘岛度蜜月,结婚第二天一大早就飞走了,在她的挣扎与纠结中。杨振晨给了我惊吓,但他还算绅士,送我回了家。回家才发现汪敏没在。不是我大惊小怪,实在是时间太晚,婚礼早就结束了,她能去哪儿?打了电话,没人接,给刘妈妈打电话,说她早就回来了。
我急了。因为无端旷工一个月,医院的工作她辞了。现在让我找人还真想不出可以问谁。脑中只有一个声音:“没事,敏子出去走走,明天就回来了。”忐忑不安到半夜,收到一封短信“然,我想出去转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不用担心,我很好。”是汪敏。我立马拨回去,手机关机。她真心想静静。
手机打不通,我只能改发短信,希望她什么时候开机能瞧着。短信没有歇斯底里,更没有胡思乱想,只是简简单单问了一句:“还回来吗?”我担心,真担心她从此人间消失。
是我不好,她回来后一直精神恍惚,也没有了以前的活泛性子,做得最多的就是发呆。我曾问过她在想什么,她只是笑笑说:“没什么。”那段时间我也正为感情之事困扰,对她的关心自是少了。若是我能早一点找她谈谈,也不至于像此时一样,不知她在哪里。自责只能暂时放进心里,人都走了,我能做得只是默默期盼她还会回来。
她说没事,我不信,最后一次见她是杨振晨带我离开经过大厅时,我瞄了一眼,她笑得很开心,喝酒很豪迈,来者不拒。我当时心神都被杨振晨的话锁住了,只是寥寥一眼,忽略了她的异常。她能喝,但从不见她如此豪饮,即使是毕业聚餐也不曾。敏子心事重,我们三人都不是藏得住心事的人,特别是在面对对方的时候,不过相较起来,敏子是比较深层之人。也是这会儿,我才深刻体会到,在S市快十年了,我们依旧只是一个漂泊者,表面枝枝蔓蔓好不繁盛,内心却是竹子,没心没根。好累。
后来她陆陆续续会传一些信息,陌生的号码,陌生的地址,只字片语,让我们知道她很好。定期能收到她的信息,我也放下心来,没在纠结她在哪里?也没有非要问出一个答案。她是我们三个中最早独立的女子,照顾自己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担心。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自身难保,已经没有多余的心里来顾及其他。心中有愧,只能埋在心中。
经历了婚礼上的惊心动魄,我安稳了两天。杨振晨没有来找过我,就连电话也没有一个,我也提心吊胆了两天。我一直当婚礼上那一幕是他我气昏了神智,做出的不理智行为,经过两天的冷静,他该是后悔了。现在想来我都觉得那不是他。
我的想法永远都只停留在我的想法上,世上的事情依旧在运转,他来了。汪敏的事情加上两天的提心吊胆,我的睡眠质量变很差,一点风吹草动,立马惊醒,醒后就再也不能入睡,许多事情在脑海里绕圈绕圈再绕圈。好命的我也第一次体会了什么叫智者多虑,虑者少眠。
“你……你来了。”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出颓废,更不想他看见我顶着爆炸头,穿着睡衣,踩着拖鞋的邋遢样。只是他打突击的技术实在了得,我已完全来不及改变,于是口齿开始不清,眼睛开始乱飘,身体开始不听使唤。
他睨视我好久,久到我脚上的拖鞋夹带都快被我夹断了。他指指我的头发,径直扰过我进了门。我这才注意到他手里提着的物件。他将手中的袋子放在厨房的长桌上,取出里面的几个盒子,一一摆开,接了盖子,放好筷子,才回头对正在发愣的我说:“过来吃饭。”
对于楞到外太空的我来说,遇到外星人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事吧?
“怎么,不饿?”他挑眉。
原来外星人也有眉毛,也能想地球人一样活动自如,新发现,重大发现,我家有一个外星人,和杨振晨长的一模一样的外星人。
“你……你是谁?”我很镇定,眼前的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振晨,他对我的怨很深,深到都让小说里男主虐女主的手段都使出来,哪会这么好心,一大清早送便当?现在的S市,我除了杨振晨,谁也不怕,即使是传说中的外星人,也许我真该遇到外星人,请求它们将我带走,这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次他的眉没挑,换成了眉头紧皱成川。“有本事你再问一次。”
威胁,赤裸裸的威胁,他不是杨振晨。真正的杨振晨从来不使用威胁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有什么他都直接来,专制独裁。就连胁迫我签所谓的“情妇协议”也是笑着说的,虽然内容怎么听都是威胁,可表情很容易让人跳戏。哦,对了,我们并没有签署所谓的“情妇协议”,口说无凭,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吻,我应该是能赖账的吧?
赖账是一回事,肚子饿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理需求,还是那句老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乖乖坐到长桌另一头,端起一次性饭盒埋头吃起来。
他也跟着坐下,翘着二郎腿,抱着双臂,悠闲瞧着我吃饭:“头抬起来些,菜汁儿都沾到头发上了。”
我稍稍抬了点头,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是杨振晨,是大学时代那个杨振晨。那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