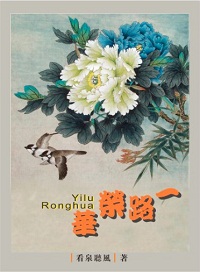一路走来一路读-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只能以其昏昏,使人也昏昏。因为,他们常常只是比学生早读了几年这些含混的教材,他们的面前也只有那几张不知所云的照片,也根本无缘见过真实的“高迪”。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已被彻底改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注重精美插图的图书或杂志编辑,我们甚至可以在巴塞罗那的街头,邂逅那些年轻的来自遥远东方的建筑教师。他们神气地提着炮筒子一般的照相机,利落地像剥花生米一样地剥着幻灯片的胶卷,犀利的眼光透出专业。这不仅是他们的幸运,更是今天的中国学生们的幸运了。
高迪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成熟在世纪之交,只是比我们整整早了100年。1852年6月25日,他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只有23;000人口的叫做Reus的城市。6岁之前,他一直是个病病歪歪的孩子,被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幸好,在慢慢长大起来的时候,他也渐渐好起来,虽然他一生都没有彻底痊愈,都时不时地被病痛所困扰。人们说,小时候体弱的孩子比较敏感,人们也说,西班牙如画的景致孕育了一个艺术家。可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可能都是在高迪已经成为高迪以后,人们随意添加的注解。
我们只知道,他小时候是个普通的孩子,惟一表现出艺术倾向的,是他在一份和小朋友一起办的杂志上,负责画插图。高迪一家后来搬到巴塞罗那,他在那里读建筑,读得非常刻苦。在此期间,家里的重要经济支柱被折断——他当医生的哥哥去世了。家里5个兄弟姐妹,只活下了他和婚姻失败的姐姐。父亲老了。他必须刻苦。高迪读着书,体验着建筑的语言,甚至没有女友。相对他给后人留下的那些建筑作品,他自己本人似乎并不留给人们多少幻想的空间。
在我们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是高度兴奋、妙语连珠的,本身就是一个散发着巨大热量的感染源。他们有能力即刻地就使周围的人被调动起来。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显得沉稳,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木讷和走神。可是,他们将热情倾注在他们的创造物之中。你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个作品,一个不能言语的物件,感受他们心中的汹涌波澜,甚至天真烂漫。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至于高迪,不是一个极端,可他大概是接近于后一类人的。
高迪不是一个超人。从他走过的路径,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常规痕迹。他们都是先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做专业化的、但是并不突出的早期作业。然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平庸者的区别,是在某一天,或是某一刻,他突然能够把自己的灵魂揉入自己的作品。这个作品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是灰暗的沉闷的,但是某种光亮,会在深不可测的地方突然闪现。打动那些能够感应的人们。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悟”。它可能来得早,也可能在很晚才出现,可是,没有它,一定不能算是艺术家。
而高迪开始发出光亮,不仅是在深处,他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亮丽的、精彩的、焕发着宗教热情的。高迪是一个充满宗教感情的人,这种宗教性是西班牙式的。西班牙是一块浸透了宗教的土壤。但是,西班牙人的宗教感情不走向抑郁的成熟,而是怀着热烈的献身的强烈向往。
第二部分 走路(二)寻访高迪(2)
巴塞罗那是高迪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有着高迪的主要作品。专家们分析他的作品是东方式的,但凭我的愚钝,很难看出这些理论的深层妙处,我只感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他设计的公寓们,不论放到哪一个都市的大街上,也许都会有突兀和破坏城市整体感的风险,可是,放在巴塞罗那,就是恰到好处。公寓,那是多么令建筑师们沮丧的枯燥题材,可是高迪却把它们处理得神采飞扬。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高迪的建筑是雕塑性的。可是,在外形非常大气的整体雕塑感后面,还隐藏着高迪对庭院和建筑内部的精心处理。这在他的米拉公寓中(Casa Mila,1906-1912)表现得很充分。他耐心地在这个交给他的空间里,一点也不肯马虎地,里里外外做着他迷恋的事情,把一团团泥土,捏成一个个精巧的作品。又用一串串铁花,舒服地把它们搭配连接在一起,一层又一层地盖上去。人们看高迪,不仅从外面看到里面,从下面看到上面,甚至要一直钻出顶层,看到屋顶。那里,本应该是烟囱是通风口的地方,竞有一片扭动着的精灵的塑像,精致却又粗犷,仿佛有白云飘过,它们就会吟唱,在乌云下面,它们就会嘶喊。
在欧洲,那也是一个早期印象派和新艺术运动的时代。高迪和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是一个独立的探索者。但是新艺术运动在室内设计上的效果,几乎是高迪建筑的最佳配合。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迸发的光彩,流动的曲线连着梦幻的走向。在那个时候,艺术家用的还是相当传统的手段,可是,他们的开放的精神,却使他们的能力挣脱和超越了他们手中能够掌握的材料。
高迪也做园林。他做的盖尔公园(Parc Guell,1900-1904)也在巴塞罗那。那是用马赛克镶嵌成的一个幻想世界。从那个门口的小教堂,你似乎可以感受到高迪的巨手,在轻重恰如其分地捏塑着墙面。然后,在几乎是带着指纹痕迹的曲线里,高迪顽童般地,用他对色彩的特殊感觉,一小块一小块地,向柔性的泥里,摁进那些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马赛克。登上公园的大平台,人们决不会转一圈就舍得下去,平台的边缘,是游动着的马赛克座椅,舒展着作为建筑作品的力度和气势,而每一段细细看去,又都是一幅小小的印象派美术作品。从那里向下看去,你会看到公园“趴”着那只著名的彩色大蜥蜴的台阶,通向教堂,通向出口,通向外面的世界,这个时候你会问自己,人长大了为什么就不可以依然天真?
巴塞罗那最叫人服气的,是正在建造中的“萨格拉达家族教堂”(Expiatory Temple of the Sagrada Familia)。它始建于19世纪末,而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的时候,已经是21世纪之初了。是的,没有算错,它已经建造了100多年。然而,它还正在被建造之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创了现代建筑的记录。但是,这确实是现代社会罕见的对艺术的坚韧追求。在这100多年里,许多著名的西班牙艺术家怀着对宗教和艺术的双重热忱,投入了它的设计和制作。大家也都承认,对它倾注了十几年心血,把自己最后的岁月完全交给它的高迪,使这个教堂获得了灵魂。
望着大教堂的照片,我又回想起在巴塞罗那的日子,想起在一个又一个教堂中的流连和静默,想起在巴塞罗那有过的心情。西班牙并不是哥特式教堂的发源地,它的发源地是法国。正因为如此,当这里开始修建哥特教堂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建筑形式的成熟期了,它们不论大小,都近乎完美,都非常适合呼唤一颗敏感的心。今天回想巴塞罗那,我都有一种近乎是尖利的痛苦感觉: 在那些日子里,曾经有过的纯净和朴素,竞如此轻易地就被自己完全丢失了。现在,是我最应该闭上眼睛,重新感受巴塞罗那教堂中一片烛火中的气味,遥望那消失在夜空中的高迪的教堂尖顶的时候。
高迪不是一个在生前就倍受赞誉的人。人们并不理解这样一种奇异的思路。可是高迪已经不再环顾四周。在建造“萨格拉达家族教堂”的时候,已是高迪的晚年。他完全沉浸在宗教精神之中。这个教堂对于他,首先是一个宗教圣殿,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品,更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物。在这时,他已经有足够的智慧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一个仰慕他的年轻的德国建筑系的学生,向人们打听,怎样才能见到老年的高迪。人们指着巴塞罗那主教堂对他说,每天清晨5点,当这里响起弥撒的钟声,你一定可以看到高迪。果然,在那个时候,在主教堂第一排的凳子前,他找到了跪在上帝面前的高迪。高迪不再寻找什么,他只寻找上帝的指引。没有人知道他那颗跳动的心在感受什么。人们只看见那高迪在全力营建的大教堂,那“基督诞生”正立面的钟楼,在一年又一年地缓缓升起。
它们是浑厚的,有着千年的宗教根基;它们又是现代的,有着最奇特的造型,顶尖缀着高迪式的马赛克,色彩斑斓,在阳光和月光之下,一闪一亮。它们升起来,在晨曦中,像是尚未苏醒的生长着的巨木,也像是上帝指引下的高迪那难解的心灵。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同的位置和能力,高迪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却不是一个有能力和这个世界纠缠的人。他只能希望这个世界忘记他,留给他创作和思考的清静。多少年后,人们打开一篇论述高迪的文章,前面以这样一句引言,使人们想起了当时真实的高迪,那句话是:
“请远离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
第二部分 走路(二)斯密森的神秘礼物
每个大国都有自己顶尖的博物馆。到法国,不可不去罗浮宫;到英国,不可不去大英博物馆;到俄国,不可不去冬宫。到我们中国来的老外,没有一个不去故宫博物院。这些博物馆,无一例外地是当年的王室遗产,那里面是几百年上千年的精华积淀,不是光花钱就能建得起来的。就像法国人说的,“世界上有哪个拍卖行,胆敢给《蒙娜·丽莎》估价的”?美国只有200年历史,没有王室遗产这一说,在艺术收藏上就先短一口气。可是,你要是跟美国人这么说,他们在点头承认的同时,或许会悠悠地回你一句:“不过,我们有斯密松宁,他们有吗?”
斯密松宁就在首都华盛顿。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是著名的国家广场,广场的南北两边,有一栋一栋壮观的大厦,北边是美国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南边有佛利尔美术馆、沙可乐美术馆、非洲艺术博物馆、艺术工业大厦、赫尚博物馆、雕塑园、国家航空宇航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和位于别的地方的威尔逊国际中心、国家动物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以及在纽约的库伯惠特博物馆,等等,就组成所谓斯密松宁学会。而华盛顿市国家广场两侧的这些博物馆,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体系。
在国家广场北侧,有一栋欧洲中世纪复兴风格的大楼,有着高高的塔楼。和附近的宇航博物馆相比,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古典的风格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斯密松宁大厦。从南大门进去,在进入正厅以前,有一段不长的走廊。走廊左侧是一个大理石的房间,正中的高台上,放着一个花坛形状的大理石棺。洋洋大观的美国斯密松宁学会就是从这个石棺开始的。
200多年前,大致在美国刚建国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叫詹姆斯·斯密森(James Smithson)。他的生父是诺森伯兰公爵,母亲有皇室血统,可以说他身上流着英国最高贵的血。可惜,他是一个私生子。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俗,他不能继承父亲的名位,而且一辈子受到歧视。他天赋极好,聪明过人,而且由于受歧视而极其用功。21岁自牛津大学毕业,一年后就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科学上卓有成就,有一种锌矿就以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