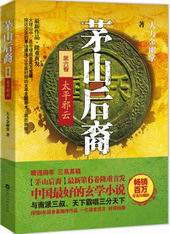太平广记-第2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穿好衣服,恭恭敬敬施礼,拜他为师。宣律刻苦修练,常常在夜深时修行,站到台阶前往下摔落。他正往下摔落的时候,忽然感到有人接住了他的双脚。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少年,宣律急忙问他是什么人,为何深夜到此,少年说:“我不是平常人,而是毗沙门天王的儿子那吒太子。为了保护佛法,特来拥护和尚您,已经来了好长时间了。”宣律说:“贫道在此修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麻烦太子。太子即然如此有威神,西域有许多需要你作的佛事,希望太子去那里发挥自己的神威。”太子说:“我有佛牙,虽然珍藏很久了,但是我连头目都舍得,我怎敢不奉献给您呢!”宣律收下了。这就是如今崇圣寺里的那只佛牙。
明达师
明达师者,不知其所自,于阌乡县住万回故寺,往来过客,皆谒明达,以问休咎。明达不答,但见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谒明达,问曰:“欲至京谒亲,亲安否?”明达授以竹杖。
至京而亲亡。又有谒达者,达取寺家马,令乘之,使南北驰骤而去。其人至京,授采访判官,乘驿无所不至。又有谒达者,达以所持杖,画地为堆阜,以杖撞筑地为坑。其人不晓,至京,背发肿,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为黄门侍郎,扈从西还,谒达,加秤于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门为湖城令,达忽请其小马,雍门不与。间一日,乘马将出,马忽庭中人立,雍门坠马死。如此颇众。达又常当寺门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马何多?”又长叹曰:“此中触处总是军队。”及后哥舒翰拥兵潼关,拒逆胡,关下阌乡,尽为战场矣。(出《纪闻录》)
明达法师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现住阌乡县、万回过去住过的那座寺庙。路过这里的行人都去拜访明达,向他问卜吉凶。明达并不答话,只能看到他有所表示就是了。曾经有个人拜访明达。问道:“我想要去京城看望父母,不知双亲平安与否。”明达递给他一支竹杖。他到京城时父母都死了。又有个拜访明达的,明达牵来寺庙里的马让他骑上,自南往北奔驰而去。这个人到京城后,被授为采访判官,整年骑着驿马到处奔波。还有个拜访明达的,明达用手里的锡杖在地上画了个土堆,又用锡杖在地上挖了个坑,这个人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到京城后,背部肿起个大瘤子,割掉后,身上的血流尽了,于是死了。李林甫为黄门侍部时,侍从皇帝往西而返回京城,途中拜访明达,明达将一杆秤放在他的肩上。回到京城后,他被拜为宰相。李雍门为湖城县令时,有一天,明达突然跟他要他那匹儿马,雍门不给他。隔了一天,雍门骑上马要出去,这匹马在院子里突然像人一样直立起来,雍门被摔了下来,当场死亡。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有一段时间,明达时常站在寺庙门口向北张望,自言自语道:“此处平川上怎么有这么多兵马。”又长叹道:“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军队?”到后来哥舒翰屯兵潼关,以抗拒胡兵的侵凌,潼关附近的阌乡到处都成了战场。
惠 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干昔时,但不知其甲子?”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图氏,一日因谒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耳。”广异之。后一日,仍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
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
用橡栗食,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废,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观。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问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绔,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
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师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
时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出《宣室至》)
唐宪宗元和年间,武陵郡的开元寺有个僧人法号惠照,看起来已经衰老了,身体也很瘦弱。他好预言人的吉凶福祸,而且都能说中。性格狷介孤独,从不跟许多人在一起说笑,常常关着门独自一人呆在屋里,周围也没有侍童陪伴。他总跟乡下人讨饭吃。有个八十多岁的乡下人说:“惠照法师住在这虽六十年了,他的容貌跟从前没有一点儿不同。只是不知他到底有多大岁数。”后来,有个叫陈广的,从孝廉举为武陵的官吏。此人爱好佛教,有一天便来寺庙拜谒。他遍访了各位僧人,最后来到惠照的房间。惠照见到陈广后,又悲又喜地说:“陈君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陈广十分惊讶,因为自己从不认识惠照。他问惠照道:“从未与法师交往过,法师为何惊讶我来晚了呢?”惠照说:“这件事不是马上就能说清楚的,应当与你详细地谈一宿的。”陈广觉得奇怪,过了一天,他又来到惠照住宿的地方,向他请教这件事。惠照于是讲道:“我是刘氏的后代,彭城人。是刘宋孝文帝的玄孙。曾祖父是鄱阳王刘休业,祖父是刘士弘。他们都精通《史记》。先辈们因有文学才能而负有盛名,为南齐竟陵王子良所熟识,子良招纳优秀的文学人才,先辈们也都参预了。后来又在齐梁两朝时作官;作过会稽县令。我出生于梁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夏季五月。三十岁开始在南陈求官,到陈宣帝时,作过小官,不为人知道。我跟吴兴的沈彦文是诗酒之交。后来长沙王陈叔坚与始兴王陈叔陵都广泛召集宾客,非常有声势。宾客们依仗自己受到权贵的宠爱,互相之间不服气。我与沈彦文都在长沙王的门下。等到兴王陈叔陵被杀害后,我与沈彦文担心长沙王也不能幸免,那就会殃及我们,于是一起潜逃了。我们躲在山林里,用橡栗充饥,穿一件短上衣,无论隆冬盛夏也没有其他衣服可以更换。有一天,一个老僧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对我说:‘你的骨相很奇特,不会患病的。’沈彦文也向他施礼、求药,老僧说:‘你没有刘君那样长的寿命。有什么法子呢!即使吃了我的药,对你也没有补益呀。’说完就告辞走了,临走时又对我说:‘尘世间因名利争强好胜,到头来能得到什么呢?只有佛教徒能不追求功名利禄呀!’我很敬佩他说的话,从此,一连十五年不问世事。后来又与沈彦文一起到了建业,当时陈王朝已经灭亡。宫阙残废,台城冷落,荆棘丛生,景阳宫也挂满了蛛网,只有空荡荡的房子还存在,至于衣冠文物之类,全都荡然无存。老朋友偶而相遇时,扯起衣襟直抹眼泪,哽咽着说:‘陈后主骄奢淫逸,终于为隋文帝所灭,实在可悲啊!’我更是止不住地抽泣。我又询问陈后主与陈氏诸王的下落,得知他们都进了长安。我与沈彦文提着一个布口袋,沿路乞讨,终于到了关中,我是长沙王原来的宾客,他对我恩遇十分深厚。听说他迁移到瓜州去了,就又赶到那里去拜见他。长沙王从小到大都过的是豪华日子,而且又很早就封为王爷而显贵起来;所以,如今虽在流放之中,仍然不能营生。当时他正与沈妃畅饮,我与沈彦文再次拜倒在他面前时,长沙王悲痛地哭了好长时间,然后洒泪而起,对我说:‘一日之内家国沦亡,骨肉离散,难道这不是天命么?’从此我便留在瓜州住了几年。长沙王死了几年后,沈彦文也死了。于是,我落发为僧,遁迹于会稽山佛寺中,在那里共住了二十年。我那时已经一百岁了,虽然容貌干枯瘦削,但筋骨强健体力不衰,尚能日行万里,便与一位僧人一起到了长安。当时唐朝皇帝占有天下,建立年号为武德,共有六年。从此之后,我或者住在京都洛阳,或者云游长江两岸,就连三蜀五岭,也没有我不去的地方。如今我已二百九十岁了,平生屡经严寒酷暑,从未有过小小的疾病。贞元末年,我在这座寺庙里曾梦见一个伟丈夫,他衣冠楚楚,仔细一看,原来是长沙王。我把他接进屋请他坐下,谈起往事来他非常伤感,就象他在世时那样。他对我说:‘十年后,我的六世孙陈广,会到此郡为官,法师一定要好好记着这件事。’我便问他道:‘王爷现在干什么?’答道:‘在阴间作官,官位很高。’然后哭泣着说:‘法师仍然健在,而我已六世为人了!实在令人悲伤啊!’梦醒之后,我便记下你的名字,放在经书箱子里。到去年,已经过了整整十年,我便以你的姓名,打听郡里的人,听说你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