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同人)[希腊神话]阿多尼斯的烦恼-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深刻轮廓,也被拥有精致梨涡的植物神以嘴角噙着的美丽微笑给镀上了柔和的愉悦光色,减去几分沉积的郁色。
他强压下震惊,万分艰难地眨了眨眼,才僵硬地找回自己微微颤抖的声音:“……请容我向陛下道贺。”
他想,自己再也不需要对陛下这几日的行踪心存疑虑了——尊贵冥王的寝殿可不是属下该放任好奇心去探索的禁地。
“道贺?”达拿都斯听得一头雾水,困惑的视线来来去去,无论如何都看不出陛下那与往常一般无二的冷脸究竟透露出了什么神秘信息,叫稳重自持的兄弟都露出异色。
“唔。”
心里愉悦得难以言喻,哈迪斯堪堪维持住表面沉默地瞥了他一眼,不着痕迹地小翘了翘唇角,自若地接受了。
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连指尖都酸软疼痛,软绵得无法起身的阿多尼斯自然是无法亲眼目睹这份可贵默契的。
“啊。”
跟初次体验美妙滋味,并很是欲罢不能的冥王不同,每当回忆起之所以让他落入这般田地的任何细节,都会叫他羞窘气愤得将脸一路红到耳根,一边重重地叹气,一边把头彻底埋进柔软的枕头中,恨不能与世隔绝。
剧痛叫植物神在慌乱下变成了兔子,结果还来不及松一口气,志在必得的冥王显然没将这点无足挂齿的小小阻碍放在眼里。他没有强制性地用神力将意图抗拒到底的王后变回人身,而是当机立断地变成了一只公兔,还在下一刻无师自通地压了下来。
在还没反应过来的错愕下以兔子形态被强压着,翻来覆去地激烈缠绵了几次,一处被点燃的炭火和干柴相会,便是毫无保留的炽情燃烧。一会是被扰的滔滔江河,一会是被揉捻的蜜汁,一会是焰滚滚的熔岩。神力透支的阿多尼斯不知不觉地就恢复了人形。白皙细腻的肌肤似在热水蒸腾下的泛着诱人的薄红,水雾氤氲的双目茫然地睁着,花瓣般的双唇微微翕动,光裸的胸膛随呼吸徐徐起伏。修长的双腿被分得极开,腿间狼藉得一塌糊涂。
当落在食髓知味的冥王眼里时,这便等同于在好不容易偃旗息鼓的火苗上又无声地泼了一桶油。
阿多尼斯并非不想直接昏过去了事,但相连的神格却不允许他这么做,于是在整个漫长的过程中,他的神智始终如精力充沛地蹦跳着的乌鸦般活跃,每一个羞愤欲死的细节都逃不开——比这还糟糕的是,甜蜜渐渐被掺入了这以痛苦为主来和出的面团,他一面发自内心地用理智去抵御它,一面又难以逃避被注入体内的强烈欢愉。
“温柔可亲的殿下,为何看起来满腹愁烦,又究竟是因何埋首那乏味的床褥?它的惨白可羞见更白嫩妍丽的肌肤,别赏毫无功劳的它饱啖这份美色的荣光。”不知何时起就趴在床沿,好奇地盯着他看的冥石榴忍不住开口了:“若是单相思会有被厌弃的愁苦,恰似被婆娑泪眼演绎的一出哑剧,然而陛下对你的爱慕,就如行走在新雪上会烙下足迹般凿凿,半点不如质疑。”
仍自厌中的阿多尼斯听得头痛欲裂,怕牵扯到痛处,唯有极其缓慢地回过头来,手肘半支上身,将脸转向全然不解,偏偏还爱多管闲事的这颗胖石榴,面无表情地问:“你是谁?”
这句简简单单的话可替被骚扰的他报了仇——冥石榴瞬间就被吓得摔下了床,要不是地毯柔软厚实,怕是要当场皮开肉绽。
阿多尼斯心道不好。
出乎意料的是,它却没有惨叫,只默默地重新爬了上来,旋即近乎尖锐地啜泣了一声:“要是忠心仆人的无心之语让你不悦,大可以让我粉身碎骨,而不是用憔悴的铁杵来施展一场细细碾磨的酷刑。”
阿多尼斯不禁揉了揉眉心——不知为什么,这浮夸的做派,倒是诡异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若要为自己辩护,就得举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他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会冥石榴卖力的表演,忽然道:“倘若你曾获得过一份毫无保留的信任,那定能道出我与陛下相识的原委。这来得唐突的婚姻,究竟是被技艺精湛的持弓者猎取的战利品,还是错误与爱交融后毫无价值的产物?”
冥石榴这次是货真价实地吃了一惊,在小心地确认它用身心去膜拜跟随的神祗是认真在问询后,不知所措地用金穗花们津津乐道的揣测作答:“分明是和谐美好的乐章,又因何被撇上刺耳的指控?陛下恋慕你的善和美质,避来此地的你则依恋这份安宁祥和,婚姻两头的配偶是万般登对,一往情深的眼不应被荆棘的锐刺所戮,铭记温柔的抚摸也不该被避若蛇蝎。”
第三十二章
两情相悦的一对?
纵使丢失了记忆,也不意味着他要任人糊弄。
阿多尼斯立刻就要开口细询,只是眼角余光恰巧捕捉到了那道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侧的模糊身影,下意识地住了口。
哈迪斯直接就问:“身体可还有不适?”
想到昨晚那牢牢地扣着后腰的手臂,果决强硬如鹰鴁捕猎的亲吻,炽热且力道十足的夯击,比潮汛要来得汹涌的热烈,连绵不断地填满了那道被深埋的浅浅欲壑,尚且青涩的植物神便不受自制地红了耳窝。
若说那荒唐的过程完全是痛苦的,又未免太不诚实。前期的生涩和粗鲁带来的磨合过后,除开那些酸软,被翻来覆去做了许多次的他其实也从肌肤的亲密碰触间品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只是强制的动作中带来了太多难受,携着屈辱和震惊一起给盖过了。
——夫妻之间的敦伦便是这样复杂而激烈的吗?
不知丢失的记忆里的那些空白曾经是被如何书写的,他想着自己身为冥后,就无法对这‘丈夫’生出深深的排斥。
“是。”他犹豫了会,还是决定不去幼稚地不搭理对方,默默地用被褥将自己裹得如最严实的蚕茧般密不透风,就仿佛这样起到保护作用,才重新躺下去:“陛下。”
这位行事莫测,脾性无常的冥王的身上究竟残存着多少自制力,是如今浑身筋软骨散,虚弱又疲惫的阿多尼斯是再不敢赌了。
“嗯。”
哈迪斯淡淡地应了一声,面上丝毫不露对这疏远称呼的不满,也不在意他的冷淡,径自坦然地在床沿坐下。
若不是阿多尼斯眼明手快……毫无防备的冥石榴差点就被当场压成了石榴汁。
目光先是在植物神烙上不少暧昧红痕的脖颈处稍作流连,又恰到好处地赶在爱妻的恼怒发作之前移开了去。
阿多尼斯一瞬不瞬地与他对视了会,既有担心对方会再为所欲为的紧张,又有因那透着露骨意味的眼神而羞恼,最后索性阖上眼来抵触,试图强行给自己营造出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心忖终于明白往日被自己的弩箭瞄准的可怜猎物是何种心情了。
冥石榴左瞅瞅右瞅瞅,直觉对冥后虎视眈眈的冥王陛下或许没看到渺小的自己,只是考虑到以胖胖的身材没法在下一刻迅速消失,唯有费劲地仰着脑袋,小心翼翼地招呼道:“高贵的陛下,请容我献上瞻仰。”
哈迪斯一声不吭地握住阿多尼斯露在外面的右手,唇平平地抿成一条线,对它的话语不管不顾,许久后突然慢条斯理地问:“它吵醒你了?”
阿多尼斯浑身不自在地挣了挣,只觉那像被铁钳牢牢禁锢般无法撼动,像被硬生生地塞入狭小鳝鱼皮中的狮虎,可品出这平静无波的话语后的杀气时,还是僵硬地做出了回答:“没有。”
无形的威慑力一松,被镇得半死不活的冥石榴这时才喘出一口气来。
阿多尼斯生出恻隐之心,忍不住想解放这抖若筛糠的小家伙,便睁开了眼,越俎代庖道:“铺满鲜花的祭坛无需多余的点缀,再甘美的蜜汁也不应被倾入已然盈满的器皿,在陛下对名为赞美的陈腔滥调感到厌烦之前,快快退下,放开多余供奉的香烟,履行你该尽的职责——”
话尚未说完,就被哈迪斯突兀地伸向他的手给打断了。
“陛下?”
常握着低奢权柄,时而攥着黑色缰绳的手指修长有力,却是初次流露出浓重的眷恋与亲昵。它先是试探性的,轻轻在净姣的颊上抚过,像是细细描绘着精巧的面容似的,徐徐掠过眉眼,温柔地将微潮的一缕发丝撩到耳后,露出光洁细腻的一截颈来。
阿多尼斯无奈地停下话来,发现这位陛下真是越来越爱动手动脚了,难掩躲避意味地偏了偏头,问道:“陛下?”
哈迪斯凝视着那小巧的喉结,心不在焉地应道:“唔。”
“难道连最后一点理智也被摒弃了吗?”植物神唯恐对方又要攻城略地,忙道:“再贪婪的渔夫也不会将误闯网中的幼小鱼苗掷入鱼篓,只有头脑发昏的君王才会对臣民索求无度,那比淤泥中冒出的水泡还要叫人作呕。昨日既你已成功斩关而入,今日便合该幡然醒悟,如弥达斯痛恨给他带来痛苦的财富般痛恨这叫人沉迷的诱惑。”
“节制是智者的美德,是船上重要的桅杆。横冲直闯的狂狼会给来往的船只送去倾覆的噩梦,一泄如注的暴雨叫和平的大地变成汪洋,有恃无恐的飓风是对闲散云朵的冒犯和挑衅,肆虐旷野的大火能叫肥沃的土地变得不堪入目的焦黑。喜好让情欲放纵的非掌管爱情的阿芙洛狄特莫属,除非你是遭了爱驾着天鹅车的她的阴谋诡计,就不会如可悲的希波墨纽斯和阿塔兰塔,在供奉大地之母的神圣庙宇前那称不上隐蔽的海绵石上放荡地结合,最终沦为在草莽中无望徘徊的野兽。”
哈迪斯暧昧的摩挲动作蓦然一顿,像是听进去了这番劝说了般,无端端地停在了发顶。
那双深邃的绿眸中透着厚重的疑惑,他轻轻地捻了捻指间那柔软得不可思议的莹白花瓣,又以指节抵了抵碧绿晶莹的花蕊,确认这不是幻觉后,不禁困惑地蹙眉。
在植物神墨绿色的柔软发丝间,不知不觉出现了一朵通体纯白无暇,蕊部却碧如翡翠的小花。绽开的花瓣就像被淅淅沥沥的小雨浇洒了一夜般莹润,稚嫩的茎上镶嵌的芽苞,则是惑人的淡金色。
哈迪斯很确定,在自己于今晨离开之前,它都是并不存在的。
阿多尼斯倒不怀疑他是在故弄玄虚要作弄自己,只顺着神情忽然变得奇怪的他的手摸索过去。当敏感的指腹碰触到小花时,面上的错愕就远比冥王的要厉害得多了:“什么?”
哈迪斯贴心地操控着神力,手指拂过阿多尼斯面前,轻而易举地变幻出一面极清晰的镜子出来,叫偷偷摸摸长出来的它无所遁形。
“花?!”原本只是惊疑不定的植物神瞬间睁大了眼,都顾不得身体不适地猛坐起来,不知是疼得厉害还是惊异这变化地倒吸了口凉气:“怎么可能!”
哈迪斯知他自己也不清不楚,便不再追问。
他趁着阿多尼斯心神不宁的空当,利索地舒张了手臂揽住冥后光裸的肩膀,视线却始终无法从白色小花上移开,甚至又碰了几下被折腾得摇摇晃晃的它。
接触到轻轻颤动的蕊的指尖,沾了一些晶莹剔透的冰凉粉末,他踌躇着轻轻尝了些许,竟比狄俄尼索斯亲手制出的佳酿要来的浓醇香甜。
花粉的味道太过美好,让从不注重口腹之欲的他都忍不住又尝了一点。
“请别再碰了。”阿多尼斯越发觉得头疼欲裂,挥手驱走了水镜,却也

![[希腊神话]复仇者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45/45033.jpg)
![[希腊神话]生来狂妄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47/47545.jpg)
![[希腊神话]女神的品格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73/73867.jpg)
![[希腊神话]原来我是向日葵啊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73/7391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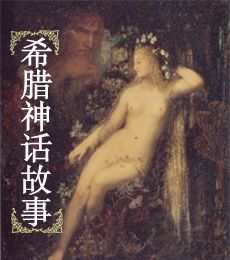
![(希腊神话同人)[希腊神话]冥府之主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89/8977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