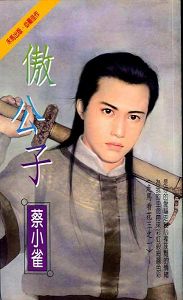公子倾雪-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已多年不曾和人这样痛饮过了。”
一般的禁地无非就是放着自家的武功秘籍或是破解之法,在厉害的就是破解他家武功的秘籍,但晏无端环顾四周,这密林阁不像是放秘籍的地方,倒像是住人的地方。松柏翠竹生得尤为茂盛。
“只是在下不愿被人打扰,所以舒公子才派人守在此处,以防有人勿闯,伤了性命。”那人想是看出晏无端在思量什么,及时说出了她心中的疑惑。
“既然如此,今日倒是我的不是。只不过能喝到先生的绿意新酒倒也不是枉然了。”晏无端知道,这世上有种人因厌倦了江湖纷争,多数选择退隐于山林,有些则是居于一处,不想见人。而这样的人通常都是武功极高的。
“在下晏无端,敢问先生尊姓?”
只见那人轻轻一笑,银灰色的瞳眸也渗出暖人的笑意。“昔年我行走江湖时,众人送了我一个绰号,你就叫我殊狂吧。”此翁殊不然,醉后语尤颠。
这号人物,晏无端是听人提起过的。据说此人甚爱喝酒,若是有人想找他帮忙只需奉上令他满意的酒。他若觉得此酒合心意,便是天大的忙也是会帮的。若是你上门求事,正好搅了他喝酒的雅兴,那么便是有去无回了。因此,有了个绰号叫酒仙殊狂。此人的武功在二十年前就已无人能敌,只是不知为何突然就失踪了。
江湖上的人总是关注新起之秀,又有谁还会记得当年的酒仙呢!若非此人自报家门,她也是不会将眼前的人和那个随性豪迈的酒仙联系在一起的。
“酒已喝尽,殊狂先生有事就说吧。”总不会无缘无故放她进密林阁的。晏无端只觉得又被麻烦找上了,而这回似乎还是个不能拒绝的麻烦。
“和聪明人说话总是特别令人开心。”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姑娘腰间所系的应该是红涤魂铃吧。”一般人也只是将其当成普通的腰饰罢了,并不会以一件武器的眼光去看它。
“先生,好眼力。”
“那么,姑娘所习的应该是意族的音魂。”殊狂慢慢道来。
晏无端听了言,心中不禁对殊狂此人另眼相看,江湖传言果真不假,真乃神人也。
晏无端自行走江湖以来,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而红涤在他人眼里也只是普通饰物,还从没有人能将她的武器以及所习之武这么准确的说出来。
不由得对殊狂此人钦佩起来。
“意族的武功虽说堪称精湛,但身为意族之人的你也应知道意族的极昼之说。”所谓意族极昼,便是当习武者所练的武功到了一定的层级,就会受到限制,并且无法将武功练到最顶层。并且习武者每使一次武功就会受到反噬,到最后武功尽失。
晏无端闻言,有着一闪而逝的震惊,而在这一闪而逝中,她甚至动了杀念。虽然,她的杀念也只是那么一瞬。意族,是一个不允许任何意族以外的人窥探的。
“呵呵,姑娘何必动怒,我无意窥探意族的辛秘,只是曾经有人向我提及过此事。”殊狂显然是察觉到了她那极淡的杀念。
“谁?”
“楼、玉、阙。”薄唇吐出这三个字。
“师叔?”那个传闻中的人物,那个将意族武功发挥至极的人物,那个意族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人物。
“你是玉枢子的徒弟。”殊狂先生很肯定地说,
“是。”
“难得让玉老怪找到个徒弟。”好像意有所指,又似陷入了回忆里。
“玉老怪性子怪,没想到教出来的徒弟倒不似他。”殊狂见晏无端并不说话,显然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淡然一笑。他从袖口摸出一个瓷瓶,放到她面前。
见晏无端根本没有问这是什么的念头,他也不以为意,自说道:“极夜草。”
玉老怪寻了二十年的宝贝,用以克制意族的禁制,可终究是没有寻着。
却是任谁都不会想到,这极夜草一直在他身边,他本不是意族之人,极夜草对他而言是没什么用的。
而他原本也是想将它送与另一个人的。只是,他还不曾将它送出,那人却已匆匆离去。
意族极夜草,晏无端当然知道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不然她师父寻这么多年,也不会毫无进展。
当世只余三株的极夜草,对意族人而言,可说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
师父一生追求武学的至臻之镜,却也始终突破不了意族的极昼之说。而二十年前,无意中得到极夜草的师叔也销声匿迹,终是没有人真正见过传说中的极夜草。
“你尽可放心,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极夜草。”说完,便将瓷瓶挪向晏无端。
若是别人这么说,也许她还会有所怀疑,但是殊狂却是没有理由骗她。一个武学与声名都已如仙级的人,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先生何意?”如此价值不菲的东西,这么轻易放在她面前,定然不是让人看看的。晏无端不是傻子,她若是想要这东西,必须是要付出代价的。
“帮我照顾一个人。”
“先生也许不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好徒弟。”所以孝敬师父这样事玉枢子也并不稀罕她做。而追求武学的至高之地,她更是没有兴趣。
若非当年玉枢子败给楼玉阙,自知在武学上胜不了他,也不会将她带上云浮山,收她为徒。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突破极昼,打败楼玉阙。
只是,在意族人眼里的至宝,对她而言也不过是云烟。
“这极夜草你迟早会用到,而帮我暂时照顾一下舒倦,你也并不会有何损失。”
“暂时是多久?”
“我要出趟远门,在我回来之后,我希望舒倦依旧安然无恙。”
“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活着也是一种痛苦。”像这样弱小的人,在意族是毫无人同情的。她没有遗漏,殊狂说的是舒倦的安全,而非倾雪楼的安危。
“你只需回答我行或者不行。”
“一个月。”
“成交。”
☆、花未眠
暖暖的东风还带着春日里的湿气,吹开了朦胧的雾色,露出了月亮。月光也是淡淡的,带着圆和的暖意。东蕖池边的垂丝海棠,在袅袅的东风里,无力地微摆着,仿佛在诉说说着不可动听的秘密。月亮在不经意中转过了厅廊,照进了薄纱围绕的帐幔里。
沁凉的青石板上,佣人早已将北辰上好雪猊皮做成的地毯柔顺的铺成了一圈。
雪猊性傲,独居于北辰最为严寒之地,及其不易捕获。就是北辰最为厉害的猎人要补上一头完整的雪猊也得花上少则半年的时间,这也只是幸运的。有些人甚至是死在了严寒之地,尸骨未寒。
雪猊中又以纯银色的尤为珍贵,甚至是比寸两金的小叶紫檀都要贵上千倍。这是生命为代价的结果。
只是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么珍贵而稀有的东西,如今却是被人用人当作地毯而已。
这纯银色的毛皮毯上,静静躺着两个人。
微寒料峭,春风拂过重重纱幔。仿佛是窥视了纱帐中的静谧,又缓缓地离去。
浅眠中的叶翩折,似乎被这微风搅了眠,不满地皱起了眉头,随即那琥珀色的眼眸便睁了开来,冷然地看了下四周,不带一丝情绪。
睡在他身一侧的雨绯色感觉到了他轻微的动作,随即也醒了过来。
“主人。”他轻声地唤道。氤氲的眼里有着刚醒时的迷茫。
叶翩折起身,毛毯从他的胸前滑落至腰间,露出皙白的肌肤,在烛光中散发着粙亮的光芒。
雨绯色见状,连忙起身,也不顾自己是否有穿衣袍,只将挂于一旁屏风上的红袍拿下,低着头,小心翼翼地伺候叶翩折将衣袍穿上。
他就站在他的身旁,却是没有那股勇气敢直视他的容颜,只是微微抬眼,看见他在烛火下,摇曳的风姿容华,便已觉得此生无憾。
刚想伸手将藏于红色锦袍中的墨发挑出,叶翩折却是眼神一冷,“啪”一个巴掌甩在他的脸上,看都不曾多看一眼,走出了帐幔。
雨绯色直愣愣的站在帷幔中,不知所措,他心中念着的人却已经不带一丝情绪的离去。他怎么就忘了,叶翩折最珍惜他的头发,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允许碰的。
容渊侯叶翩折,性冷戾乖张,素以手段狠辣闻名于南越国。据闻他曾一日之内坑杀幽州城内三千儒士,只因有个儒士在教坊教习时,曾言,天下美颜者甚繁,但若能与容渊侯媲美者,唯东隐国之相天机公子凤玠已。
众儒士闻言,皆以为是。
容渊侯向自负己颜,不满儒士之言,皆坑杀之。
南越王虽对此事有诸多不满,碍于西北之地,容渊做大,一时竟也不能奈何与他。
阵阵微风拂过,一院海棠纷纷垂颜,落于一旁的东蕖池中,无限风光。红色花瓣,随风落沾了身子,他也懒得理会,只合着眸子,听风吹叶动,流水涓涓。
直到一片花瓣直直地飘到他的眼睫,花瓣上透着淡淡甘香沾了微凉的夜露竟透出一股说不出的曼妙来。
淡淡的熟悉的香,他微微张开眸子,琥珀色的眼眸异样的魅丽,莹光流转,似释放了精魄的妖狐,不经意间就有着魅惑人心的妖异,却又在瞬间抹上了迷蒙,透着淡淡的哀伤。
岁月静好,却也只是一个人坐看火染霜晚。
“侯爷,属下无能。”默然出现一个全身黑衣的劲装男人,单漆跪地在他的面前。
“败了。”叶翩折嘴角淡有的笑,细长而纤瘦的之间划上了海棠那荆棘丛立的钩子,只是轻轻一动,纤弱的生命就在他的手中完结。轻轻语调,看似那么浓情惬意,却是字字欲夺人性命,叫人不胜心寒。
他似乎将人派出去的那一霎那就已经知道结果了一样。
容渊侯的暗夜十三杀,只余他一人回来复命。继而又是新的杀手接替原来的十二杀,而他却也从来都是看着十三杀的人一批一批的换,犹如流水一般。
曾经,他以为侯爷留下他的命是对他的恩赐,当时间犹如指尖的朱砂咯到他的心里,再划出一道道血痕时,他才明白,最残酷的惩罚不是死亡,是看着曾经认识的人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无能为力。
他是不被允许死的,这就是侯爷的恩赐。
白色的锦缎裹金靴覆上了地上无情物,只余静谧中的那一丝肃色。
较之于南越国的四季如春,东颍国如今仍是处于被皑皑白色包裹着的状况。东颍的冬季历来时间比较长,这寒冷而又漫长的日子,十分难熬。东颍的百姓却已然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总会折腾着想法子使他们在这茫茫的日子里不至于因冰冷困苦而心生畏惧。
倾雪楼内,一如既往的安静,许是怕打扰了公子的静养,是以不论是谁,在楼内总是轻声行事,便是初初进楼的人,也会被那种弥漫在楼内的气氛所传染。
只是今日,却有些特别。
晏无端出现的时候,这场倾雪楼内的比武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几天前舒倦就已经派人来告知过她,今日有场楼内的比试,希望她可以赏脸参加。今日一早,舒倦亦派人再次向她邀约,晏无端只是应了声知道。舒倦拿出了他的诚意,却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