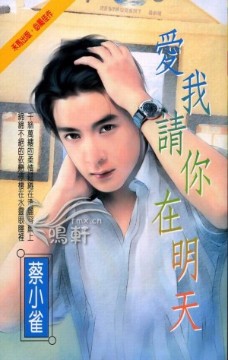谁让你在深夜里微笑?-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一个已婚男人而言,还有什么比离家到一个充满暧昧传说的城市生活一个月更有吸引力呢!
今夜,我们要启程到南京去;目的,冠冕堂皇:授课。我们这个地方经济不怎么样,应试教育在全国却小有名气。我们应南京某民办教育机构的聘请,前往该市讲课一个月。每天4 节课,每节课报酬100 元,食宿交通费由对方负责。呵呵,也还不错。这些,都是老刘联系的,他是大哥嘛!
对于我们而言,报酬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只要我们勤快,在B 市补补课,编写资料,也能弄几个钱,如前文所述,对陌生城市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向往,才是我们不辞酷暑的动力。
“唉!”老刘长叹一声,我知道,这是孙大圣跳出五指山时的愉悦。
“大哥,这次我们可以好好玩一玩了。”三狗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老刘的“啊”的深刻含义进行了阐述。
“哎,老胡才是大哥。来,老胡!”老刘递一根烟给一个50多岁的家伙。这个家伙头发梳得光溜光溜的,即使身材最苗条的雌性苍蝇也站不住。
老胡笑了笑:“刘老师就不要客气了,有志不在年高嘛!这两位小兄弟怎么称呼呢?”
老刘便将我们几个互相介绍了一番;前排那个大汉也是我们的同志。
我这才弄清楚,我们五个人,我教语文,那大汉姓陈,教数学,老胡教化学,老刘和三狗,大家都知道,分别教英语和物理。老胡和老陈,都是老刘的朋友,也是B 市一所赫赫有名的高中的教师。
老实说,他们四个人都比我快乐,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可比性――家与陌生城市之间的对比。但是,我也很快乐,我希望在南京,有什么奇遇,降低我在B 市的痛苦指数;准确地说,是降低对朝烟回忆的依赖程度。我们,已有3 个月没有联系了。我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甚至有些仰慕了:以前三个星期不见面,就像掉了魂,现在三个月音讯全无,魂儿还好好的附在身上。按这个进度发展下去,我元无雨重振雄风,也是指日可待了。所以,我也和他们一样欢呼雀跃。
我们坐的是长途卧铺汽车,咳,票还不好买,我们去的时候,只有三张票了。我和三狗年龄轻一些,将铺位让给了他们三个,我们俩睡在过道里。这里最烦,一些人起来上厕所,从我们头上跨过来跨过去的。有一次,一个女士从我头上跨过的一刹那,我不幸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她的白色短裤可隐约可见的黑黑的东东,害得我大半宿睡不着。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90天没有过性生活了。TNN 的!
我拍了拍三狗的脚,他立即坐了起来,原来他也没有睡着。
“TMD ,一些女人从老子头上跨过来跨过去的,晦气!”他抱怨道。原来,他也注意到了这个。
“看见什么了吗?”我笑着问。
“看见个××!”他骂道。
我心里说,我刚才还真是差点看见了呢。
天亮的时候,我醒了,原来昨晚还是睡了一会儿的。我睁开眼,汽车正在驶过南京长江大桥。这座桥我在小学课本里早就认识了,可以说是久仰大名。但是,说实话,桥面坑坑洼洼的,还不如我们B 市的××长江大桥。也难怪后来老刘有那么多的优越感。
下关车站是终点站。下关这两个字,给我的是深刻的仇恨,60多年前,倭寇攻占南京,在下关屠杀50000 多中国军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下关惨案”。据史载,死难者的鲜血,染红了江面。然而,现在的下关人,甚至南京人,又有多少还记得这个屈辱呢?我倒是看见了许多人举着牌子:问路3 元,带路5 元。原来,这个也可以生财。晕!
我们又坐上了出租车,向××中心驶去。司机问:“你们是哪里的呀?”
我觉得那声音有点像鸟叫,一点也不雄浑。
老刘抢着说:“武汉哪。你们南京城好小啊!”
我窃笑,我们B 市再过300 年,也未必赶得上南京呢。
司机说:“啊,武汉的,武汉好大啊?”
三狗马上说:“我们武昌就有南京大。”
晕!
这时,一直不说话的老陈道:“咳,南京比香港差远了!”
司机肃然起敬道:“这位是香港的客人哪?”
“不是。我刚刚从香港旅游回来。”
再晕!
老陈又说:“你们这儿的出租车好破啊!”
老刘忙拉了他一下,但话已收不回来了。
司机有些不高兴了:“你们武汉的出租车都是什么车呀?大奔吗?”
“差不多,差不多。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是香港的情况。”老刘忙打圆场。
司机撇撇嘴:“你们又不是香港的。”
老陈还在唠叨:“这么破的房子,还立在路边,也不拆掉;还有,这样的电线干也敢用―――香港决不可能这样!”
再再晕!
到了××中心,嗬,我们都乐了:我们的照片都被放大了,贴在中心大门口的广告牌上。我看见了自己的介绍,上面写着:“元无雨××名师团高级教师主讲高中语文主要著述《××一点通》《××考霸》《××讲析》《高中语文×谈》。”没想到,自己这么有成就啊!霎时对自己也很敬佩了。
最搞笑的是老刘,戴着眼镜,不多的头发向后耸着,颇似葛优在《围成》里扮演的李梅亭。他显然对自己的形象很不满,问我:“无雨,我就是这幅模样啊?”
我笑道:“没有关系,发廊小姐不会到这里来的。”
老刘大笑。
我知道,老刘到这里挣的钱,不一定够得上他的花销。果然,第三天晚上,我们吃过饭,去夫子庙步行街闲逛,回来路过一家美发店时,他说:“兄弟们,进去看看吧!”我们自然不好反对,就鱼贯而入了。
老板娘看见一下子涌进5 个大男人,喜从天降,忙招呼我们坐下,问我们“想怎么服务”。老刘严肃地问:“你们有那些服务?”
老板娘笑嘻嘻地说:“按摩啊,捶背呀,其他的,你可以和小姐商量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老刘是对老板娘本人很感兴趣。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老刘说,我刚才过去买烟,看见那家美发店的老板娘长得好像阿莲。三狗就诡秘地向我一笑。所以,现在三狗他们就存心玉成老刘的好事,就说,我们到上面去,老大和老板娘就在下面吧。上面是暗楼,专门搞按摩或其他活动―――这种结构和B 市的一样。我想,中国各地的美发店,大概都是这种结构吧!
几个小姐就带着我们上去了。上面也是几个隔间,但都没有门,颇像火车上的硬卧车厢,只不过多了一面帘子。大家都各自钻了进去,捶背呗!
“老板是捶30还是捶50?”我听见了,是隔壁替三狗捶背地小姐在问。
“30怎么捶?50又怎么捶?”三狗笑嘻嘻地问。
“你捶了就知道嘛!”小姐嗲道。
我身边的这个贴着我的耳朵问:“老板你捶多少的呀?”
我说:“我不是老板。”
“到我们这儿的,都是老板―――你到底捶多少的呀?”
“看看隔壁吧。”
“阿梅,你的老板捶多少呀?我们老板看你的呢!”
“老板,捶50吧!”那个叫阿梅的对三狗说。
“那就捶50的吧!”三狗爽快地说。
“那你也捶50的吧!”
我只好答应了。
“那你等着,我去那套套。”那女人说。
“要那个干什么?”我想,哪有这么便宜的。
“给你打××呀!”那女人诡笑着说。
“什么叫打××?”我好奇地问。
“嗯,打××,就是我用手帮你弄,保证让你舒服。”
TMD ,原来是手Y 呀,我才不干呢!我的××,只有两个人碰过,一个是我名正言顺的老婆,一个是我最爱的人。我才不会让你碰呢。你那手,不知碰过多少男人的××!
我说:“我捶30的。”
她马上不高兴了:“不是说好了嘛,怎么就变了脸?”
“我不习惯。”
“小姐,”三狗在那边叫道,“人家还是个处男,你想占便宜呀?哈哈哈!”
那女人饶有兴趣地问:“你真是处男?”
“你关你什么事?”
“随便问问嘛!”
我实在受不了她的手在我身上乱捶,就坐了起来,说:“聊一会儿吧,过会儿给50。 ”
她又高兴了,就和我聊起来。
“你们是哪里的呀?”她问。
“武汉,武汉的。”三狗抢答到。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
“不能告诉你。老大在下面,我们不能乱说。”我笑着说。
“你是哪里的呢?”我反问。
“苏北的。你是武汉的?我在武汉上过大学呢!”
我才不信呢。
“你上什么大学?”我故意问。
“武汉大学。”
我晕!武大毕业的,会干这个?即使干这个,也不会到你们这个街角小店干吧!
“呵呵,还是半个老乡呢!”我打趣道。
“所以,你要照顾我们的生意嘛!”
“我这不是来了吗?”三狗又抢答了,“我问你,捶50的多不多?”
“多哇!”
“那你不看了好多男人的××?最长的有多长?”
晕,狂晕哪!
“哈哈哈,那怎么能告诉你?”阿梅浪里浪气地说。
“三狗,你能不能闭上你的臭嘴?”我实在受不了。
“你不也是在捶50的吗?装什么正经呀?”那家伙叫嚣着。
是呀,我有什么资格在他面前当正人君子?我就沉默了。
“哎哟,哎哟。”三狗又在那边叫起来,估计快到位了。我却没有心思听,也不想笑,只觉得好无聊,好无聊。
我们回到宾馆看电视,节目叫《美人关》,就是一群男人在一群女人面前搔首弄姿,由女人投票淘汰,被淘汰的男人被女人推进身后的水池。尽管如此,三狗还是很羡慕,说自己要去报名,并且记下了电视上的电话号码,约我第二天陪他去电视台报名。
“呵呵,如果我得了第一名,五万元奖金我们平均分,怎么样?”
“你如果得了5 万奖金,我再给5 万。”我讽刺道。
“你有5 万元吗?”他反唇相讥道。
我还语塞了呢!正在这时,老刘拖着疲倦的身体进来了。
我慌忙给他倒杯水。
“怎么样?”三狗垂涎三尺地问。
老刘呷了一口水,喟然道:“那女的好可怜!”
“怎么了?”老胡关切地问。
老刘点燃一枝烟,娓娓道来。
原来这老板娘是安徽人,由家长作主,嫁给了村支书的儿子。而村支书的儿子是个弱智,所以她生了儿子后,就逃到南京搞这个了。
“嗯,是够可怜的。”一直不说话的老陈也开口了。
“那么,”三够迟疑了一下,“你们没有?”
“你这个小龙!”老刘笑道,“就关心这个。”
老胡和老陈也伸长脖子等待着。
“我先让她给我按摩,”老刘又点了一枝烟,狠狠吸了一口,吐出一股浓烟,“然后,我给她按摩。”
“这样啊!”三狗又张开了他那可恶的嘴。
“后来呢?”老陈问。
“后来,咳,我发现她的乳房好小。这说明她好久没有和男人这个了。唉,她还说我们有缘分呢!”
“是有缘分。”老胡肯定地说。
“后来,我给她500 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