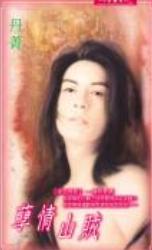伤逝情-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朗,我们是两个无可救药的傻B。’
‘鲁文,还想听我胡说么?’
他凑过来,给我点上一颗烟。’说吧,就算给你解解闷。’
我不由得苦笑,我已经从一个倾听者角色转换到了倾诉者。
‘其实刚才说的,我也不信。有时候你要挖掘表象后面的真理往往会很痛苦。打个比方说,我们知道,莫要以貌取人是我们认知的真理。但是事实呢?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人以貌取人,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爱情也一样。从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动物人和社会人。动物人往往展示的就是一些本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罗素认为一夫一妻制是违背人类的本性的,他就主张多夫多妻制。我还真觉得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鲁文惊讶地看着我。
‘我知道你的想法,你肯定觉得这和性放纵,滥交没有区别。事实上,性放纵和一夫一妻制是事情的两个极端,多夫多妻制才符合人的本性,变异思迁就是人的本性。’
‘不是吧,人总算还是情感动物吧。算了,我不打断你。’
‘人有情感是没错,但是情感只能保证一个男人和女人之间能够维系得久一点,而不是永远,而且这段时间的长短也应人而异,变异思迁是人的本质。再说社会人。一夫一妻制是历史的选择这没错,因为多夫多妻制很容易滑向性混乱,从而使得整个人种都崩溃掉。但是,光是一夫一妻制没有办法约束住人的本性,所以老祖宗才会搞出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来,才会主观地造成女人依附男人的态势,让女人从经济上依附男人。而现在不同了,男女平等,道德滑坡,都在松动一夫一妻制的底线,使得这些保证不再那么有效。因为除了情感之外,还有太多的因素能够左右男女间的平衡。所以说,有不少人在情感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想到生个孩子,有了孩子那一切又不一样了,因为两人之间又多了一种亲情在维系,尽管它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东西。’
‘你说的好像有些道理,但我总觉得哪里出错了。’
‘臭小子,你是想说我的脑子出错了吧?’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在和我背书哪?’
‘当然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好好,谢朗,你接着说。来,兄弟给伟大的哲学家满上酒。’
‘老实说,有时候我觉得很荒谬,平等是爱情的必要条件,但平等又为爱情埋下了隐患。《晃晃悠悠》里面的周文和阿莱,《成都》里面的陈重和赵悦,他们都有无比美好幸福的开始,为什么我们又觉得他们的结局是无可挽回的,是那么冷冰冰的现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陈重和周文都一样,他们一直没有改变,或者改变得微乎其微,而他们的另一半改变的又实在太快太多,让人悲哀的是他们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心里咯噔一下,感到全身发冷,我和秦卿又何尝不是这样。直到今天说出了这些话,我才真正想明白了。’当这种平等关系失衡的时候,他们的爱情早就死掉了,维系他们的只是情感而已,等到连情感都无法维系的时候,分手就变得无法回避。所以,我不再相信爱情,你要双方都不改变不可能,你要双方一直保持前进的步调,又何其艰难。你怎么能够期望生活在两个不同空间的人还可以彼此相爱呢?’
我的话音越来越低沉,仿佛喃喃自语。
鲁文拍拍我的肩膀,’了解,了解,还是喝酒吧。’
我真诚地向鲁文笑笑,也举起了酒杯,’所以,与其问我爱情到底是什么,还不如拉住小蕾蕾的小手,不要让她溜走了。干杯!’
我和鲁文一起都沉默了下来,望向窗外。窗外正好有一个年老的乞丐跪俯在道边,寒风里,一头苍白的头发随风飘拂,随着过往行人的脚步,捧在乞丐手里的破瓷碗,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地面,好像一下一下地敲在我们的心头。
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正文 八
“第五章 不如归去?
恋爱不但是一种病态,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黄舒骏《恋爱症候群》
‘谢朗,今天晚上聚聚吧,孙蕾也会过来。’
‘我不想出来,别逼我,我只想一个人呆着。’
‘唉,你又这样。你不怕会闷出病来的?离婚的人多了去了,喝醉几次,发泄一下,不就什么都过去了?你看看你,连工作也辞了,这样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呆着,有什么好?’
‘……’
‘秦卿真的要比你坚强。昨天,孙蕾告诉我,秦卿QQ的ID改成快乐放飞了,和别人聊得可欢了,你呢,你叫崩溃边缘!何苦啊!’
‘别说了,兄弟,放过我吧,我挺好的。就这样。’
我现在真的后悔,那天为什么一冲动就告诉鲁文这些破事儿。他倒好,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不是约我去巴国布衣尝川菜,就是去钱柜唱歌,生怕我有什么想不开。其实,至于么?我只是不想面对这小两口怜悯的目光。
鲁文问过我,离婚就离婚么,为什么要把工作也辞了?我知道他的想法,我承认这次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坎,照理说,忘情于工作是一个不错的解脱办法。事实上,这几天我翻来覆去地在想,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留在上海?我该何去何从?我还需不需要再在IT行业里继续打拼下去?还是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反正现在只要养活自己,这变得非常之简单了。
‘我们是迷茫的一代,是漂泊的一代。我们不属于北京,也不再属于家乡了。’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这样和沈帅这样瞎掰。
‘这简单啊。等你和秦卿结婚以后,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当年说这话的沈帅,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今年四月份,沈帅在电话里语无伦次地和我说,谢朗,你知道吗,今年的愚人节,张国荣跳楼了,我儿子出世了,他叫沈天笑,老子要他天天都开心。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家就是扎根。现在家湮灭了,我又被打还原形,成为浮萍,我对上海这个城市不再拥有归属感。在北京厮混的同学把自己戏称为’京漂’,是的,现在我已经是浩浩荡荡的’海漂大军’中的一员了。
昨天晚上,父亲给我电话,他很开心地和我讨论退休后的生活规划,把老家的房子好好拾掇拾掇,装修一下,弄弄花草,再养一条狗,最好我再加把劲,孙子他来带。父亲说,年轻的时候都想走出去,到他这把年纪就应该回去了,就像曾经在上海滩闯荡过的祖父一样。电话那端父亲说的神采飞扬,电话这端我喏喏而言,我张了好几次口,想告诉他事情的真相,最后还是挂了电话,一心盘算着叶落归根,含饴弄孙的父亲那么高兴,我实在是开不了口啊。
…… ……”
“铃——”
“喂。”
“程姐,我是侯锦华,你的朋友袁原在东魅喝醉了,还有个小子很不地道,老缠着她,我们差点和他们动手,可你朋友不领情啊,她死活不肯回家,还骂我狗拿耗子,我真是冤死了。你还是过来一趟吧。”
“啊——,好的,我马上过来,小猴子谢谢你,你先帮我看着一点。”
程柠心里很奇怪,袁原怎么会这样?可能,她也有不足向外人道的秘密吧。程柠拭干了泪痕,匆匆补了妆就出门了。
等程柠赶到东魅的时候,袁原真的把她吓得不轻。袁原一脸绯红,一手夹着七星,靠着吧台和程柠离开前就见识过的那个小白脸正在划拳。那么吵杂的环境,居然老远还让程柠听到袁原高八度的嗓音。
“人在江湖漂啊,哪能不挨刀啊。”
“五刀砍死你!”
(”三刀砍死你!”)
“两刀砍死你!”
(”一刀砍死你!”)
“你又输了,喝!给老娘喝!”
而小猴子和他的几个朋友正坐在吧台的另一端喝闷酒,一边死死地盯着那个得意的小白脸,颇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程柠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袁小姐,咱们还是划小蜜蜂吧。”小白脸暧昧地笑着。
程柠一把拉住袁原,”袁原,你怎么喝成这样?别喝了,我们回家吧。”
“咦,程柠?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我们划拳。一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啊……”
“看你比划的,小蜜蜂?还老母鸡呢!你喝多了,袁原,我们走吧!”
小白脸又凑了上来,”来,袁小姐,我和你划小蜜蜂。这位小姐,你也划拳吗?”
袁原醉眼斜睨着小白脸,”你是谁啊?滚一边去!我要和程柠划拳。”
“小猴子,他们几个人啊?”
“就他一个人,死乞白赖的……”
“就他一个你还搞不定!你怎么那么面啊?这个月的奖金想不想拿了?揍他!”
小猴子几个呼啦往上一围,那个小白脸见势不妙马上就软了下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不划拳就不划拳么,真野蛮!”,说着就溜了。
小猴子嬉皮笑脸地凑上来,”程姐,要不要我们帮忙,送你朋友回去?”
“不用了,谢谢你。”
(。。手机电子书)
“程姐,别的不说,刚才你可真有大姐大的风范。”
“贫嘴!就这么着,我们先走了,你们玩得开心点。拜拜。”
“拜拜。”
别看袁原刚才划拳划得那么凶,事实上她真的喝沉了,来到街上被冷风一激,脚步更是踉跄,而且身子还一个劲地往地上出溜。午夜的大街分外冷清,天空中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还别说今天是周末,即使是平时的这个时间,新天地外面的出租车还是来来往往从不间断的,今天倒是邪门了,等了足足有五分钟还是没来车。程柠架不住袁原,只好扯着她靠在路边的梧桐树上。程柠琢磨,改天得提醒袁原该减肥了,整天就知道串来串去地吃吃吃,身子死沉死沉的。
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强生,程柠连连招手。哪知前面一个穿着深色风衣的男人直冲那辆强生跑去。程柠不由得无名火起,”喂,你讲不讲理?车子是我们叫的!”
那位男士惊愕地转过身,不由得两人都愣住了。
竟然是谢少言!
“程柠,我们再来划拳……”
程柠呆呆地看着谢少言,说不出话来。
“袁原喝醉了?你们先走吧。再见。”谢少言冲着程柠一笑一点头,转身向前走了。
“喂,小姐,你们到底上不上车啊?”
程柠最后看了一眼那渐渐远去的孤单背影,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冰冷而湿重。
好不容易拖着袁原上了出租车。
“上哪儿?”
“去、去新天地,东魅。”
“啊?”司机惊讶地回过头,上下打量着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的袁原,”喝得那么醉?”
“是呀。”程柠不自然地笑笑,”师傅,去浦东,浦东大道,民生路。”
“哦,你们是海运学院的学生吧?”司机暧昧地笑着。
“不是。”程柠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自己和袁原看上去真的还有那么年轻吗?什么眼光。
“上回也有一个朋友,在万家灯火喝醉了出来上我的车,死活喊着要去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