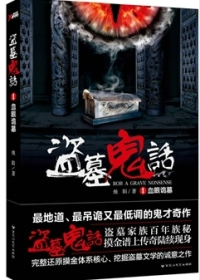宝珠鬼话-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天路上顺。手链新买的?”随口问了一句,她的眼神登时亮了起来。
“我老公从新几内亚带来的,好看吧。”通常,林娟把那位有钱的大老板叫老公,花她钱的小白脸叫我家宝贝,借以区分以免兴头上叫错。
“好看。”
“是吧,是吧,有价无市的古董呢。”一边说,一边眯着眼睛幸福地摸着手链。简直和某只狐狸自恋时没什么区别。
有时候,林绢和狐狸还真是很像的,比如两个人都很好看,两个人一听到别人说他们好看,都会洋洋得意。这也大概就是全班那么多人,为什么我独和她走那么近的原因吧,某些方面来讲,她和狐狸一样相处起来不用太费心。
“啧,宝珠,老早就想说了,你手上这串很久没换过了吧,式样蛮老的。”总算欣赏完了自己的,她又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我手上那串珠子上,在老师滔滔不绝开始讲课的时候。
夜校老师讲课的时候似乎永远是只管着自己的,一股脑地照书宣读,不管底下的学生究竟在做啥。听不听在你。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确实,有些年头了,和我岁数一样老呢。当年被姥姥挂在我脖子上,长大了不能继续挂脖子,被我绞了绞,弄成两箍缠在了手腕上:“是啊,我姥姥送的。”
林绢白了我一眼:“不是我要说你,你今天穿的衣服,和这串珠子配起来简直搞笑透了。”
“大姐,知道我穷,不要老打击我好不好。”
“一般店里十几块钱就能买到一根和衣服搭配用的手链了,穷不死你的好不好。”
“那也要有那闲工夫去逛的是不是。”
“你在说我很闲?”
“我啥都没说,姐姐。”
“切。你这小白,什么都不懂。首饰这东西,可讲究了,有些人穿衣服讲究品位,往往疏忽了身上的装饰,其实这玩意越小,越能看出一人的品位来,知道不。”
“绢啊,你干脆去开个个人仪表培训班吧。”
“你损我啊。”
“夸你呢。”
“嘿嘿。其实,我这串还不算好的。我老公说,他在南美有一次见到过一种真正的极品手链,那才叫好看。”
“极品?什么样的。”
看到我有点感兴趣,她朝两边看了看,故意压低了声音:“骨镯听说过不。”
“古镯?是什么,骨头镯子?”
刚问完,又换来林绢一顿白眼:“说你小白,你还真白上了。骨头的镯子,有人把那种不值钱的东西当极品吗?”
“那是什么?”
“所谓骨镯,其实是舍利。舍利是什么你知道不。”
这回换我白了她一眼:“据说我比小白稍微聪明一点,还知道舍利是啥。”
她嘻嘻一笑。眼瞅着老师朝她方向瞥了一眼,迅速抬高书本,压低脑袋:“佛家有佛骨舍利,那串手镯,是用十二颗佛骨舍利串出来的,据说全世界也不过就那么一两串。”
“是么,啥样的,你见过?”
她点点头:“老公给我看过照片,对了,照片我手机里存着,要不要看看。”
“要。”
伸手进包,片刻,林娟摸出了她的手机。
我瞅了一眼:“啧,又换了。”
“最新款嘛。”
“你当换衣服呐。”
她没理我,半晌,把手机往我眼前一送:“就它。”
我接过来朝屏幕上看了看。
也就那么片刻的工夫。之前嘴上还挂着刚才嘲弄林娟的笑,直至那张图从屏幕上跳进眼里,我不由自主一呆。
屏幕上一张小小的照片,漆黑色的底,上头一串白色的手链,手链是由十多颗大小不一形状不整的小粒骨状物串成的,关节分明,纹理清晰,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着一层珍珠般温和光洁的白光。
很古朴的一串链条,虽然我不清楚林绢所指的极品的美,到底体现在它的哪一方面,但我绝对可以肯定,这玩意儿,它让我很有眼熟感。
“喂,林绢……”又仔细看了看,我听见自己开口。
“干吗?”
“下次来上课帮我个忙吧。”
“什么忙?”
“我有样东西,我想让你帮忙看看那是啥。”
“嗯。”随口应了我一声,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因为这会儿她全部的心思正放在新来的那条短消息上。我百般无聊地抬起头。正考虑是不是得认真听会儿课了,朝老师这里看了一眼,随即却惊得差点把手里的书丢下地。
讲台上那位老师和往常一样正面无表情端坐着分析那篇英文短文,灯光下一张脸很白,和这里所有人一样,看上去像是几天几夜没睡好。当然让我惊得几乎把手里的书掉下地的,并不是她这张脸。
就在她讲台边,确切地说,就在她脚下,一个身影抱着膝盖坐着。
十六、七岁少女的模样,同样苍白的一张脸,却因着全身火一样红的一套棉袄子,显得格外的刺目和怪异。
这可是七月流火的天。
我突然意识到我看到了什么,但在这地方能看到这种东西,不太可能。
怎么可能……
它看上去至少……
正盯着它的方向看着,那东西突然象意识到了什么,原本低垂着的头一抬,两只眼睛直勾勾盯向我。
我被它吓了一跳。
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再朝那方向看去,身影却不见了。老师站起身开始在黑板上写东西。裙摆随着她的动作一飘一荡,就像刚才蜷在她脚下那个瘦小的身影。
第四章
回到家的时候,空气里全是湿漉的自来水和香波混合出来的味道,狐狸包着浴巾缩在客厅沙发上似乎睡着了,一头长发还湿着,把沙发上的颜色弄得深一道浅一道。
狐狸的头发是漆黑色的,很长,躺着的时候可以拖到地上。刚来的时候他会很自恋地捻着自己的头发叹气,然后嘲笑我:‘宝珠,人家说兔子尾巴长不了,原来你属兔。’现在他收敛了很多,大概头发被绑在水管上的滋味不太好受。
不过说也奇怪,他明明一只长满了白毛的狐狸,变成人身后怎么会是黑头发的,不是都说白狐狸长白头发吗?害我破灭了从小学到现在那么多年之久对白头发狐狸精的美好遐想。
光着脚走到他身边,手在他鼻尖上扇了扇。没醒,看样子睡死了,因为狐狸的耳朵和鼻子是最敏感的,和狗一样。我放心俯下了身子。
“你在找什么。”刚凑近了他的手腕在黑暗里仔细看的时候,冷不丁他突然间开口,把我给吓了一跳。
“找拖鞋。”飞快地回答,一边飞快跳起身跑到墙边上打开了灯,没有去看狐狸的眼睛。狐狸的眼睛在黑暗里会发出一种蓝不蓝绿不绿的光,光里看不见瞳孔,只有两点黑东西闪闪烁烁,如果不小心看到的话,很有点吓人。
“找拖鞋干吗不开灯。”翻身从沙发上坐起,狐狸张开手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两只手腕上都空空荡荡的,而他似乎也知道我在看什么,手放下的时候故意敞开了搭在沙发背上,一副便宜你了,让你看个够的欠揍表情。
身后窗外一道影子贴着玻璃一动不动,是那位无头帅哥。
“不想吵醒你呗。”从鞋架上抽出拖鞋丢到地上,我朝无头帅哥瞪了一眼。他拍拍窗,然后转身离开了。而那样的动作通常是他表现情绪的一种方式,可怜的家伙,都这样了还对别人幸灾乐祸。
“哦,我真感动。”狐狸捻了捻头发。又习惯性看向我的,随即撞到我的目光,嘴巴一咧,垂下头。
“狐狸,我的手链呢。”
等的大概就是我这句话了,因为他眼睛又弯了起来:“什么手链。”一边回答,一边捏着手腕。
“我上课前借你看的手链。”
“哦,那个啊。”
“在哪儿?”
“不知道。”尾巴一甩,大概以为我看不见。
“狐狸,别太过分,还给我。”
“不还。”微微地笑:“已经扔了。”
“扔了?!”几步走到他身前。
而狐狸眼见着我过来,身子一横,重新缩进沙发里:“想非礼啊。”
我伸向他脖子的手一阵恶寒,特别是接触到他那双妩媚得让汗毛都能跳舞的眼神的时候:“我KAO,狐狸,你能不能别笑得那么淫荡。我对女人没兴趣的。”
狐狸眨巴了下眼睛。一个翻身背对着我趴好了:“那就别来理我。”
“手链还我我就不来理你。”
“你要手链做什么,宝珠?”
“戴啊。”
“你不要原来那串了?”
“我还有左手的是不。”
“它不适合你。”
喉咙口一堵。耐了耐性子才把骂他的话咽回去,我在他边上蹲了下来:“狐狸,你又没见我戴过,怎么知道不适合。”
突然回头,他出其不意拍拍我的脸:“什么样的长相配什么样的首饰,猪一样的就带带珠子的啦。”
“狐狸!!你找死啊!!”
“谁让你趁我睡着的时候偷窥我。”
“我长针眼来才偷窥你这只裸体狐狸!!”
“裸体?宝珠你好色。”
“快还给我你个死狐狸!!”忍无可忍一巴掌拍向他的背,啪的一记脆响,不出片刻,他背上五根通红的指印随着声音的消失慢慢显了出来。
我愣了愣,因为没想到狐狸居然没躲开。平时指头离着几公尺远他就已经闪得没影子了。
然后看着狐狸坐起身,抓了抓后背。
我搓搓手,因为手掌心火辣辣的疼。看样子那一下够他受的:“你就是欠揍,”有点心虚,不过不能让他给察觉了去,狐狸这生物给脸上脸,同情他他会让你后悔到想哭:“还给我不就没事了。”
他看了看我,脚一翘,斜靠进沙发背:“扔都扔啦,怎么着,你看着办吧。”
“你……”
“我困了。”
“狐狸你今天有问题。”
“明天一早还要出门呢,晚安宝珠。”手撑着头,他闭上眼睛。
“手链到底在哪里。”
“问垃圾回收站吧。”
“给个理由。”
“宝珠,别让我感觉在甩了你行不。”
“死狐狸!!明天去垃圾回收站找你那些破糕吧!!!”
“好的好的,先准备好赔人家定单的钱。”
“死狐狸!!!!!!”
搬开阁楼正西方的桌子,底下有一只坛。坛子是姥姥以前用来腌酱菜的,很有些年头,那种五六十年代传统的纺锤形式样,原本油光甑亮的釉面上一层老灰。
把坛的盖子打开,里头还有一股淡淡的酱油味,不过坛子里是空的,除了坛底一层薄薄的朱砂,还有一张被朱砂压在下头的黄裱纸。
这是狐狸的印,作为收留它的报偿。
据他说这种印叫地网,是明末清初时道家常用的一种驱鬼术,虽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术法,但驱散一般的孤魂野鬼,那是绰绰有余。我对此始终将信将疑,虽然确实从他住进这里之后,至少在这屋子的一定范围内,那些东西再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出入我的视线,甚至靠近我。但也并不绝对,比如那只经常会闯到别人家找自己头的无头鬼阿丁。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虽然在意料之中,但难免还是有点失望,手链确实不在这里,而这是我在狐狸房间翻箱倒柜一无所获后所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可能。
连这地方都没有,那么手链到底被狐狸藏哪儿去了,还是真如他所说的,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