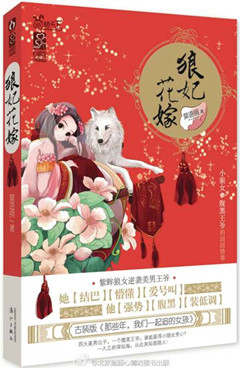江山記-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者,你有何把柄落在文家手中?”
“臣妾如今依文府而存。与文侍读感情若何,与文家是否有把柄,乃是臣妾和文家的事,不干社稷,更无关皇家。陛下何出此问?”我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他盯了我半晌,道:“朕只是想知道。因为朕需要一个答案,才能下决定。”
“什么决定?”
“因为朕肯维护一个无德无能的女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朕想要你。但朕又不能要得不清不楚,所以朕得知道你和文家的干系到底如何。”他把后四个字咬的很重,而我却被第一句话给打懵了。
平心而论,皇帝对我不好么?相对宫里他人而言,他对我非常特别以及极其地好,毫无疑问。但他一直阴阴晴晴,疏疏近近,如云如风,搞得我整日里心都提在嗓子眼。文禾早看出来皇帝的意思了,所以他与皇上对话的语气里,常常带有生硬,可愚笨如我,却没能理解到。两个人对阵,文禾面对天子,生杀之内,岂有胜算?现在可好了,我一想到这些,除了手疼膀子疼,头也开始闷疼起来。我说:“臣妾已经订下亲事,陛下也是知道的。臣妾与文府干系,便是如此。”
“朕的意思已经很直白了。如今宫中皆知你得朕宠爱,恐怕连宫外也泛传开了。而文侍读似乎并无反应,你可确定他对你心意?”他穷追不舍。
“陛下太不了解文侍读了。若流言可破他心,令他宁信人不信我,那臣妾早已不在此地了。臣妾谨遵信诺,未曾动摇,求陛下成全!”我又待顿首,他却忽然伸手托起我的下巴,令我仰脸看着他。
“前些日子,你二人可不是这个态度。你不是还要求朕放你归去么?今日又笃定如此,朕真是想知道,他到底给你吃了什么?”他稍稍用力,我眉心一耸,心下恼怒说道:“他给臣妾吃了陛下没有的东西。”
他眼底落下乌云,冷冷说:“宋掌籍,你可知朕是谁么?”
“当朝天子,九五之尊,皇极御顶。”我一字一顿回答。
“那你方才所言是什么意思?”他在生气,喷出的愤怒气息扫在我脸面上。
“人生而愿有相守,”我说,“若认了相守,便一生不弃。不管是刀山火海,还是浪底涛尖。如果见了别个的好就忘了自己当初许下的坚持,那世上还有什么是可守?什么人是可信?”
他沉默。继而平复了口气,脸色却更难看了:“就是因为朕来迟了一步么?”
我看着他眉宇间的阴霾,双眸中游荡的丝缕倦怠,想起那个晚上,他趴在龙案上熟睡的样子。想起香气缭绕中,他握着书卷,在我耳边呢喃诵读的样子。想起我从龙榻上醒来,他撩开帷帐浅笑着对我说话的样子。想起我上午自烫,他拉着我的手吼我的样子。还有刚才,他斥责后妃,然后温柔而霸道牵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的样子。我如何不曾心疼这个背负江山疮痍的男人?他不是庸君,却难以施展;聪敏自制,仍无力回天。他怀抱中兴理想而勤奋工作,想要改变一个时代,但是没有成功。
“皇帝,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是老托说的话,我复述给眼前的他听。他闻言面上阴郁更甚,咬牙道:“那你又是什么?”
“我是,时间长河里,一颗飘来的微尘。我只是微尘。”我望着他的眼睛,说。
“朕若一定要封你在册,你便会再次飘走么?”他的手触着我的下颌,微微颤抖。
我不忍心再看他的表情,垂下眼睑,深吸一口气,“请陛下恕罪。”
仿佛过了很久很久,我感到他慢慢地松开了手,那压迫感和衣服上的香气也随之离开。待我睁开眼再看时,他已然回到了龙案后面坐下。
我刚要开口说点什么,他抢先一步说:“叫王承恩。”
我叫了王承恩进屋,皇上头也不抬,又恢复了往常带一分慵懒的威严,说:“把宋掌籍归回尚仪局,以后不必来御书房侍驾了。”
王承恩愣了一秒,行礼:“遵旨。”
我终于可以再回到尚仪局,离开这是非之地,按说应该庆幸才是。但为什么,见他收起真容,坐在赭黄绣龙大案后头,再次把那君王面具戴上,竟会觉得心肝如绞呢?我默默对着他行了礼,随王承恩走出御书房。
第二卷 龙之卷 第十四章 失踪
回到了尚仪局,我觉得日子似乎比以前要更别扭。在她们眼里,大约我就是一个自作聪明,令皇帝新鲜了二日又厌弃的攀龙失败的傻妞,皇后和田贵妃眼中的钉,肉中的刺。除了向我布置任务的徐瑶以外,没有人主动与我接触,但凡有事,她们也尽量转徐瑶告知我。皇上不再传唤我,但也不说削职或是有什么别的安排。这难捱的日子总是过得很慢,只一点好在我主要做的是整理典籍,拟出部分目录然后排架,不需要与人接触。徐瑶是刻意把这个任务安排给我的,而且指明每工作三日,隔一日。这么算下来,也就相当于有双休日了。
我在忙碌的空隙里让红珊打发人去桃花渡问了一次清歌的事情。她告诉我仍然在找,没有确切的线索。我能想出胡黾勉内心着急却仍淡定平和的表情,搞不好还会安慰别人:莫焦心,会找到的。
明天就是第一个休息日了,为了让后天的开始更轻松,我决定今日多整理一些。一册一册收列记录,重新码放,不知道过了多久。库里一向偏暗,有人在时便一直点着灯,所以当我揉着酸痛的腰出了库时,发现天已经黑了,心想不好。拿着牙牌奔到城门口,御林军守兵已经关了大门,他们认得我,扬扬手道:“宋掌籍,今天你出来晚了,都戌时了,不能出去了。”
“我干活误了时辰,可否通融一下?”虽然知道门禁森严,还是想求个情。
守军摇摇头,不再说话。
我叹口气往回走。这宫中并没有我的铺位,因为我是不留宿的。惟一一次……是在御书房,那之后一系列的折腾令我心有余悸。如今只有去求徐瑶,让她帮我安排凑合一晚了。孰料回了尚仪局,发现徐瑶已经走了。掌籍刘琨瞥了我一眼,爱搭不理地说:“徐典籍去了古今通籍库,一时半刻回不来。”
皇城之内是不能乱走的,尤其古今通籍库离后宫之地非常之远,尤其我还是一个路痴。我出了尚仪局,不知道往何处去。慢慢地走了一刻,到了奉先殿墙外的道旁,这时,我忽看到奉先殿外角落里的树影下金光一闪。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在一棵巨槐后面。可是我太熟悉这金光了,看见它的同时便不由自主拔腿跑过去。等我到了树后,发现却空无一人。我四下张望,只见奉先殿南墙昏暗的拐角处,一片衣袂一闪而过。我定了定神,跟在那人后面走过去。会弄出这道金光的,唯有此人,可他为何要躲我?
在影影绰绰的道上,一边远远地跟着那不明的身影,一边还要躲避别人的发觉,我直跟到乾清宫西苑门外,那身影又不见了。失去目标,我在大门外躲开守门太监的视野,往里窥视。一切都似乎没有异常,那个身影仿佛从未出现过,守门的太监依然偶尔打着瞌睡,间或有端着盘碗的宫女宦官出入。御书房的灯依然大亮着,我知道他照例仍是把自己埋在奏折书堆里。我守在那灯光无法触及的暗处,觉得那间自己曾几度出入的房子现在距离有千里万里,都不像是真实的。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我忽然感觉面前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连些微的风声和宦官们低声的耳语都消失了。那门口两个守门太监依然微垂着脑袋,似睡非睡的样子,可是居然站得非常稳,连衣角都不再摆动一下。我正在疑惑,却见门里出来了刚才的身影,一身粗布短打,在御书房透出的灯光里不慌不忙地走出来。我惊讶地盯着他,觉得手脚冰凉。他径自往原路方向去,却又停了一步,扭头看向了躲在宫墙阴影中的我,粲齿一笑,继而消失在路的那一边。
一倏忽的不真实感过去,我发现前头的空气又开始流动了,微风也轻轻吹着。一个御前牌子从西苑门出来,上手推了一把正打盹的守门太监,那太监站定了,低声说了句什么,又昂首挺胸站着了。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似乎毫无所知,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他——那个挨千刀的偃师。
我再回到尚仪局的时候,徐瑶已经在里面,见我回来,责备了我一下,怪我不该乱跑。继而安排我同她一起住一晚,明早再出宫。我点点头,谢过她,乖乖跟在她后面走。我累得半死,可是心里又很清楚,这一夜,我恐怕很难成眠。
第二天一早,我在宫门打开的第一时间就出了皇城。文府的轿子还没有来,我便自己找了脚夫回去。红珊在房里已经准备了干净衣服,盥洗水,薰香等。搬到文雪的房间以后,我便有了单独的浴室,其实就是一小间半封闭的屋子,连接汲水,薪火加温,比以前客房可自在多了。我沐浴之后感觉清爽,困倦也去了不少。一边吃早饭一边等着头发晾干,让红珊帮我拿了外出的服饰,待会陪我亲去一趟桃花渡。
桃花渡依然是老样子。一层唱戏,没到饭点,都是些闲散人员,嗑瓜子吃糕点,喝茶聊天。我想没有了清歌的好嗓子,客人多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吧。
今日程丹墨也在,他正站在戏台出将帘旁下跟宁超说话,发现我来了,两人走过来揖手行礼。我还了礼,开门见山问:“清歌可有消息了?”
两人对视一眼,程丹墨说:“宋姑娘,清歌还是没能找到,更可惜的是,勤之兄也走了。”
“什么?他也走了?”我意外地问,“他何时走的?”
“昨日。对了,他好像留了信给宋姑娘是吧?”程丹墨看向宁超。宁超点点头,从袖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页信纸,寥寥几句话:飘零我今已惯,拜别诸君,寻亲此去,愿与他年共饮山前。黾勉上。
我呆了一刻,再看一遍,想从他的字里行间找出深意。他不是皇上的人吗?怎么可能就这么走了呢?我总觉得昨天,直到现在的事情,都像是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这整个的主使,是偃师,还是皇帝?
程丹墨见我一会皱眉一会撇嘴,说道:“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收起信纸,“他说去寻清歌了,就此拜别。”
“我们也派了所有人,安排了所有关系去找,可是都没找到清歌,只知道有人看见她出城,有人说她往南去了,却再没有线索。”宁超遗憾地说,“勤之一定急坏了,所以才会不告而别,幸好留了封信,不然我们还以为他也失踪了呢。”
“那是自然的,横竖清歌那丫头也是勤之兄唯一的亲人了吧。”程丹墨也叹息。
我倒觉得,胡黾勉的决定没有这么单纯。可是目前我并无证据,更不好与他们说什么。最好还是附和一下吧,但我刚待开口,只听得二楼一个欣喜的声音叫道:“宋璎珞!”
第二卷 龙之卷 第十五章 再会
众人一齐抬头往二楼望去,只见二楼楼梯口被一具身躯生生堵住了大半,上下楼的人都动弹不得。那身躯的主人,不是陶玉拓小姐又是谁?她穿湖蓝织锦提花褙子,绣花褶罗裙,脸上绽开大大的笑容,下巴也变作三层,直向我招手:“好久不见!”
一层散座的人们都不看戏了,保持同一个姿势望着她:张口、仰头、瞪眼。我感到身旁的宁超和程丹墨在看着我,便也笑着回:“是多日不见,玉拓一向可好?”
“宋姑娘,要不你先上去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