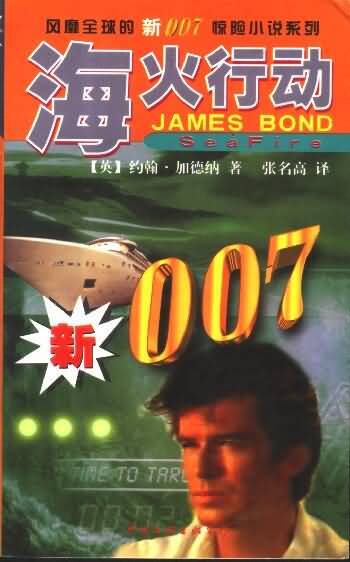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只有几个月。”阿弗纳对她说。“也许是一年,我无法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没问你。”肖莎娜回答道。
“我尽量多给你写信。”阿弗纳继续说。“你不用担心没钱。”
“我不担心。”
她越不反对,阿弗纳越是觉得要替自己辩护。他变得狂躁不已。“我告诉过你可能会这样,”他说,“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
“我知道。”
“那,你知道的话,”阿弗纳说,对她勃然大怒相当没有道理。“你还要我干什么?我无能为力。”
肖莎娜笑了起来,她用双手托住脑袋。蜜黄色的头发从前面垂下来,她将它们从脸上吹开。“你的问题,”她说,“就是你真的不理解。”她吻了吻他。“孩子出生时你会争取回来,是不是?”
“我发誓回来。”阿弗纳热情地说。“我保证回来。”
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第二天早晨,他洗了一个澡,打好包,然后踮着脚走进卧室。肖莎娜还在熟睡,或者好像还在熟睡之中。阿弗纳弯下腰吻了吻她。她总是不去机场送他。
现在是9月25日下午较晚的时候了,阿弗纳从米迪酒店正面粉红与白色的墙壁上的窗户中望出去,他看见罗讷河对岸、“吉桑将军”河堤的灯光亮了起来。河面上灯光粼粼。日内瓦这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玻璃屋。
阿弗纳移动视线,首先落在卡尔身上,然后是汉斯、罗伯特和斯蒂夫身上。他们都回头看着他,神情轻松、自信,充满了期待。
看着他们坐在那里,阿弗纳突然有一种感觉,尽管他才第二次见到他们,但他最了解的是这四个人,最亲近的也是这四个人。他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带给他的身体上的震颤,他能猜到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真情实感。
他们在等他开口说话。
阿弗纳说话了。他说得轻松,漫不经心。他偶尔看一眼卡尔,卡尔正抽着烟斗,用点头对阿弗纳说的话表示肯定,或者用一句话或一个手势来纠正他说的话。汉斯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着,罗伯特靠在椅子上,双眼闭着,手插在衣袋里。斯蒂夫时不时地吹一声刺耳的口哨,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
不过,阿弗纳开始滔滔不绝地念那十一个目标的名字时,他安静了下来。汉斯暂时停止了手中的涂画,连罗伯特也睁开了眼睛。阿弗纳停下来之后又恢复了沉寂。
“呃,”汉斯终于开口了,手里又开始涂画起来。“我们对他们似乎了解不多。背景知识有点不足。”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了,”阿弗纳说。“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知道他们有谁喜欢打牌。”
“我明白你的意思。”汉斯点点头。“伊弗里姆所说的无辜的旁观者,似乎不包括爆炸的时候。”
罗伯特抬起头来。“你错了,”他说。“不一定不包括。他要求我们多动脑筋,就这样。”
“明天,”阿弗纳说。“今晚我们就搬进去吧。”他的话起作用了。他们是他的队员,是他的同志。
阿弗纳在“大使宾馆”给卡尔、汉斯和罗伯特订了房间。而斯蒂夫住在米迪酒店里。会议结束后,阿弗纳和斯蒂夫去散步。街上车子川流不息,晚饭后的人们拥挤在舍弗鲁广场,看起来兴高采烈,举止优雅。几乎是本能地,阿弗纳和斯蒂夫将脚步向河边迈去。
玛希那桥走到一半时,斯蒂夫停下来,靠在用金刚石装饰的栏杆上。此时桥上人迹稀少。城市的灯光,就像弗雷斯大转轮上的反光,在波浪上扭曲着,旋转着,让人沉沉欲睡。“伙计,我有一种感觉,”斯蒂夫说。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好像在提一个巨物似的。“我有一种感觉,并不是我们都能活下来。”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
“不过,别担心。”斯蒂夫说。他停下来,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咧开嘴笑了。“我也碰巧有一种感觉,你和我可以活下来。”
第三部 任务
第五章 威尔·兹威特
里奥纳多达芬奇酒店位于罗马梵蒂冈城的费得格拉池,是个价格适中的假日酒店风格的酒店,非常对阿弗纳的胃口。
酒店顶层的房间可以远眺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也能看见圣天使堡。更重要的是,在阿弗纳看来,酒店干净、现代,浴室里有三星级的淋浴器。而且隔壁就有一家“格拉池小酒馆”,窗户里有一只巨型猪头,阿弗纳每次看见它时总觉得很滑稽。
阿弗纳和卡尔住进里奥纳多达芬奇酒店是10月15日,星期天——这天离他们第一次离开以色列前往日内瓦的那天差不多三个星期了。自从10月10日以来,斯蒂夫和卡尔一直住在费米齐诺机场附近的“假日酒店”。而他们的总部设在汉斯、罗伯特和阿弗纳下榻的奥斯提亚的一家酒店里。奥斯提亚是地中海的一个度假胜地,距罗马几英里。同一天——就在他们办理退房手续搬到罗马之前——罗伯特在面向海滩的一个停车场遇到了他的一个联系人。联系人递给他一个结结实实的购物袋,里面装了五支22口径的贝雷塔手枪,每支手枪配了两夹满满的子弹。
第二天,10月13日星期一,早上8点30分左右,一个意大利年轻人开着车,在离酒店一两个街区的地方接上阿弗纳和罗伯特。这里是费得格拉池的边界,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广场,名叫自由广场。车开得悠哉游哉——按照罗马人的标准——汽车穿过台伯河上的马格瑞塔桥,绕过坡坡罗广场,沿着壮观的波各赛别墅公园边沿,顺着意大利大道一直向前就到了诺门塔那大道。汽车左转两次——第二次是违章的——之后来到迪里雅斯特街。从这里开始,汽车进入居民区安静曲折的林荫道,朝着北边的安尼巴利亚诺广场驶去。
虽然从喧嚣的旅游中心威尼托区出来不到十分钟,但安尼巴利亚诺广场完全是一番不同的景象。它是罗马众多不起眼的广场之一,因而不能像其他著名广场那样,夸耀自己有古寺、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喷泉,也不能夸耀有历史上著名的宫殿。实际上,除了一个极小的公园之外,安尼巴利亚诺广场上什么也没有。公园里有十几棵未经修剪的树木,从柏油环绕的土里长出来。那天晚上许多小型“菲亚特”汽车、“雷诺”汽车、“大众”汽车和“兰布雷塔”脚踏车都朝这个并没有停车场的地方拥挤。能挤多少挤多少,这是罗马的风格。
六条街道随意地向广场汇聚。两条向北的街道几乎是平行的,分别是玛萨茨乌科利街和伊瑞特雷街。后者的延伸段叫利巴街。这两条街道形成一个楔形,其南端的尖端就是安尼巴利亚诺广场。在这个楔形中,有一座不规则的七层公寓楼群,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租住在这里的是中等收入的罗马人,楼群的两边和楔形的尖端都有入口。面对安尼巴利亚诺广场的是C入口。一楼是小商小贩做生意维持生计的地方。C入口的左边是一家理发店。附近有一家餐馆,叫迪里雅斯特酒吧,在右边。
汽车到达布雷萨诺那街的转角处,阿弗纳碰了一下司机的肩膀。那个意大利人把车停下来,让阿弗纳和罗伯特下车。车子绕过安尼巴利亚诺广场,沿着来路快速离去。他的任务完成了。这时是晚上9点过几分。
阿弗纳和罗伯特逛到广场另一边,看到汉斯已经坐在一辆车子的乘客位上。车子停在C入口和迪里雅斯特酒吧之间。汉斯也注意到了他们,但没有任何表示。不仅没有任何表示,反而跟坐在驾驶座上的那个意大利女孩说起话来。阿弗纳和罗伯特看着她从汽车上下来,慢吞吞地走到迪里雅斯特酒吧拐角处,转身,又朝汽车走回来。
这个意大利女孩不知道这个信号的意思。这个信号的意思是,住在C入口上面公寓里的被阿弗纳和他的突击队看作“目标”的人在家,但现在出去了。如果他还在楼上公寓里的话,那个女孩会一直待在车里。如果这时候汉斯注意到出了问题,任务要流产了,他就会让那个女孩开车离开。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走到广场的另一边,也许是二十五码以外。斯蒂夫正在一辆租来的挂着米兰车牌的绿色“菲亚特125”车上等着。斯蒂夫车上也有一个意大利女孩,但她坐在乘客位上。如果汉斯发出了“流产”的信号,阿弗纳和罗伯特就会上斯蒂夫的车离开。
但这时,任务似乎在继续。阿弗纳和罗伯特在看得见斯蒂夫和汉斯的地方继续在广场上走着,轻声地互相交谈着。他们知道这时卡尔已经办好了他和阿弗纳在里奥纳多达芬奇酒店的退房手续——其他人早些时候已经办理了退房手续——而且把那套新护照、驾驶证和一些现金放在罗马预先安排好的地方,以防他们分开不得不独自突围出城。此时,卡尔也许还坐在附近一家上班族的酒吧里的窗户边,一边安安静静地喝着一杯康帕利汽水,一边观察着在广场上交叉的几条主要街道的情形。他的主要工作要晚些时候才开始。
这时——也就是9点30分左右——大街小巷仍然相当繁忙,不过,车辆比白天少多了。白天,罗马的大部分地方都是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但到了晚上,郊区的住宅区远没有那么忙。在罗马的大街上,除了数不尽的猫之外,主要就是青年男女们的“伟士帕”摩托车沿街而过的呼啸声。但漫步在街角,或站在街角互相交谈的人什么年龄的都有,所以罗伯特和阿弗纳也没有引起路人的注意。罗马根本不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城市。
又过了三十分钟,阿弗纳看见汉斯从停在C入口的汽车里面走出来。汉斯看了看表,走到司机旁,靠在门上与坐在驾驶座上的女孩闲聊了一会,然后挥手跟她再见。他看也没有看一眼罗伯特和阿弗纳,就穿过广场,向伊瑞特雷街的方向走去。那个女孩把车开走了。斯蒂夫仍然跟另外一个女孩坐在几十码以外的绿色“菲亚特”上。
很显然,应该各就各位了。目标的习惯似乎有些规律。如果这个特殊的晚上也不例外的话,几分钟以后他就应该从几个街区以外的女朋友家回来。在转入C入口之前,他仍可能在迪里雅斯特酒吧停下来打一两个电话。他公寓里也有电话,但突击队得到情报,由于欠费,电话被切断了。
汉斯把他的车支走意味着他看到了从广场那边漫步而来的一对意大利年轻夫妇。他们不是目标。那个女的双手挽着那个男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目标”回家的时候,在前面离他大约一分钟路程的地方走着。这对年轻夫妇知道,他们出现在安尼巴利亚诺广场上,就表示过去三天来他们一直监视和跟踪的那个人正在向他们靠近,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发给谁的,又为什么发这个信号。
看到这对夫妇以后,汉斯就要到第二辆用以逃离的车旁。这是一辆租来的货车,停在离广场几百码的地方,一个有些年纪的意大利司机耐心地坐在驾驶座上。阿弗纳和罗伯特悠闲地穿过广场,向公寓楼的C入口走去,同时留意绿色“菲亚特”中斯蒂夫的动静。在门廊徘徊得太久是不明智的。直到,或除非坐在斯蒂夫旁边的那个女孩下车,阿弗纳和罗伯特才能进入大楼的门廊。
如果她下车以后走开了,阿弗纳和罗伯特绝对不能进去。它是这次任务流产的最后一个信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