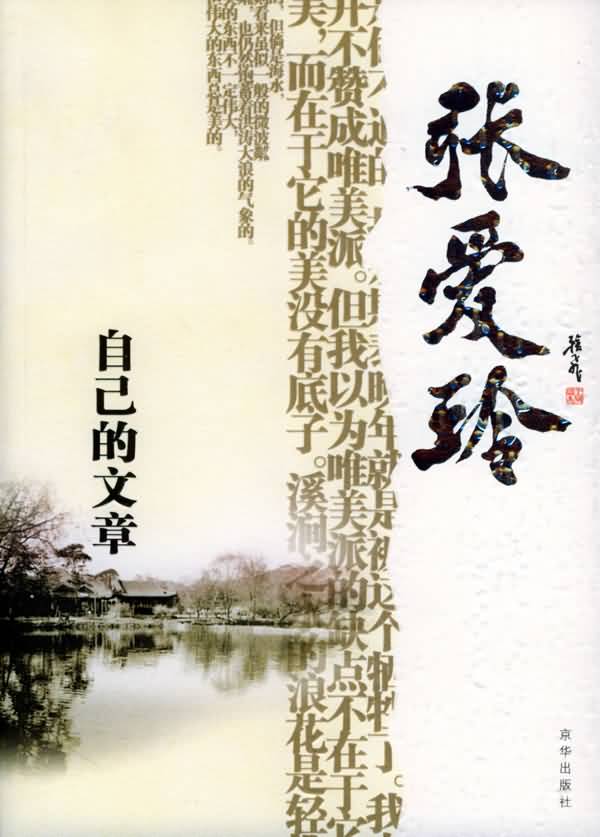余华散文随笔集-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认识是基于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客观。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而人的意志一旦投入生活,诚然生活中某些事实可以让人明白一些什么,但上当受骗的可能也同时呈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生活欺骗了我。因此,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当我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理解:我在逃离现实生活。汉语里的“逃离”暗示了某种惊慌失措。另一种理解是上述理解的深入,即我是属于强调自我对世界的感知,我承认这个说法的合理之处,但我此刻想强调的是:自我对世界的感知其终极目的便是消失自我。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世界的无边无际。我并不否认人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消解自我,那时候人的自我将融化在大众里,融化在常识里。这种自我消解所得到的很可能是个性的丧失。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排列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再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它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时间的顺序在一片宁静里随意变化。生与死的界线也开始模糊不清,对于在现实中死去的人,只要记住他们,他们便依然活着。另一些人尽管继续活在现实中,可是对他们的遗忘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死亡。而欲望和美感、爱与恨、真与善在精神里都像床和椅子一样实在,它们都具有限定的轮廊,坚实的形体和常识所理解的现实性。我们的目光可以望到它们,我们的手可以触摸它们。
二
对于一九八九年开始写作或者还在写作的人来说,小说已不是首创的形式,它作为一种传统为我们继承。我这里所指的传统,并不只针对狄得罗,或者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狄更斯,也包括活到二十世纪的卡夫卡、乔伊斯,同样也没有排斥罗布—格里耶,福克纳和川端康成。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旧小说,还是新小说,都已经成为传统。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即我们为何写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什么?我现在所能回答的只能是——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更为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
这种接近现在的努力将具体体现在叙述方式、语言和结构、时间和人物的处理上,就是如何寻求最为真实的表现形式。
当我越来越接近三十岁的时候(这个年龄在老人的回顾里具有少年的形象,然而在于我却预示着与日俱增的回想),在我规范的日常生活里,每日都有多次的事与物触发我回首过去,而我过去的经验为这样的回想提供了足够事例。我开始意识到那些即将来到的事物,其实是为了打开我的过去之门。因此现实时间里的从过去走向将来便丧失了其内在的说服力。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如果我此刻反过来认为时间过去只是时间将来的表象时,确立的可能也同样存在。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过去的经验是为将来的事物存在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只有通过将来事物的指引才会出现新的意义。
拥有上述前提以后,我开始面对现在了。事实上我们真实拥有的只有现在,过去和将来只是现在的两种表现形式。我的所有创作都是针对现在成立的,虽然我叙述的所有事件都作为过去的状态出现,可是叙述进程只能在现在的层面上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回忆与预测都是现在的内容,因此现在的实际意义远比常识的理解要来得复杂。由于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事物同时存在现在之中,所以现在往往是无法确定和变幻莫测的。
阴沉的天空具有难得的宁静,它有助于我舒展自己的回忆。当我开始回忆多年前某桩往事,并涉及到与那桩往事有关的阳光时,我便知道自己叙述中需要的阳光应该是怎样的阳光了。正是这种在阴沉的天空里显示出来的过去的阳光,便是叙述中现在的阳光。
在叙述与叙述对象之间存在的第三者(阴沉的天空),可以有效地回避表层现实的局限,也就是说可以从单调的此刻进入广阔复杂的现在层面。这种现在的阳光,事实上是叙述者经验里所有阳光的汇集。因此叙述者可以不受束缚地寻找最为真实的阳光。
我喜欢这样一种叙述态度,通俗的说法便是将别人的事告诉别人。而努力躲避另一种叙述态度,即将自己的事告诉别人。即便是我个人的事,一旦进入叙述我也将其转化为别人的事。我寻找的是无我的叙述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李劼强调的作家与作品之间有一个叙述者的存在。在叙述过程中,个人经验转换的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回避直接的表述,让阴沉的天空来展示阳光。
我在前文确立的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针对个人精神成立的,它越出了常识规定的范围。换句话说,它不具备常识应有的现存答案和确定的含义。因此面对现在的语言,只能是一种不确定的语言。
日常语言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语言,一个句式可以唤起所有不同人的相同理解。那是一种确定了的语言,这种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它强行规定了事物的轮廓和形态。因此当一个作家感到世界像一把椅子那样明白易懂时,他提倡语言应该大众化也就理直气壮了。这种语言的句式像一个紧接一个的路标,总是具有明确的指向。
所谓不确定的语言,并不是面对世界的无可奈何,也不是不知所措之后的含糊其词。事实上它是为了寻求最为真实可信的表达。因为世界并非一目了然,面对事物的纷繁复杂,语言感到无力时时作出终极判断。为了表达的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
当内心涌上一股情感,如果能够正确理解这股情感,也许就会发现那些痛苦、害怕、喜悦等确定字眼,并非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它们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要是使用不确定的叙述语言来表达这样的情感状态,显然要比大众化的确定语言来得客观真实。
我这样说并非全部排斥语言的路标作用,因为事物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纷繁复杂,它也有简单明了的时候。同时我也不想掩饰自己在使用语言时常常力不从心。痛苦、害怕等确定语词我们谁也无法永久逃避。我强调语言的不确定,只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表达。
我所指的不确定的叙述语言,和确定的大众语言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对世界的感知,而后者则是判断。
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大众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因此我寻找新语言的企图,是为了向朋友和读者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
世界对于我,在各个阶段都只能作为有限的整体出现。所以在我某个阶段对世界的理解,只是对某个有限的整体的理解,而不是世界的全部。这种理解事实上就是结构。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段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现实的必然性。但是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常理推断之中。我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告诉别人:事实的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事实本身,任何一个事实一旦进入作品都可能象征一个世界。
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表面上看为了表现更多的事实,使其世界能够尽可能呈现纷繁的状态,我采用了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但实质上,我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并开始脱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我发现了世界里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在这个整体里,世界自身的规律也开始清晰起来。
那个时期,当我每次行走在大街上,看着车辆和行人运动时,我都会突然感到这运动透视着不由自主。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事先已经安排好,在某种隐藏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所有的一切(行人、车辆、街道、房屋、树木),都仿佛是舞台上的道具,世界自身的规律左右着它们,如同事先已经确定了的剧情。这个思考让我意识到,现状世界出现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有着必然的前提。因此,当我在作品中展现事实时,必然因素已不再统治我,偶然的因素则异常地活跃起来。
与此同时,我开始重新思考世界里的一切关系:人与人、人与现实、房屋与街道、树木与河流等等。这些关系如一张错综复杂的网。
那时候我与朋友交谈时,常常会不禁自问:交谈是否呈现了我与这位朋友的真正关系?无可非议这种关系是表面的,暂时的。那么永久的关系是什么?于是我发现了世界赋于人与自然的命运。人的命运,房屋、街道、树木、河流的命运。世界自身的规律便体现在这命运之中,世界里那不可捉摸的一部分开始显露其光辉。我有关世界的结构开始重新确立,而《世事如烟》的结构也就这样产生。在《世事如烟》里,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情节与情节,细节与细节的连接都显得若即若离,时隐时现。我感到这样能够体现命运的力量,即世界自身的规律。
现在我有必要说明的是:有关世界的结构并非只有唯一。因此在《世事如烟》之后,我的继续寻找将继续有意义。当我寻找的深入,或者说角度一旦改变,我开始发现时间作为世界的另一种结构出现了。
世界是所发生的一切,这所发生的一切的框架便是时间。因此时间代表了一个过去的完整世界。当然这里的时间已经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时间,它没有固定的顺序关系。它应该是纷繁复杂的过去世界的随意性很强的规律。
当我们把这个过去世界的一些事实,通过时间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够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的新意义。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由记忆来完成的,因此我将这种排列称之为记忆的逻辑。所以说,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结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
事实上,传统叙述里的插叙、倒叙,已经开始了对小说时间的探索。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