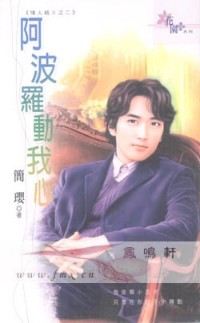我心不属于你-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南宫隼淡淡瞥望,起初思绪紊乱,只觉得影中人架惊不驯的神态异常熟悉,且活力清新的笑颜带着致命的吸引力。突然,他漂亮的眼眸半合,浑身如遭一记重槌击身般疼痛不已。
“她是谁?”懒懒吐出悠扬的嗓音,他极力克制沸扬的情绪,优雅地将症变的手移至腿上,紧握成拳。
到底是自小呵护他到大,南宫雀与南宫凰光凭他一句疑问,马上听出不对劲。两姊妹交换一眼,同感纳闷。
“抱歉。”曹姊急急走至,打断他们之间不寻常的气氛。“嗨,大情人,好久不见。”她热情轻笑,先抱了下南宫隼。
“马大哥刚去十楼。”南宫隼柔化脸上稍嫌僵硬的线条,温文一笑。
“噫,模特儿呢?”南宫凰奇怪地环视左右。
酒会一开始便不见曹姊大力推荐的女孩,她刚回旧大楼去找,听说那个女孩正为一件巧克力CASE忙得晨昏颠倒。
“模特儿?”原来是自家人。南宫隼拉回身子,舒缓地啜饮葡萄酒,很高兴积压心中的种种问题将要得到解答。
曹姊登时有些尴尬。“澄空先上七楼参观,顺便填饱肚子,等会就来。”能告诉他们澄空为了一件她认为过分隆重的礼服闹瞥扭,不肯来吗?
澄空?南宫隼感兴趣地拿起照片。
“她的全名是?”那恩爱的一夜,她化了浓妆,艳光四射。卸妆之后,她清新如朝露,竟漂亮得如此耀眼,动人心性,一样的醉人。
捉到妳了,宝贝。南宫隼猜不透心里那股几近雀跃的喜悦所为何来,他该感到愤怒才对。
“阿隼,别打她的主意。”曹姊夺回照片,郑重警告。
“为什么?”南宫凰好奇,哪个女人不想多巴结阿隼的?
“因为妳们家这个万人迷恰巧是她最讨厌的类型。”
讨厌?南宫隼一时无法理解。
“太花?”奇女子出现,这下子不爱谈八卦的南宫雀也感兴趣地凑进一脚。
“难道会是别的?”三位女人哄堂而笑。
他脸上的阳光陡地沉掉了半边,残酷的嘴角难看地掀了掀。
这可有趣了。
※※※
“哇啊!看看谁来了。”温蝶蝶瞟见身着一袭白缎改良式圆襟旗袍的佟澄空踏进酒会,跨张一呼,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就要休克了。
她要将雪海剁成绞肉。从在休息室里看到这袭别致的礼服和高跟鞋起,佟澄空便生了杀人念头,直到温蝶蝶的惊呼声强化了它。
这三天忙着工作几乎住进公司。本来为了避开南宫隼,她不打算参加酒会的,谁知曹姊软硬兼施硬逼着她来,还自作主张让雪海上班时顺便帮她带礼服来。
早晚会被雪海给气死,她哪件礼服不挑,偏偏挑这件她为了当大姊伴娘而订制的礼服,穿这件衣服很难走路耶!
沿路行来,她忙着应付高跟鞋,没大多时间想起这款兼容传统与颠覆的旗袍有多引人注目。这袭衣袋传统的是它以旗袍为雏形,发展出一袭另类不脱高雅的无袖低胸礼服,特别在腰后衬一片薄如蝉翼的轻纱,走起路来摇曳生婆,自有一股飘逸的美感,抢眼之余,分外柔媚。然而,她却一点儿也不喜欢。
不愿让同事看到这样的她,无非就怕那些人如同花痴所想,将她的人格贬得奇低,以为她和其它女同事一般,用寥寥布料粉饰并加强自己的信心。倘打大家盛妆打扮纯粹为悦已者容,她没话说,偏偏大家只为博南宫隼这位君王一笑。
搞不懂这些“粉雕玉琢”的女人怎么想的,辛苦化上一、两个钟头的妆去取悦那个女伴犹如过江之鲫的花心男人,何苦?
“是谁口口声声嚷着不来的?”披着鲜黄色薄纱体服,温蝶蝶半露的酥胸为她赢得“酒会之花”的美称,揽尽在场男士觊觎的眸光。
老天,这女人还在呀。“这是妳家,还是本小姐不能有出尔反尔的自由?”倒霉,酒会从三楼延伸到二十五楼,层层人山人海,处处万头钻动,碰到熟识的机率着实低之又低。她挑七楼参观是着眼于“梅组”将迁来此处,欲一探日后的工作环境,哪知肚子里一尾蛔虫先她一步,堵在这儿。
嘿,如此看来,知她者莫若花痴也,赶明儿她若失意时,只消借花痴的肩一叹,烦恼还不立即滚得远远的。
“哎呀,妳快别这么说,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仗势打压妳呢!”温蝶蝶风情万种地啜一口美酒。
脚好痛,先找个地方坐下。啊,有了,吧台就在九点钟方向。
掉头一转,佟澄空碍于旗袍开衩太低,行来不婀娜当真不行。这便是她一看到这件衣服就抓狂的原因,她边叹气边挺起胸膛,终于万般辛苦地抵达吧台。当她气喘如牛地坐上高脚椅,刚向酒保点了杯血腥玛丽,温蝶蝶已随后追至。
“啊,抱歉,没注意到妳喳呼些什么。”除了年龄忌讳,花痴第二件不能忍受的事,便是她唱的戏没人附和,所以她喜欢找她斗气,因为她很好撩拨,一激就上火。
想想,自己还直是没用,不过少了温蝶蝶,倒也无聊,斗气也是一种工作上的助力。
温蝶蝶承认佟澄空姣美的身段经过一番粉饰确实玲珑,夺走不少原属于她的爱慕眼光,但她不会输。
“不经水滋润的花朵,纵使娇艳亦有枯萎的一日。”
老天,开打了吗?这些天吃不饱、睡不好,没力。“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佟澄空娥得前胸贴后背,不必温蝶蝶邀请,径自饥馋地抓来她盘中的肉,啧啧大啖。“不过花的种类有很多种,有些花嗜水如命,得天天浇天天灌溉,开出来的花朵却未必娇艳,徒增花农烦忧。有些花呢一年浇一次水,自行吸取养分,偏偏开得比谁都好。”
怪矣,这小妮子似乎坦然许多,好象不再对这种隐喻“性”的话题避之如蛇蝎,无趣极了。
“总比有些花儿甚至不知道‘水’的珍奇,远胜三分吧?”温蝶蝶试探道。佟澄空向来沉不住气,善良的人说是直率,看不顺眼的连太屌也能骂出口。
好,等她再吃下一片肉,就有对阵的气力了。这回花痴尽管放马过来,小姐她今天有恃无恐,什么都不怕。
佟澄空饿了几夭几夜啊?“唉,水呢,有分好几种。像海水,河水,浊流,山泉,溪涧……
这女人有病,水不就是水而已,哪来那么多废话。佟澄空抬眼看她,皱眉的同时边囫囵吞咽食物,好不容易肚子填饱了三分,她腾出嘴巴,才要开口——
“佟澄空小姐请到十楼贵宾室,佟澄牢小姐请到十楼贵宾室……”大般风景的扩音器一遍遍清晰响起,坏了佟澄空一吐为快的佳机。
杀千刀的死马头,好不容易逮到机会顺顺多年怨气,他居然在紧要关头召唤她!佟澄空合拢嘴,怕自己忍不住咒骂出声。
无论佟澄空改变多少,因何而变,她先上“兰组”是事实。温蝶蝶代佟澄空接过酒保推来的酒杯,塞给佟澄空,意气风发地兀自以杯撞杯,娇声欢呼,“祝我升官愉快,坎拜!”
“坎、拜?”
“唉,从今以后我得开始适应没有妳的日子,好沮丧。哦,嗨,张经理,好久不见。”温蝶蝶一点也不沮丧地拋下连串愉悦笑声,扭着美臀迎上前,迅速消失在佟澄空眼前。
“佟澄空小姐请到十楼贵宾室,佟澄空小姐请到十楼贵宾室……”清柔的声音再次执着地催促。
要连下几道金牌马头才会满意?当她是岳飞啊!烦不烦。
佟澄空放下涓滴未沾的酒杯,拿起盘子夹满菜肴,气恼的边吃边晃向人烟最稀少的楼梯间,拾级而上。
好久没穿高跟鞋,脚痛死了,都是雪海惹的祸。
忿忿踩上十楼,佟澄空初踏上楼面才发现此楼不若其它楼那般喧嚣。纳闷地慢慢拐进室内,赫然发现自己掉进一片壮阔无限的撒哈拉沙漠,视觉交错的瞬间,震撼与感动在佟澄空心灵深处交织、回荡。
怀抱久久无法自持的心情,她呆呆地走进辉映布景的橙色灯束下。早就知道“梅组”有一座室内摄影棚,供其成员学习摄影,却没想到是这般的气派。
“宝贝,慢慢转过身来。”
鸡皮疙瘩掉满地,佟澄空大大地打了个冷颤,回头看见方在摄影机后面移动镜头的人,不禁心生惊悚。南宫隼此时已从镜头后探起身,半边脸沐浴在残弱的光影底,另外半边则完全被黑暗吞噬,营造着某种类似复仇的氛围。
佟澄空惊骇地转身想走。
“甜心,妳真美。”慢条斯理晃到她面前,南宫隼俯身欲偷香,却被怒眼相向的佳人不给脸地挡住。“好久不见,妳想不想我?”他热烈地看她,笑容微微扭曲。
“我很忙,没空。”佟澄空缩回颈项,说得很是应付。不能让他碰到她,他的手和眼神具有麻醉作用。
“这是个适用于各种情况的好借口,不是吗?”南宫隼阴郁地勾起她偏开的脸,眼睛突然被她滑嫩雪白的天然肌肤给吸引。“鲜少看到女人不着妆比着状更美的,妳真是得天独厚的宝贝。”颊边这两络标新立异的红发好香。
脏死了,为了工作她忙得两天没洗头,这位大情人竟然陶醉地埋在她头发里。
“节制点行吗?”她推开他,抿着笑意。为了保持情圣的伟大地位,这人的牺牲想必可
“我很努力在控制了。”南宫隼被她莞尔的表情逗出笑容,亲昵的手指来回刷抚她柔嫩的脸颊,彷佛极爱这样的肤触。
魔咒!不行,她不会栽在这种花心的男人手上。佟澄空冷冷地拨开他的手,俏脸黯沉。
“如果没别的问题,我还有事。”真糟的感觉,全身软趴趴,被他一摸呼吸便急促了起来。这几天乐在工作里,不曾再想起那场无边春梦,真不知他怎么神通广大的知道她在……“是你叫我上来的,不是——”她惊异地看向他。
亦趋亦步跟在她后头,南宫隼环住她的腰,扭身一带。“不是马头。”手指流连地梳理她的秀发,他淡然地说。
“拜托你别动手动脚好吗?”无暇理会悻然疾跳的心,她既急且气,着慌地四下张望,就怕一个不小心成了绯闻中的要角,从此夜夜垂泪到天明。
南宫隼拚命告诉自己,她没有用那种他很见不得人的表情羞辱他,绝对没有。然而他铁青的面容完全不肯被说服,直线上升的体温更是愤怒的具体呈现。
“放手了好不好?”还越摸越上瘾哩。“我还想在这里混到老,不想一天到晚澄清这、澄清那,烦死自己。你懂我的意思吗?”她尽可能缓和自己的语气。
她没烦死前,南宫隼丝毫不怀疑自己会先入坟场,死因是气愤过度导致脑溢血身亡。
“想在我的公司混到老,绝对没问题。”他呕得胸口直发胀。“我可以利用职权替宝贝安插工作。亲爱的,妳想要什么职位?说来听听,我对床伴一向大方。”
这匹种马当她是什么了!佟澄空怒火冲天,二话不说,脱下鞋子狠敲他额头一下。
一时间,额上的疼痛比不上她给的错愕,南宫隼滑稽的表情介于暴怒和匪夷所思之间。
“既然你记性不好,我就再说一次。从下一刻起,你我各奔天涯,互不相识。”她死也不愿沦为他的玩物。
“不相识?”南宫隼阴莺地揉着伤处,疼痛强力发酵,霎时扩散至全身,夹带着一把怒焰。“妳不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妳的行为,或者向我道个歉什么的?”
“解释什么?又道哪门子歉?”她坦然地瞟他。
有耐心点,她不是一个任人揉捏的呢娃娃,她的年纪尚轻。“臂如:妳为什么上我的床?如果妳真如我所听到的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