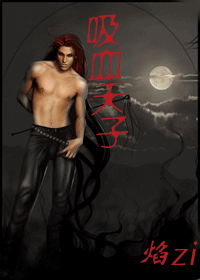赌棍天子-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常侍鲍叔莲白胖白胖的脸笑得出褶子:“皇叔担忧得过了!要说这太初宫台城九门,势力最大的还是大司马门、西掖门、东掖门、南掖门,不都是大王岳家的么?”
皇甫道知神色带着少许的尴尬,勉强笑一笑道:“岳家?孤和太后才是叔嫂,才是一家。”
“极是!”鲍叔莲笑开了花似的妩媚,“倒还要请皇叔下旨,宫禁缺人,以往太子东宫都要有一万武士,现如今整个太初宫不过一万八千而已。太后担惊受怕,唯恐至尊出什么岔子,看来还是要募兵!”
这节骨眼募了兵,名义上姓皇甫,其实却是太后私人的。所以,这点,皇甫道知丝毫不让:“国家征战连年,大家都快吃不消了。中常侍不是没看到北边来的奏报,江陵王皇甫道延自那时逃走,也不顾母亲和家人均在江陵和荆州被擒拿,自己个儿一口气投奔了北燕,当了个什么篡伪的江东王,竟把叛逆做成了叛国!如今北边边界那么样的水火之势,都顾不上增兵,我们这里再增,我怕自己将来要钉在奸臣册里了。”
鲍叔莲笑道:“皇叔先嫌千秋门只有区区二千,现在又何必在老奴面前如此清高?”他的笑容有点寒意,捻着手中的数珠淡淡道:“大王麾下人亦说,千秋门是多事之秋,杨家女郎的事不早不晚偏偏发生在那里,尚不知为何呢!”
皇甫道知琢磨明白这话的言下之意,顿时怒发冲冠:“哪个人如此胡说?”想一想却又明白过来,冷笑道:“莫不是那个满口张狂的赌棍?”
“是不是赌棍老奴不知道。”鲍叔莲低头看了看数珠上的一个结疤,特意好好地多摩挲了两圈,漫不经心道,“人倒是挺老实的。他这几句话老奴甚是费思量啊,望大王善待这个侍卫,万一太后那里要问话呢?”
老实个屁!皇甫道知恨不得现在就把杨寄提溜过来抽死,冷笑道:“这样的人才,孤自然少不得‘善待’,中使的话既然问完了,可否把这个证人还给孤?”
鲍叔莲拊掌笑道:“果然是大王的心肝尖儿,才不过三天,大王就舍不得了。放心,一根头发丝都没有少!老奴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动大王的人哪,这就给大王送来!”俯身告退了。
中常侍不“敢”动,皇甫道知可是恨不得亲手打死杨寄才好,焦躁中好容易看见那个高大而郎当的身影近前,皇甫道知刚见杨寄有要下跪问安的架势,便已经狠狠一脚蹬过去,怒问道:“你当我是你主子么?你敢出卖我?!”
杨寄猝不及防被踢了个窝心脚,胸口生疼生疼的,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莫名其妙挨脚跟,他心里也窝火,干脆坐地上也不起来了,抬头顶撞道:“哦哟,大王好大火气!我哪里出卖你了?不能这么冤枉人吧?”
他这三天一个人被关着又没啥事,除了想想沈沅,就是想想被沈岭逼着看的《六韬》。那日只随便翻了一页读了读,夹生饭一样,这两日无聊时老琢磨,反而咂摸出一点滋味来,此刻正好现学现卖,对皇甫道知说:“‘两陈之间,出甲陈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就是姜太公为周文王打仗,也知道用乱阵晃敌人的眼。赵太后和后宫的人想要什么结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好容易劝得那可怜虫招供,这个乱局是容易造的?”
皇甫道知压低声音说:“那你把我扯进去,我只能对这事睁只眼闭只眼,庾家就不做大了?”
杨寄大大咧咧冲皇甫道知翻了个白眼:“笨!太后提防桓家,再提防你,回头一看,嘁,庾家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到时候是和你这个‘或许有’较劲,还是和真实力的庾家较劲?桓家呢,又码足了力气和谁斗?你犯个若有若无的小错,就可以藏身在草丛里了,让庾家做活靶子,你自己不用挺腰子上赶着去打群架,多好!”
皇甫道知脸青一阵白一阵,既承认杨寄说得有那么点道理,又恨他言语无礼,不言声又是一脚跟过去。杨寄见他用力不大,便侧过身子让胳膊承受了,让这位位高权重的皇叔发泄一下怒火。他夸张地“哎哟”一声后笑道:“下臣不是先就问了吗,是不是要造个乱局,如今不是乱得很好看吗?大王要是信不过,只管把下臣养着,若是我说错了,那时你再杀了我出气。好啵?”
皇甫道知胸口起伏着,冷笑道:“行!哪天太后和桓家打起来了,我就放你和沈沅见面。若是你说错了,我就先打沈沅给你看,再打你给沈沅看!”
这位要不是建德王,杨寄的一个大“呸”外加口水已经要喷他脸上了。杨寄知道皇甫道知心眼窄,最喜欢看他被逼的样子,所以做了一副又惊又怒的样子给这位大王看饱了。果然,皇甫道知心情略好了些,没好气地对杨寄说:“滚吧!”
杨寄“哎”了一声,打个挺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又揉揉自己的胳膊,拍马道:“大王好大气力,下臣这会子还肚子疼、胳膊疼呢!”他又脸皮一嬉,恭敬地向建德王告退了。
他被关了三天小黑屋,心里自然坏得很,好在出来这天是个好天,一路几乎飞奔,流了一身臭汗,才觉得心里的憋屈释放出来了一些。杨寄一路飞跑,脑子清醒地转着,他和皇甫道知,死对头是当定了,但是,两个人总在一局樗蒲里打对门,不合作也要合作。能让皇甫道知觉得还有利用价值,就是他杨寄的保命之本。
到了营房,杨寄迫不及待想和沈岭报个平安,却在门口被曾川逮住了,他把杨寄一拖,拖到个僻静的墙根儿,然后来了个差点勒断他肋骨的熊抱:“你小子,居然活着出来了!”
杨寄几乎透不过气儿来,狠狠在曾川胳膊上捣了一拳,才得以松开,没好气道:“那儿活着出来倒不难,在你这儿活着出来好难!”
曾川笑道:“我还不是担心你!乡里间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回;咱们这里人都知道,一进废东宫,再和鲍叔莲那老妖怪见个面,半条命已经归阎王了。”
杨寄吃了一吓:“不能吧?!那个老妖怪,除了长得妖形,说话妖声妖气,对我还挺不错的嘛。”
“是哈?”曾川笑得不屑,也猥琐,拍拍杨寄的肩膀,“怪不得宫里专程有人过来打听,问你为人如何。”
“你怎么说的?”杨寄瞪圆眼睛问。
曾川道:“如实说咯!说你阳_痿不举,是个银样镴枪头。”
杨寄气得伸手揍了曾川胸脯一下:“你才是阳_痿不举!你才是银样镴枪头!什么兄弟!断送我发达的机会啊!”
曾川笑道:“人家本来就不止打听我这一处,上次那艘花船,你以为人家不问?再说了,你阳_痿不举,才不用上太后那儿伺候——你大概不知道吧,这鲍叔莲怎么得宠的?不就是靠为太后拉皮条才得宠的么?哦,你总不是希望和卫又安一样,以色侍人,爬太后的床,然后发达发达再发达吧?”
还有这茬儿!杨寄愣了愣,终于对曾川笑道:“这么看,你倒是好兄弟。”
“一般,一般。”曾川谦虚地说,然后一勾杨寄的肩膀,“哎,昨晚上与人家赌樗蒲,输个底儿掉。你再指点我两招?”
☆、第60章 政变
杨寄心不在焉敷衍了曾川一会儿,约了下一场樗蒲赌局的时间,目送他喜滋滋回去了,才赶紧几步奔向自己的营房。
沈岭见到他,真是大大地舒了一口气。杨寄要解释,沈岭摆摆手说:“我已经四处打听过了,前因不用讲了。你赶紧告诉我,后来你怎么出来的?”
杨寄便把他进到那座破败宫殿之后的事,包括怎么构陷那抬轿子的宦官,又怎么拍中常侍的马屁,才得以逢凶化吉的事儿都说了,最后道:“我还恶心了建德王那家伙一把,他气得半死,又觉得我有道理,踹了我两脚也拿我没辙。”
沈岭默默地听着,最后说:“搅乱一潭水,你行事还是聪明的。但是,时机未到,建德王和你的对头倒做定了,你以后要多个敌手,不大明智。”
杨寄一撇脖子:“我见到他就恨得牙痒痒!”不过,片刻后又说:“我懂。我还是会忍的,忍到我能跟他抗衡为止。何况,我虽然把他扯进去,对他也未必不是好事。我就是怕,万一将来争夺皇后之位的事情闹大,建德王倒霉,会牵累还在王府的阿圆,所以,还是宁可把建德王摘开。”
沈岭忖度了半日,方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想得也对。不过,世事难料。桓氏被陷,未必乖乖领罚;庾氏独大,未必会自负忘形而不能抓住大好机会;而皇甫道知和赵太后做了鹬蚌相争里的渔翁,却未必斗得过老奸巨猾的鹬和蚌。”
杨寄笑道:“本来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就像我再好的樗蒲技巧,也须对赌场上的命运服气。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见阿圆。等我见了阿圆,和她好好商量一下,再想下一步的对策,能求建德王放我们回去就求,求不到,少不得使其他法子,总不能永远被他牵着鼻子走。”
他说了这一会儿话了,眼睛其实一直盯着正在睡午觉的阿盼,见她酣实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突然想起件事,拍拍脑袋道:“那姓缪的小宦官,招供之后就被处死了,我答应过他,要为他照顾老母亲。说天天膝下伺候,我也分不了身,但是,送点钱去,嘱托个邻居帮帮忙,也还勉强。”
沈岭点点头说:“行善事自然不错。只不过,一切也当有度。”
杨寄点点头:“都是穷人家,我最懂这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苦处。但是,我自己做不到的事,也只能看看了。像那缪家的小宦官,他自己看不透情形,还想赖活着,真是傻透了。但当时,我做出那样的事,自己还是于心有愧的。”
沈岭目视杨寄,面无表情地说:“那么,今日你去长干里找缪家老妪,你可好意思见人家呢?”
杨寄笑道:“没事,我皮厚。”沈岭亦笑道:“就还缺点心狠手黑。”
“心狠手黑?”杨寄愣了。
沈岭摆摆手说:“你去吧,就当我是说了瞎话。”
晚上,杨寄回来,早早地就上榻睡了。一勾月牙挂上窗棂,沈岭在地铺上,听着杨盼时不时发出咂嘴声和婴儿呓语,也听见杨寄不停地翻身,不断给杨盼盖被子的动静。
“睡不着?”他终于忍不住发问了,“是不是阿盼有些吵闹,要不,我来带她睡吧?”
“不用。”杨寄的鼻子有点瓮声瓮气的,好一会儿又说,“不是因为阿盼。”
沈岭默不作声,过了好一会儿道:“阿末,杨朱哭歧路,因其过跬步而觉跌千里,因其可以南而可以北。阮籍茫然,因为没的选;杨朱困惑,因为可以选的太多,生怕自己后悔。你呢,若是没路走,我看你已经选择了赌一条命;但若是有的选,你怎么选?”
这个话题相当宏大,杨寄本来就烦乱得睡不着,这下双手枕头,眼睛睁得更大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想了多久,反正觉得屋子里寂静得连窗外风动柳梢的声音都能清楚分辨。“二兄,”他轻轻说,“没睡?”得到了沈岭清晰的答复,杨寄飘忽难定的心也突然感觉安宁了,他轻叹一声说:“是有千千万万条路,我也不知道哪条是对的,哪条就把我引入歧途,哪条就把我带进死胡同了。但是,反正也没法子后悔了,就像樗蒲的摇杯已经停下了,想再摇两下也不成了,我能选的,也就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