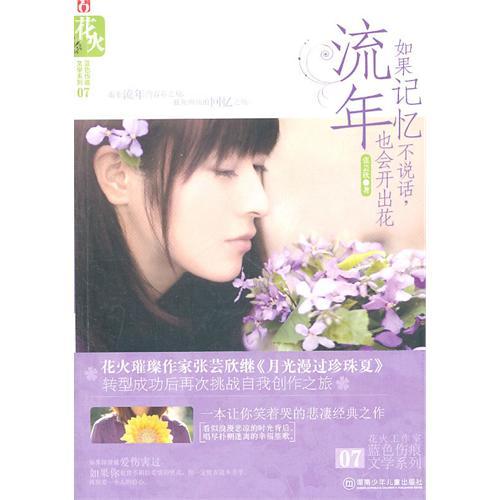四月紫花开-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敲门声响起,盈芳迅速开门,黝黑高大的家志立即进入眼帘。她百感交集下,差点忽略两旁扶得气喘吁吁的智威和宗祥。
“呼!这小子一身精壮,可真重!”宗祥抱怨着。
“你们似乎喝了不少酒。”盈竹闻味道说。
“是呀!他的抗体强嘛!”宗祥笑嘻嘻的说。
智威把家志安置在床上,很不放心地说:“你可不要人虐待他呀!”
“虐待?”宗祥挤挤眼说:“有这么漂亮的小姐,哪叫虐待呢?”
他那暧昧的表情,让盈芳微微脸红。她没好气地将两人推出去,她只是要“谈话”而已,却被恶意抹黑!
“等一下。”关门前,智威交给她一封信,“这是给家志的。他醒来,就让他看。”
室内又恢复寂静,盈芳把信放在桌上,就坐在床边。
三个月不见,家志晒得和黑炭一样,脸的轮廓更坚硬,也散发着更多的男性气息。她几乎看呆了,明白了自己的爱,眼前的他已跳脱英俊或迷人的字眼,只是如逢亲人,有份痴迷,有份感动,到想流泪的地步。
她情不自禁地画着他高高的额头,直挺的鼻梁,柔软的唇,到下巴喉结。平滑温热的肌肤,给她极好的触感。
情绪略定后,她才注意到他一身的脏臭,T恤及牛仔裤都沾着泥块污迹,在洁白的床单上很不协调。
盈芳眼珠一转,唇角露出了一抹顽皮的笑容。他以前曾趁她不省人事脱她的衣服,此刻不正是报仇的最好时机吗?
她愈想愈有趣,于是费尽力气,脱下他的衣物,只留一条内裤在身上。当完成任务时,盈芳的脸又整个绯红。她并非没见过家志裸腿或打着赤膊,但都不是在这种毫不设防的情况下。
外面的夕阳已完全没入山后,四周黑影幢幢,床边小灯所投射的光芒,透着一种柔幻似梦的气氛。
盈芳沉迷于家志的体格之美,那壮硕有力的男性线条,和她如此不同。她再仔细看,上面散布着一些伤疤,手臂、胸肌、肚腹都有。她忍不住用手去触碰,一条条轻抚着,想象他曾历经的争斗和危险,手腕上有一处甚至是她割的。她动作极为温柔,直到腰间,才蓦然而止。
以下是禁区……盈芳的眼光迅速掠过。她在做什么呢?但理智早飞出窗口,她的手依然在他腰际,在一个刀疤上,柔柔按着,像是抚慰。
家志一直觉得自己躺在大河的月亮上。
奇怪!月亮明明在天空,怎么会飘在水面如浮萍呢?这一个思考,刺穿了他迷糊的脑袋,费了一番劲儿,在黑暗中他抓到一条绳索,努力荡呀荡的,终于跨到现实来。
他记起在河边的帐篷里和智威喝酒,然后宗祥也来。他们破例地不禁他酒量,并且神情都有点怪异,智威严肃得过头,宗祥又动不动就乱笑。等他饱了酒虫,想一问究竟,天上又圆又大的月亮就掉下来了。
月亮上果真舒服,那气味、那抚摸,恍如温柔乡……慢着!他不能再沉醉了,除了阿姆斯壮那票人,没有人在月亮上走过,更遑论愉快地躺着了。
他勉强自己睁开眼睛,却看到盈芳!
他立刻闭上眼。这是哪里?比月亮更好,或许更糟的地方吗?她手的动作传到他脑里,该死,她在挑逗他吗?
他的肌肉变硬,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在持续的静默中,他微眯着眼偷看她。三个月的分离,她怎么又变漂亮了?尤其是脸上的红霞,如初绽的玫瑰花瓣……
哦!惨了,她正中他的痒处了!
家志希望她的手不要再停留他的左腰,但她似乎对那儿特别有兴趣。他再也忍不住了,在扭曲爆笑出现之前,他的左手轻按住她的右手。
他醒了!盈芳一惊,想抽身,但家志力道加重,热热的温度包围住她。她又羞又气又急,使出武力,家志猛一翻身,她就被压在床上。
呃!这绝非他的原意,但此情此景,他有一种非碰她、逗她不可的冲动!
“刘家志!放开我!”盈芳挣扎叫着。
“是你绑架我来的。”他说完又加几句,“而且剥光我的衣服,抚摸我的身体,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我……我只不过要报复去PUB的那一晚,你的非礼行为而已!”她急急说着。
“是吗?那一晚我还吻了你,你不也应该吻回来吗?”他将脸俯了下来。
“下流!”盈芳狠狠咬了他的下巴说。
家志惨叫一声,她立刻挣脱他的箝制。
这一下,他完全清醒,用力甩着头说:“老天!他们是给我灌了什么东西?”
“迷药!”她微喘着气说:“谁教你不肯见我!”
“迷药?!”他睁大眼睛说:“太过分了!这是谁的主意?”
盈芳不回答,只递过去那一封信。
家志打开一看,里而两行字迹写着: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善有善报?我中文不太好,只有请老弟你自己做智能的判断了。
智威居然给他来这一招!家志看了盈芳一眼,什么都没说,拿起衣服,就冲进浴室。
这又是哪门子的幼稚举动?盈芳本想追过去骂,但她因方才那一幕,心尚未定,所以只坐在椅子上,愣愣地发呆。
一阵如急雨的冲澡声,像洗不完,又戛然而止。家志走出来时,头脸仍是湿的,身上又穿回原来的脏衣服。
“你为什么要躲我?”她开口就问。
他东张西望,终于坐到床沿,然后才正经地看着她说:“我以为是你不愿意看到我。”
“那是我太生气了,但人总有气消的时候吧!”她又问:“你知道我在找你吗?”
“智威说了。”他点头。
“既然如此,你还不出面,还让大家像无头苍蝇般找你,你觉得这很有趣吗?”她的声音变大。
“出面做什么呢?我说要保护你,却差点害到你。我有罪,不该自我放逐吗?”他说。
“放逐个头啦!你这叫逃避责任!你说过要代替我哥哥照顾我一辈子的……”她说。
“不是一辈子,是到你嫁人的时候。”他纠正。
“我又还没嫁人!而且……而且你这样生死不明,音讯全无,教大家担心,很没道义情分,你知不知道?”她很伤心,但用愤怒的口吻说。
“我早就没有道义情分了!”他低声地说。
“一切都还是为了程子风,对不对?”她更生气了。
他看着她,眼神很怪异,好一会儿才说:“不是为了我义父,而是为了你。”
“为了我?”盈芳心一惊,住坏的方向想,忍不住难过地说:“为了我,躲到这里来?可见你一定很讨厌我,嫌我任性、麻烦、爱颐指气使,你早就想摆脱我这个包袱了,对不对?”
见她快哭出来的脸,家志一时情急说:“不!绝对不是!是我的错!我……我不该对你有非分之想,不该对你有超出兄妹的感情……”
“你……你说什么?”盈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惨白的脸,让家志手足无措。对爱情的方式,他完全陌生,看到茶几上有一把削苹果的小刀,直觉就拿给盈芳。
“你砍我吧!我还欠你十刀,我罪有应得!”
盈芳接过刀,慢慢走过去,内心激动得无法言语。他在乎她,而且当她是能产生欲念的女人,可是这种感觉,有像她一样深切,一样不能自拔吗?
她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本能一闪,两人跌到床上,她顾不得姿势,胁迫地说:“你爱我吗?”
“说真话吗?”见她美丽又明亮的眼睛,他不禁承认说:“我爱你。从一开始写信给你,从你来监狱看我,我就有不安分的念头。这五年来,你一直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我真不知道我们怎能相安无事到今天……”
盈芳的心颤动着,但她必须要确定,刀离更近,手也更痛,她问:“你对我的感觉和敏敏不同吗?”
“当然不同。”他毫不犹豫地说:“她像姊妹,而你……你就像我的心、我的呼吸,放弃了就会生病。”
“程玉屏呢?你说过她秀色可餐的。”盈芳又说。
“是吗?我都忘了,若我说过,那一定是开玩笑。她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如其它女人一样,只是不相干的人。”他有些困惑,顿一下说:“我是不是愈说愈糟糕了?你很生气吗?”
“不!这是你说过最有内涵,最讨人喜欢的话!”她放下刀子,紧紧抱住他说:“我爱你,我也爱你好久好久了!”
“什么?”他一使力,翻到旁边坐了起来。
“瞧你怕成那样!”盈芳又气又好笑的说:“难道你可以爱我,我就不能爱你吗?”
“可是……可是,你应该爱那些名门公子呀!”他说。
“去他的名门公子,他们对于我,连一条虫都不如!”她坐到他面前说:“我宁可跟着你。”
“但我现在一文不值,什么都不能给你。”他摇着头说。
“我不在乎!”她微笑地说:“你到地狱,我也到地狱,而且还要和你同一层,永远不分开。”
“盈芳,你很傻,而我很自私。”他捧着她柔美的脸说:“我无法拒绝这种诱惑,你知道你正把自己送入狼口吗?一只无家无业又到处流浪的狼。”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也是一只狼,而且并不比你善良,谁吃谁还不一定呢!”她仍是那甜美的笑容。
他再也受不了,唇碰到她的,轻怜蜜意地吻着。两人再也不保留爱意及欲望,全身紧紧相合,清清楚楚地感受那灵与欲共舞的美丽。
呀!她就是他生命的故乡呵!
他的唇深入,几乎将她粉碎;那轻移到胸口的手,又令她销魂。由他的急切,她更体会到他忍抑多年的爱,只愿她能给他更多……
这时,房外有人敲门,智威的声音传来问:“你们还好吗?”
家志轻咒一声,放开盈芳。
“我们现在这样子能见人吗?”她轻语着。
他看她一脸眼波流醉的娇态,自然不愿别的男人瞧见,脑筋一动,就牵着她说:“我们由窗口跳出去!”
他们像两个顽皮的孩子,穿过覆着厚厚枝叶的森林,接着就是教会的墓地。在清亮的月光下,形状不一的墓碑,在明暗之间,直立有如僵尸。
“你怕吗?”他温柔地问。
“不怕。”她笑着回答:“一点都不怕。”
于是他们不走大路,行走于坟墓之间。墓碑上刻的都是西班牙文,只有年代认得出来。
愈古老的,碑文、碑面都愈长也愈精巧。他们甚至相拥倚在一块大理石,刻有圣母的墓碑前,仔细聆听四周的声音。
地底的动静并不真切,但有不少来去的小动物。这里一切都是黑黑的,阴阴的,连拂照的月光也不例外。
他们又继续走,难民区已灯火通熄,只有风的呼嚎和几声婴儿啼哭,木屋、泥屋都静立如鬼兽。
来到河边,他们面对那如银盘闪耀的明月,映到满涨溢沸的水上,彷佛一场神舞。
家志由裤子口袋中拿出一条链子,尾端竟是那只订婚戒指。
他说:“我一直都带在身上。”
盈芳将戒指戴回手上,小形钻石在月光下莹莹烁烁,像在诉说你知我知的小秘密。
“我们还算订婚吗?”她轻声问。
“我虽然没有信心做个好丈夫,但为了你,我会试试看。”他说。
“别谦虚了!我也不是个好太太的料呀!”她说。
他笑了,拥住她,缠绵地吻着,直到喘息声掩过流水声,他们几乎不能呼吸,连云和月都静默不动了。
“我真希望此刻就是永恒。”她倚在他怀里叹息说。
“不但是永恒,还超过永恒。”他说。
“超过永恒?可能吗?”她双眸晶亮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