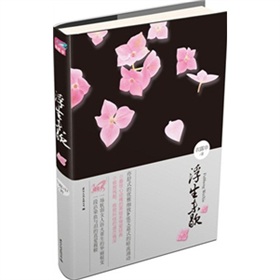眷眷浮生-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小的墓园。
这一路开的时间颇长,驶进莫干山山麓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的时间。这几年莫干山成了热闹的旅游点,国庆长假前就已经有密密麻麻的客车排在山道上,眼睛能看见的大小饭店全部挤满了吃饭的游客。秦捷扭头看看她:“饿不饿?要不要先吃点东西?”于夏晚展眼看到远处一块白底红字的标牌。“乡村旅馆”。她指指那块标牌:“那边偏僻点可能人少,到那儿去吃饭吧。”秦捷依言把车开过去,这里果然稍微清静点,找了个临窗的小桌子,点了几样乡村的野味。于夏晚拎着包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对秦捷说:“这里还有空房间,我订好了,呆会吃完饭你先回老屋去,明天再接我去看沈阿姨。”秦捷看看她没说话,低头吃饭。菜一共点了四样,两荤两素,还有个野山菌汤。不过好象两个人都没什么胃口,放下筷子的时候盘子几乎都还是满的。结帐的小姑娘看着都不说话的两个人,低声问道:“要不要打包?”秦捷扔下两张百元钞票起身就走出店外,小姑娘拿起来对于夏晚说道:“您稍坐一会,找钱马上来。”于夏晚有心说不用找了,又觉得这种说法太嚣张,不是自己的风格,只有坐着等。柜台前站着好几个等待结帐的人,正在结帐的那位极有耐心地拿着帐单一样一样核对计算,对排在后面脸色越来越难看的客人们视而不见。大概等了有二十分钟小姑娘才满脸歉意地把找钱送回来。于夏晚接过钱走到外头,秦捷正倚在车门上抽烟。“把后备箱开一下,我拿东西。”她走过去,秦捷一动不动。于夏晚知道他有点生气,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从苏州出来的这一路上他都没怎么说话。等了一会儿秦捷还是不动,于夏晚低低喊他一声:“秦捷?”“不要住这里,跟我回去。”他没抬头,把烟蒂往脚下一抛,随即从放在车顶上的烟盒里又摸出一根放进嘴里。“秦捷!”跟他来祭拜沈阿姨是可以的,可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再跨进属于秦家的任何一寸土地。那幢老屋她也曾经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陪着她来的,是秦浩。“好不好?”他握着打火机却没有点烟,垂着头,有几绺头发搭在了额上。
“住在哪里是我的自由。”于夏晚不去看他,路边有几个孩子,远远看着这辆颇拉风的跑车,指指点点。秦捷点点头,点着烟,深吸一口。僵持着的时候,秦捷的手机响了,他不动声色地接起来,嗯啊两声挂断,然后拿出钥匙按开了后备箱。于夏晚把自己的大皮箱拎出来放在地下,抽出拉杆:“你先走吧,明天早上来之前给我打电话。我住二楼207房间。”秦捷不答理她,她一个人没好气地拉着皮箱走到小旅馆里,再绕过一堆堆的客人到柜台去拿钥匙。可前台的服务员突然面露难色地对着她笑:“不好意思啊小姐,刚才我弄错了,这间房……现在不好订给你了。”于夏晚啊了一声:“为什么?我订金都交了。”服务员笑得很淳朴:“这个……小姐,喏,这是你的订金,麻烦你到别家去住宿吧,真不好意思了!”“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呀,什么叫现在不订给我了?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啊?”
“小姐……”服务支支吾吾地只是笑,于夏晚生气地对她说:“叫你们老板来,我明明订了房,你说不让我住就不让我住?哪有这种道理。”吵了一会儿老板没来,老板娘来了。她是个富态的女人,和颜悦色地跟于夏晚套近乎,可是怎么说都只有一句,房子在登记的时候弄错了,现在别的客人已经住了进去,实在没办法。于夏晚有些哭笑不得,她也不是胡搅蛮缠的人,看人家的为难样,只得乖乖收了订金拖着行李箱又出来。
秦捷还靠在车门上抽烟。于夏晚觉得有点讪讪的,拉着箱子一步一蹭走到他身边。
“为什么?”一会儿功夫他脚底下已经好几个烟头,指尖夹着的那个还在冒着烟。
“什么为什么?”于夏晚摸不着头脑。秦捷把伸直的长腿收回来:“在我身边,你就不能暂时忘记大哥?你是因为他才不肯跟我回老屋的是不是?”“你胡说什么。”于夏晚脸色一沉,秦捷突然被烟呛住,他反过身子趴在跑车的车顶上,把头埋进胳臂肘里剧烈地咳嗽。于夏晚赶忙丢下箱子跑到他背后轻轻地拍:“叫你少抽点烟,现在怎么有这种坏毛病?”她的手被他反手抓住,秦捷把试图退开的于夏晚慢慢拉到身边,扭过头看着她:“夏晚,我不想一个人,别让我总是一个人。”“秦捷!”“放心,现在照看老屋的人都不认识你,就当是陪陪我,好不好?”好不好?于夏晚又往回抽抽手,他握得死紧,不肯松。自从汽车驶进这座幽静的小山村,眼前的景物变得越来越熟悉,她的心也就跳得越来越快。秦捷瞥她一眼,突然伸手把CD键按开,猛然冲出的噪杂摇滚乐吓得于夏晚全身一跳。秦捷奸计得逞,得意地一阵闷笑。这一冲原本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她长出两口气,看着车停在了一座青砖的院门前。
老式的宅子院门不大又有台阶,汽车开不进去,秦家便在老屋外头修了两间车库。早有照看着老屋的同族乡亲站在车库外头等,热情地把两个人迎下了车。站在院门外,于夏晚有些却步。秦捷不给她感怀的时间,上来拖着手就把她拉进了院门。一步跌回到过去,于夏晚觉得呼吸停滞,她竟忘了自己开始是想摆脱秦捷的拉扯。她死死掐住秦捷的手,象是快溺水的人死死抓住任何一样不让自己沉没的东西。沉没的感觉。原来这就是沉没的感觉。她求救般看向秦捷,却在他的脸上看到了几乎是满意的表情。怎么,把我硬拉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我是如何地不能摆脱吗?“夏晚,你还记得这里吗?”秦捷拉着她穿过第一进院落,站在了内院一株年代久远的桂花树下。于夏晚苦笑,这里发生过太多的事,你让我记得哪一件,又想让我忘记哪一件?
桂花开得正好,香喷喷地,让人饥肠辘辘。秦捷把头凑近花枝深深一嗅:“真香,我还记得,那天你身上也有桂花的香味。”“哪天?”于夏晚有些心虚地跟他搭着话,太沉默太安静了会让她觉得手足无措。
秦捷一副受打击的样子,睁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她:“你是真忘了还是装样子?”
“到底什么事?”他朝她眨眨眼:“世界上真有你这么没良心的人!我的初吻,你都忘了?”
~~~~~~~于夏晚差点被口水噎到,她直眉瞪眼看着秦捷一本正经的样子:“你说什么?谁谁谁……谁的初吻?”依稀有个七八岁的男孩,一脸埋怨地捂着嘴,两道眉毛几乎皱到一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当年的于夏晚也有些红了脸,可仗着自己是姐姐,便硬着头皮去指责:“还有脸说我?明知道我在看吴阿姨摇桂花还杵在这儿挡路?撞了活该!”小小的秦捷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黑黑的短发上还有几朵桂花。老屋园子里桂花栽了好几株,可其他几棵都是火桂,花瓣花蕊苦涩不能吃,只有这一株银桂上的桂花是做桂花糖的好材料。每年桂花成熟的时节,吴阿姨就拿一张洗得干干净净的塑料布铺在树下,然后踩着梯子轻轻摇撼桂花树枝,黄色的、小小的、肥厚的花朵便纷纷象雨一样堕落下来。这个时候眯缝着眼睛站在树下朝上看,浓烈的香气从天而降,从头至尾包围住自己的感觉,能带来好几个带着桂花甜香的美梦。其实她的嘴唇也撞得生疼,她的牙齿可能磕上了他的牙齿,牙床一阵阵地酸麻。梯子上的吴阿姨格格地笑着,小秦捷在笑声中有些站不住脚,扭头红着脸跑远了。跑远了。那个青涩的秦捷。眼前的这个秦捷,跟当年那个动不动就脸红的秦捷,是同一个人吗?于夏晚站在一样的桂花香气里,看着已经不一样的人。秦捷凑过来,紧看着于夏晚的脸颊,摇头叹息:“我在你心目里就这么没地位?轻易地夺走了我的初吻,又这么轻易地忘掉?于夏晚,你很会打击人你知不知道?”“我我我,我哪有!”于夏晚后退一步,头发搔着了桂花树低垂的枝桠。
“还是这样,一紧张就结巴。”秦捷抬手帮她把头顶的树枝拂开,“能让你紧张,我也很高兴了。”于夏晚被困在他和桂花树中间,她再次后悔回到老屋来的决定:“秦捷,你别这样。你再这样,我马上就离开。”她说得一点也不理直气壮,相反地,秦捷的眼中迅速地、理所当然地浮起受伤的神色,仿佛于夏晚是说了什么对不起他的话,仿佛他才是几次三番受到言语挑弄的人。
“我哪样?我哪样了,夏晚。”于夏晚有些恼羞成怒,她用力一把推向秦捷,从他身边挤了出去,直接向出院的方向走去。秦捷当然一把拉住:“好了夏晚,我不再说了还不行吗?”“江山易改,你改不了吃shit……”于夏晚回头一边抽手一边怒瞪,儿时常常骂秦捷的一句话突然从嘴里冒了出来,秦捷没能压住,笑得捂住肚子弯下了腰。于夏晚的怒气也顿时消散,有些讪讪地轻咳几声。晚饭在后院的扁豆架下吃。新摘的蔬菜,卤水点的豆腐,还有于夏晚最喜欢的竹笋烧肉,虽然这道菜也常吃,可还是莫干山里当年的新竹笋烧出来的味道最清香,她吃顺了嘴,一双筷子只在菜碗里扒着找竹笋吃。扁豆是一种可爱的植物,绿油油爬满了架的藤蔓上,满是深深浅浅不同紫色的扁豆和紫白相间的小花,长得低的豆子已经被摘了去,长在架子顶上的豆荚都被饱满的豆粒撑得鼓胀,以前吴阿姨总是等它们全部长老以后收下来晒干留着烧稀饭吃。“你的口味倒是没变,还和以前一样喜欢吃竹笋。”秦捷夹起一块竹笋放进于夏晚的饭碗里,于夏晚扒了一口白饭,夹起这块竹笋轻轻咬一口:“这竹笋烧得比吴阿姨还是差一点,吃来吃去就数她烧得好吃。”“吴阿姨去世了。”一口菜没有咽下去,就苦涩地卡在了嗓子眼。于夏晚看向秦捷,他微笑:“去年的事,我在美国没能赶回来送她的终。不过听说她老人家走得很安静。”“为什么不通知我?”于夏晚再也吃不下了,她放下筷子。“通知你?你会来吗?”“当然会,吴阿姨的事,我怎么也都赶过来。”秦捷又咧嘴笑,这回笑得却有点勉强:“夏晚,只不过错过了吴阿姨的葬礼而已,这么些年,你错过的又何止这个?”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于夏晚心中酸楚难当。吴阿姨是最典型的纯朴农村妇女,善良能干温柔安静,在父母初逝刚到秦家的那阵子,是她给了于夏晚所有的母爱。离开的几年里,她还时常挂念着吴阿姨,可谁知道已经天人相隔。“吴阿姨的坟在哪儿?”于夏晚吸吸鼻子,秦捷递过来一张纸巾,她接着按在了鼻子上。
“就在墓园里,明天咱们一起去祭拜。”晚上住的还是她以前的那间屋。于夏晚手上拎着包,站在屋子当中局促地看着跟记忆里一样的床,一样的桌椅,一样的橱柜,甚至……墙上还挂着那幅照片。三个十几岁的孩子拥在一起,正午阳光下仿佛幸福永不止息。她牢牢看着照片上十六岁的秦浩。他的个头已经很高,张开一双手臂,揽住十四岁的于夏晚,和十二岁的秦捷。照片上的于夏晚晒得很黑,顶着乱蓬蓬的头发笑得呲牙咧嘴,她紧紧贴着秦浩,头枕在他肩上。
此刻站在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