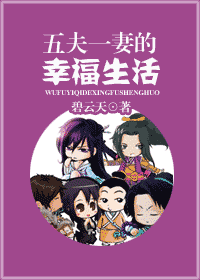平淡生活-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耳光,她挣扎着踹了德子一脚,那神经失控的一脚踹得很重很重,不知踹中了德子
的肚子还是他的下身,德子惨叫了一声坐在地上,地上还躺着凌信诚的母亲。那个
死去的女人看上去只不过四十来岁,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失血过多,脸上的颜色白
如素纸。
李文海这时再次出现在卧室门口,他催了一声快走!然后上来强拉优优。德子
咬着牙爬了起来,和李文海一道硬把优优拖到客厅。优优惊恐地看到客厅的沙发前
面,凌信诚的父亲尸横一边,头中三枪,血溅五步,绛唇半开,双目不合。这恐怖
的景象令优优不敢停步,她懵懵懂懂被李文海和德子扶持着,绕过尸体,走出大门,
一直被他们拽上了那辆红色富康。
优优看到,阿菊已经坐在汽车的后座,紧张地睁着惊惶的眼睛。这回是李文海
亲自开车,德子也仓皇挤进后座,汽车旋即开动起来,在灯光暗淡的林阴道中,急
急地行驶。那个时辰我乘坐的出租汽车刚刚开到瑞华别墅宫殿般的社区门口,正在
接受门卫罗嗦的盘查——这种社区通常只盘查出租汽车,对私家车则有些不闻不问
——当时我隐约记得确有一辆红色富康,从别墅区内放缓速度,稳稳驶出,从容不
迫地在我旁边擦身而过。
如果我当时不是被那两位负责的门卫横加拦阻,我必将第一个目睹那个血腥的
杀人现场。门卫在拦下我后,中规中矩地打电话到我所要造访的住户家中,凌家的
电话当然无人接听。门卫随即公平地告示于我:“瞧,我拨了两遍,都没人接。家
里肯定没人。”
主人不在,客人自然不能进入。我只好站在别墅区的门口,拨通了凌信诚的手
机。这才知道凌信诚正和他家的司机保姆一道,在附近的商场购物。他听说家里电
话无人接听,并未怀疑出了事情。“孩子刚接回来,可能他们都在忙吧,”他说。
他让我在门口稍等,他说他们正往商场的门外走呢。大约十分钟后,我看到了
凌家那辆宽大的奔驰。那奔驰在别墅区的门口,接上我进了大门,直抵凌家别墅。
凌家的门前一片寂静,楼上楼下的每扇窗户,都泄露着辉煌温暖的灯光。司机
停稳车子,又帮保姆搬运车内的货物。凌信诚则领我步上台阶,用自己的钥匙开门。
接下来的情形我不想再多渲染,细述那个场面肯定会让读者生厌,那也是我后
来一直试图回避的记忆,是多次让我半夜惊醒的恶梦。凌信诚那天晚上被送进了医
院,他的心脏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震动。我似乎成了那天晚上最先进入罪案现场的
人中,相对较为镇定的一个,也许只是因为我与死者并不相熟。
司机及保姆开始还试图对信诚的父母进行抢救,但死者的模样让他们几乎不约
而同地放弃了这个幻想。还因为当时更需要抢救的是凌信诚自己,他抱住母亲余温
尚存的尸体,未及哭便昏迷不醒。
在帮助抢救凌信诚之后,我因为相对镇定而第一个想到了报警。警察反应的迅
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对公安机关从此好感倍增。
那天晚上我在凌家逗留了很久,接受调查询问直到凌晨。凌晨两点我被警察准
许离开现场,又乘车赶往爱博医院看望信诚。信诚经过医生抢救,在他短短的人生
中不知是第几次转危为安,我赶到医院时他仍在药物的控制下昏睡。我找医生问了
情况之后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告诉医生万一有事可以找我。
我本想对医生说我是信诚的朋友,开口时转念又自称是他大哥。我这样转念缘
自忽然而生的怜悯,因为我忽然想到,凌信诚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举目无亲。
为了叙述的清晰我不得不遵循时间的顺序,按时间顺序我早该先把笔锋转向那
辆逃之夭夭的红色富康。那富康开出瑞华别墅之后随即放开车速,在夜晚无人的机
场辅路上仓皇狂奔。当汽车开进市区之后,都市夜晚的繁华才让车内的气氛稍有松
弛,车上每个人的心情各不相同,但从表面看他们都已惊魂略定。
李文海把车速放慢,并且开始和后座上的德子交谈。他们在议论今天的战果,
有多少现金,有多少珠宝和金饰……德子说他还从里面书房里翻出一块手表,好像
上面都是自钻,这种满天星的好表,少说也值几十万呢,只是变现不太容易。李文
海说只要是真东西,让利换钱没啥不易,回头看看是什么牌子,带到南方自会脱手。
这时他们都听到了优优的啜泣,李文海说:优优,这些东西也有你的一份,我们本
想早点告诉你的,又怕你害怕不肯带我们来了。我们也是为了你好,这种事搅进来
要杀头的。不知者不为罪,成可进败可退,得了钱有你的份,失了手没你的事。我
他妈处处为你着想,你他妈还委屈什么!
阿菊伸出双手,搂住优优,优优似乎是第一次地,对阿菊温暖的怀抱感到陌生。
她不知道李文海的冷酷无情,还能无情到哪里,而德子与他,干这事是否蓄谋已久
;阿菊对这场血腥屠杀,是和她一样蒙在鼓里,还是早就串通一气。也许那一刻优
优什么都没法细想,她的思维也许还处于休克状态,只剩下少数知觉神经,支配着
张皇无措的情绪。
他们开近一个路口,很触目的,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警车。李文海和德子,一齐
屏气息声,阿菊也全身僵硬,搂着优优的臂膀,禁不住微微打抖。优优想喊,但刚
刚苏醒的一点理性,立即封堵了她的喉咙。李文海把那支手枪,就放在空着的前座!
他小心翼翼地驾车轻轻滑过路口。那辆110 巡逻车不知何故抛锚在此,对这辆鬼鬼
祟祟的红色富康无动于衷。
过了这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危险似乎解除。李文海将车开进一条僻静的
小巷,一直行至小巷的深处,才悄无声息地靠边停住。
李文海关了车灯,看看四周很静,便回头说道:“咱们还是分开走吧,现在警
察晚上总拦车检查身份证的。德子,你先带阿菊下车,今天晚上先别回旅馆,先换
个地方住一宿再说。”
德子犹豫片刻,问:“那你呢,你去哪里住?”
李文海说:“我带优优,我们另找地方。”
德子欲言又止,拉开门刚想下车,动作迟缓一下,又收回身子,试探着再问:
“大哥,这里没人,要不要先把钱分了再说?”
李文海骂道:“你怕我贪了你的!妈的老子要贪早把你一枪崩了,还轮到你现
在问我?我看你这样子永远干不了大事!”
德子不敢顶嘴,忍气吞声钻出车子,阿菊也手忙脚乱地跟着钻了出去。在他们
关上车门之前,李文海又嘱咐一句,或者,也可以说是安慰了一句:“哎,我今天
给你的那只手机可别关了,到时候我打电话找你。”
德子马上殷勤地答应:“嗅。”他正要关上车门,没想到优优突然用力将门一
顶,快速脱身而出,德子刚刚叫了一声:“哎!”优优已推开他撒腿就跑。
优优顺着路灯昏暗的小巷,朝巷口明亮璀璨的大街奔去。她听到李文海急促地
喊了一声:“抓住她!”身后便响起了大力追赶的脚步。她拼尽全力地向前跑着,
头脑麻木双脚发飘,有点像被梦魇压迫,徒劳无功地挣扎逃命。是德子最先追上来
的,他的脚步又急又重,优优先是听到一声咬牙切齿的喉音:“你他妈往哪跑!”
紧接着她的肩部就被用力拽了一下,她身子被拽得一歪,这一歪却让德子意外脱手,
让他不由自主地趔趄了几步。优优也趔趄了一下,但脚步还能继续,德子又追了十
余米长短,还是追上来了,他再次抓住优优的肩头,这一回他抓得很牢很牢,并且
可以用足力气,将优优的整个身体扳了过来。
他当然不会想到,也完全没有防备,优优竟会突然一拳,也许还是下勾拳吧,
击中了他的腹部。然后又是几拳,那几乎是一个精彩的套路组合!那从小看熟的组
合拳优优并没练过,但冥冥之中似有神助,让她突然连贯地做出这样的动作。那第
一个下勾拳实际上已将德子置于无法招架的地步中,而紧跟着的那一组连续的击打,
则让他人仰马翻地倒了下去。
李文海也追上来了,但他离优优还远。优优离灯光通明的大街,只有几十步之
遥。李文海惟一追上来的,只有他穷凶极恶的喊叫:“优优!你他妈今天敢回去,
老子就要你的命,你敢回去我要你的命!”
连这几声最后的喊叫,也渐渐被优优甩得很远,终于连同追赶的脚步,一齐消
失在她的背后。优优已经冲出巷口,冲上大街,她不顾一切地飞奔着横穿马路。马
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纷纷避让闪躲,优优的前后左右,除了飞奔过耳的风声,就是
此起彼伏的笛鸣!
第二卷 第六章
?优优那天晚上真的没回旅馆去住,她在街上一直六神无主,一直徘徊到半夜三
更,心里才稍稍镇定下来,在这之前她只是步伐机械地朝前走着,脑子里依然充满
了血污和枪声。
此刻,她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念头在主导她的神经,是慌张无措还是恐惧
悲伤?虽然,她从没预料自己平凡的人生会遭遇如此惊惊,但却能预料,她刚刚在
凌信诚家从进到出的短短片刻,已经毁了她的一生。
她从东直门内大街一直往前走去,漫无方向。走到鼓楼时又转向南方,一直走
到了故宫的端门广场。她的双腿早已麻木,而意识却渐渐清醒。这时她记得最清的
已不是凶杀发生前后的场面与声音,而是李文海那句最后的警告。他不让她再回她
住的旅馆,也不知是恫吓还是关照。她真的不敢回去了,因为李文海是她带到凌家
去的,所以她对这桩惊天惨案,对凌信诚父母双亡,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她
甚至搞不懂自己今晚的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首犯还是帮凶。
她怎敢再回旅馆,她怕见一切熟人,也怕连累大姐,但此时走在深夜的街上,
她又难以承受心里的孤单。
她也曾想过报警。看到街上缓缓驶过的警车,她几次举手超过头顶,但又缓缓
放下,最终还是恐慌压倒一切,理智屈从于感觉。她完全无法预测一旦她投案自首,
将给她自己的未来,给大姐和姐夫的生活,带来什么后果。她一想到大姐惊愕的目
光,想到姐夫气愤的面孔,就心如刀搅,无地自容。
月光冷冽,树静无风,紫禁城高大的城墙像披了一层冥界的荧装。护城河即将
封冻,近岸处已结了薄冰。薄冰映在优优的眼里,让她从内往外,渗透了寒冷。
她沿着那条冻僵的河水,行至美术馆的西侧,在那里的一个夜间营业的小餐馆
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优优先把电话打到她住的旅馆,她让服务员帮忙去喊阿
菊。她清楚地听到服务员的嗓子在走廊里回响:“阿菊,阿菊,九号房阿菊!”紧
接着服务员又拿起电话听筒,吼了一声:“没在!”然后不由分说随即挂断。
优优再拨过去,说找钱志富,七号房的钱志富。服务员又是一阵叫喊:“钱志
富!钱志富!”然后就没了声息。过了好一会儿姐夫接了电话,听声音像是已经睡
了,鼻子塞塞哝哝,口齿混饨不清,他问:“晤,找谁?”
优优说:“姐夫,我是优优,你刚睡么?”
姐夫说:“优优,有什么事么?”
优优说不出她有什么事情,她也说不清她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事情。如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