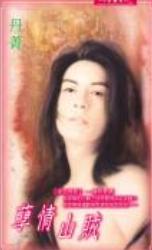太行情-第6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是不是觉得她能够污染咱们家里三代老贫农的血液?”
“我,我只是觉得你和一个不爱你的姑娘结婚不大合适!”他赶忙解释说。
“爱情真的那么重要吗?它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我说话的口气就像要和他谈论这个话题似的,“结婚之前,你可以把她当作一瓶醇香无比的美酒,一旦结了婚,即使是一拼凉水也没有关系,果真如此的话,我为了挽回一点男人的面子,可以不断扯谎道,咱这不是渴了吗?反正不论什么东西一旦到了肚子里就都一样了。”)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正当他开口跟儿子说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却一下子消失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对自己说。
我可以满有理由地告诉儿子,她是我的女儿,你的亲妹妹。
他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白的,黑的,还是红的。如果爱情确有色彩的话,他宁肯相信爱情是红的。因为他属于那个火红的年代。现如今,他老了,应该把所有的事情放下了,以便安详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然而,他确让自己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
他很孤独,自打那次事故之后,他就有了这样的感觉,而且日复一日地啮噬着他的快乐的时光。最后他觉得他得心就像黑暗里的幽灵似的,若有欢愉的话,那也只能是在这样一团白光里独自徘徊。是啊!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快乐,那他的生活也就毫无意义了。简直同死去的人没啥两样。可是,他确让自己感到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
“是的,我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他站在那团白光里大声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了些什么呢?我是谁?一个傻瓜,还是卑鄙的小人?其实,我连自己都没有弄清楚,要不然,我就不会铸成大错,去等着老天爷的报应!”
他继续对着无边的黑暗喊道:“我,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没错,我可以告诉我的儿子说,你知道吗?她是我的女儿,你的亲妹妹!你不能和她结婚!”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难道他真的要把过去那桩不光彩的事情告诉自己的儿子,告诉自己的嫁人吗?他站在那团白光里,对着无边的黑暗大声喊道。如果不说出事情的真相,他能说服那个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儿子吗?就像那一年说服村里人一样。
报应!
报应!
报应!
除此之外,他又能说些什么呢?难道我能够理直气壮地向全村的人们大声说——告诉你们,她是我的女儿。
不,他不能说。如果他那样说了,那么,他大半辈子在红岩村所树立的形象化为乌有,他也将是被人唾弃的对象,可是她是他的女儿。自从他怀疑她是他的女儿之后,更确切地说,那是她瞪着狰狞的目光,并恶狠狠地对他说——呸!别指望这几个臭钱来求得心里安宁!紧接着,便把那些钱摔到他的手里以后,没错,是梅梅提醒了我。很久以前的那件不光彩的事情重新回到他的脑海里。
我真的做过那样的事吗?一连几天,他都是这样扪心自问,但却没有什么结果。
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如果真的做错了,那也只是那个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之所以他不敢面对那双恶狠狠的眼光,是因为自从伟辰死了以后,他的心里产生了对不起伟辰的念头。
如果不是他的儿子执意要和敏慧结婚,也许他心里的所有不愉快过几个月会烟消云散的。对他来说,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现在,他的儿子却使他必须正视那件不光彩的事情,要是他真的能够确定她不是自己的女儿,他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儿子的行为。
她有可能是他的女儿。他没有很好的理由来阻止儿子和敏慧结婚,他更不能把那件不光彩的事情抖搂出来。正因为如此,他觉得生活在无边的烦恼之中,也或者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是的,当我得知儿子对她苦苦纠缠的时候,我便觉得我的报应真的来了。因为我不能阻止他,我的话,对他来说,全是耳旁风。为了不让家里人看到他的不正常的行为,他搬到了砖窑的小屋里。以免他从自己的梦里喊出自己所不希望喊出的事情。
既然他没有理由说服自己的儿子不要纠缠敏慧,那么,他只好等待,让自己耐着性子等待,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所等待着是什么。是啊!那个女人疯了,这是说,她已经不能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来求证她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
无论如何,他都不想把那件不光彩的事情抖搂出来。因此,他不得不默默地喝这他自己所酿造的苦酒。
她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女儿,他一遍又一遍问着自己。更多的时候,他对着自己不满意地大声喊道:“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呢?”
“他是个好人,而我却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他站在白光里大声喊道,“报应,报应啊!”
他走了,我却活了下来,活到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这时候,那团白光离开了他,他的眼光却直勾勾地看着它。
是啊!我的生活不再欢乐了,然而,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着那团白光大声说道——她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知道吗?不仅如此,他也可以对那个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的儿子大声说道——你们不可以结婚,因为你们是亲兄妹。
突然,她的声音重新在他的耳边响起——
不关我的事,是他,是他要我那么干的!
刹那间,那团白光把他孤单的身影完全笼罩住了。
于是,木僵僵的他仿佛被冰封于漫天的风雪之中,因为他的眼光正对着黑暗之中一双可怕的眼光……
★★★★★
很显然,树上的那几只乌鸦对于树下的人们的吵闹声早已习以为常了,因而,树底下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它们都能够镇静而又从容地应付。也或者说,它们原本跟树底下所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所以,它们压根儿不必圆鼓着眼睛去关注随时而来任何意外。总而言之,它们只要保持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那它们原本安逸的生活救不会被打破。
此时此刻,为了避开中午的炎炎烈日,这几只乌鸦不得不隐身于浓浓的阴影之中。一般来说,乌鸦是最不肯安静下来的,但与那些正在树底下吵吵嚷嚷的人们相较之下,它们的确安静许多。瞧!它们正在频频抖动着翅膀,伸长着脖子,转动着脑袋,睒着眼睛,间或发出二三声啼鸣,似乎是什么特别的声音引起了它们的注意。是的,树下乱糟糟的声音的确混杂着两种很特殊的声音,这声音(对于它们来说,真是太熟悉了,就是这样的声音使它们差点成了惊弓之鸟)正不断地传进它们的耳朵里来。
听!那两种有着惶恐感觉的声音又在一起纠缠不清了。
其中的一个声音:“要我说,还是山沟里好!连程皓也是这么说的。”
“那你来告诉我,咱山沟里好什么呢?另一个声音紧接着又传进了它们的耳朵里来。”
“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拿咱山里人来说吧,那一个不是心地善良,为人实在的主儿。”
“哥,快别说啦!什么心地善良,为人实在,亏你说得出口,难道只有这样才算得上山里人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叫傻,傻上加傻,傻之又傻,傻得不可救药啦!”
“照你这么说来,咱山里人救只有当傻瓜得份儿喽!”
“倒也未必,你想想看,咱山里人为什么不能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呢?瞧瞧人家玉良,哪个派呵!哪才是咱山里人真真正正的生活哩!”
“话虽如此,咱山里人总得有个山里人的样子吧!”
“你倒说说看,咱山里人该是什么样子?满脸傻里傻气,满嘴饭菜,满手泥巴!要不然,挎着一篮子鸡蛋到集市上丢人显眼,或为了一只小猪崽的价钱而与长舌妇斤斤计较。呸!真他妈的没出息!”
“可咱毕竟是山里人啊!”
“山里人怎么啦!可我偏要说城里好!哥,你说说看,那搂着老婆睡觉的男人为什么偏偏想着另一个女人?”
恰在这时,周海明便不耐烦地冲着银顺高声骂道:“死不开窍的王八羔子,你干吗不去问问你娘,没准你娘会让你知道,她在搂着你爹睡觉的时候,那心里头所想的那个男人是谁?”
那坐在红崖上面正在吵吵嚷嚷的人们因周海明的响亮的声音而一下子静了下来,可是周海明话音刚落,这些鸦雀无声的人们却轰然大笑起来了。此刻,就连树上的乌鸦也由于众人的笑声而哑哑的叫了起来。
银顺则满脸愚蠢的笑容凑了过来对周海明说道:“海明叔,如今东辉老弟考上了大学,本来吗?是一件好事情,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却很为你担心哪!”
“呸!”周海明脸色阴沉,瞪了银顺一眼,说,“你担什么心?”
“是啊!”金顺也是满脸愚蠢的笑容凑了过来,说,“像海明叔这样有福气的人,还能有啥好担心的吗?瞧!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城里,到了那个时候,说不定咱海明叔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城里人呢?”
“好!说得好!”周围的几个年轻人齐声叫道,“还是金顺说得在理!”
“正因为如此,我才担心哩!”银顺一本正经地说。
周海明怒气冲冲地问:“你担心我做不了城里人,是不是?”
“不是你做不了,而是你做不来。”
“啥意思?你小子有屁就快点放吧!”周海明脸色更加阴沉,很不耐烦地说。
“别急吗?慢慢来,千万不要着急,海明叔。”银顺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地吐了出来。听上去,那声音真像铁板被拖拉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之上,叫人好不耐烦,“照我看来,对于像海明叔这样有福气的人来说,要做个城里人吗?倒也不是难事,只须从今以后,种三四年巴豆就行了。”
周海明不解地问:“我种那东西干什么?”
“当然是当饭吃啊!”
“放你娘的猪狗屁!”周海明冲着银顺高声骂道。
“海明叔,你先别发火,听我说吗?”银顺说到这里,便向红崖下面干涸的河里吐了一口痰,然后,又接着说,“那城里可比不得咱这小山沟里的空气好,实在新鲜,而且还可以随地吐痰,随时大小便;所以我奉劝你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不多的三四年的时光多吃一些巴豆,也好把肚子里的所有脏东西全都吐出来,泻出来,如此一来,才不至于一到城里就忍不住地满嘴喷粪了。”
“你,你……”周海明好像是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四周的人们注视着周海明铁青的脸孔,便只好强忍着笑,最终也没让自己笑出来。
而李金顺则显出一副很会关心人的样子,压低了声音对海明劝慰道:“海明叔,你干吗这么憋着?这样的话,好端端的人会憋出病来的!”
“你,你他妈的说得好!好!说得好!”周海明双眼喷着怒火,“要是我手里有鞭子的话,那我就狠狠地抽你,你们这两个王八羔子!”之后,他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周海明的笑声把在场的人吓住了,于是,所有人的眼光全都呆愣愣地望着周海明。
可是,突然之间,年轻的人们还是终于冲破了可怕的沉默而迸发出最响亮的笑声。瞧!树上的乌鸦也因为人们的笑声而哑哑的飞去了。
正当人们纵声大笑的时候,周海山却一声不吭,使劲吧咂着旱烟卷,就好像他压根儿没有听到人们的响亮的笑声,这时候,他转回头看了看明堂,又看了看胜坤,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也像他一样没有理会众人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