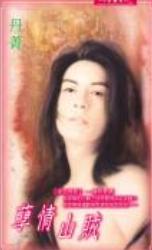太行情-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受扁担的清形。是的,我曾经无数次地歪歪扭扭地适应它,有如遭到风暴袭击的帆船在波峰浪谷之间寻找自己的平衡点。后来,我习惯了,而且能够像大人们那样通过肌肉的颤动来调节扁担的平衡。
我觉得,我长大了,因为我完全是大人们的样子,挑着满满的一担水,很自信地走着。
此时此刻,那种自信似乎消失了,我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扁担的前端,我的双脚似乎是找不到平衡位置了,至少我觉得自己行走在一只颠簸的小船上面。尽管如此,我还是使自己适应了平淡的乡村生活,因为几天以后,我重新找到了曾经失去的平衡。换句话说,我再一次很平稳地挑着满满的一担水行走在乡村的小石子路面上。
无论我怎样坚持,舅舅还是不让我同他们一块下地劳动。他说:
“城里人是经不起日头晒的!”
“我是不怕晒的,舅舅。”我说。
舅舅对我笑道:“我可不愿意你变成黑不溜湫的模样。”
“我喜欢黑皮肤的人,他们非常健壮。”
凭我怎么说,舅舅还是不让我下地劳动。因此,我帮着舅妈做些家务活。说实话,我笨手笨脚,经常是越帮越忙,而使舅妈不得不重新收拾一番。面对如此情形,我惭愧极了。然而,舅妈并不责备我,反而满脸笑容地安慰我。她总是一边忙着家务,一边用一种非常耐心的口气说着她的心里话——
“程皓,你还是让我忙吧!一般来说,我用不着下地,除非地里的活真的忙不过来。我一直操持着家务。乡下人的家务大,有些时候,并不比地里的农活轻闲,每天的三顿饭,喂猪喂鸡,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还有给牲口添草加料。不管怎么说,这忙里忙外的家务活,我都习惯了。反正,我们乡下人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没完没了地忙这忙那!”
这一天,我又挑着水桶向村里的水井走去。等我来到那里,我看到一个年轻姑娘正在摇着辘轳打水,因此,我站在旁边等着,反正我并不着急。
是啊!我来到舅舅家一个多星期了。我已经习惯了跟村里人们打招呼。虽然还有好多人我不太熟悉,但是他们都知道我,一个来舅舅家的城里人。
就像在等待之中体味某种乐趣似的,因为我见到过那样的场面——每天晚上收工回家之后,那些干了一天活的男人们,女人们,还有大一点的孩子们,他们总是挑着水桶来这里打水。一个接着一个,说说笑笑。那些不太着急的人们则干脆坐在河边的条石上面,信口开河地说一通自己想说的话。
这些实实在在的乡下人可以为了一句话,或者一件小事而争论的面红耳赤。要知道有一些人则是刚刚从地里收工回来,并没有把手上脸上,以及全身的疲劳清洗掉,就匆匆忙忙地挑起水桶来到这儿,以便争论当天,或是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如果他们开口的话,就会找得到争论的话题。也许这些话题对于城里人来说,不屑一答。很显然,对于所有这些争论不休的话题,他们并不需要得到正确的答案,而只是他们愿意把自己想说的话统统地说出来。
没错,乡下人争争吵吵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为了一些琐碎的小事,弄得双方面红脖子粗,甚至于见了面如仇人一般。话虽如此,他们还是差不多天天要见面的,因为他们每天都挑着水桶来这里打水,转动着辘轳,把水从井里打上来。
反正我不着急,再说,眼下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人来挑水。
因此,我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她把水提了上来。也许是由于我第一次单独跟乡下姑娘在一起,而且我也不习惯在姑娘的背后和她打招呼。她终于抬起头来,似乎惊愣了一下,并缓缓地说道:
“程皓哥,是你吗?”
“是的。”我努力回想眼前这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姑娘。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姑娘的眼光里充满了失望。
这个身材颀长的乡下姑娘,衣著朴素。一眼看去,却显得俊俏美丽。那双黑亮亮的大眼睛,宛如清澈无比的池水,闪烁着稍纵即逝的波光。更确切地说,她的眼睛太迷人了,因为它们能够给所爱的男人带来一个丰富多彩的爱情世界。
但见她伸出一只被太阳晒黑的手把额前散乱的秀发向旁边拢了拢。她静静地看着我,就好像正在观赏着名人字画似的。
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我的心就像一张七弦琴似的正在被一双温柔的纤手轻轻弹拨。
“你是……”我迟疑了一下,说,“你是敏慧!”
“是的。”她说,“我是敏慧。”
“你真的是敏慧?!”我惊喜地喊道。
第七章
我总是说,如果硬说我是个狼一般凶狠无情的人,那么,就算是吧!我还是要说,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世人可以痛骂曹操是个遗臭万年的奸贼,也可以盛赞他是个流芳千古的豪杰。我呢,只不过让自己稍微自私一点吗?
反正,李玉良只是依照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着。这时候,他的母亲开口说道:“你觉得东民这个人咋样?”
“你真的同意他们的婚事?”他不屑回答母亲的问题,而是向她反问道。
她把儿子的话琢磨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只是不明白你妹妹看上东民什么了?对于你妹妹的心思,你总该知道吧!”
“我知道什么?”玉良冷冷地说,“我只知道东民爱的是敏英!”
“听你宝花婶子说,东民没有喜欢过敏英。”她看了儿子一眼,说。
“是么?”玉良用最恶毒的口气说,“东民是红岩村少有的好人,喜欢帮着漂亮姑娘干活!”
“你这话什么意思?”她不解地问。
“我只是实话实说。”他并没有看她,就好像她这个人不存在似的。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道,“无论什么事情,她都有自己的理由。”
“你们啥事都不和我们商量。”她低声嘟哝道。
“或许她想把东民从敏英那里抢过来。”玉良说。
“要是那样的话,”她终于提高了嗓门,说,“就让东民见鬼去吧!”
玉良冷冷地看着母亲,说:“她能听你的话吗?”
她没有说话,只是叹了一口气。于是他说:
“如此看来,你只能同意这桩亲事啦!“
“可是,你爹的意思……”她说。
没等母亲把话说完,玉良便离开了她,因为他非常讨厌听母亲罗罗索索讲一大堆关于父亲的事情。
财大气粗。
钱多了,玉良越来越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像他妹妹执意要嫁给东民似的。是啊!我放弃了高考的机会,也可以说,我没有上大学的福分。村里人感到惋惜,在他们看来,我是考大学的料。
依照玉良的说法,那是他父亲的缘故。
走出校门的我,活像一只快活无比的小鸟,没错,他原本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他总是说,他只是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十足的胆小鬼,而且喜欢摆出一副可怜相,以便博得村里人的信任,尊重。干脆地说,他压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
长期以来,李玉良一直依照自己的个性来塑造自己,而且他总是对自己说道:
“让我去接受傻瓜们的命运,呸!我就是要与他不同,决不容许他按照自己的的可怜相来塑造我!”
要说玉良是个斤斤计较,睚龇必报的人,那是因为我不断培养着自己的自尊心。就算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傻瓜蛋吧!
在学校,同学们想方设法满足我的自尊心。他们总是说——你是我们的大哥,我们全听你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习惯了对我毕恭毕敬,连在我背后说三道四都不敢。
反正,我自有办法惩罚那些对我贰心的家伙。
实际上,李玉良是他们心目中的曹操,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们已经习惯听命于他。譬如说,报复某个同学,或是戏弄另一个同学(甚至于老师),他都能操作得恰到好处,不露痕迹。
他认为,他有着非凡的才能。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使学校里的大笨蛋名列前茅。
老师夸奖坏学生,惩罚好学生。应该说是我最擅长的把戏。
当时,他还是一个满不错的初二学生。除了对判别式感兴趣之外,对溶解度的概念具有先见之明。他曾经很认真地向物理老师说道——阿基米德先生的确是个辨别假货的高手。
PH值等于7。我总是说,化学老师眼睛的PH值小于7,因为他那双酸溜溜的眼光老是在女学生的脸上流来流去。他妈的,准是个想媳妇发了疯的家伙!倘若他把那个拐腿砍掉,换上假肢,或许有位独眼的傻妞看上他哩!
他认为,同学们崇拜他,是因为他比他们更容易记住和掌握那些令人头疼的知识,如果我拿出听话学生的功夫,就会记得住许多唐诗,宋词,以及那些之乎者也的文章。
他一直不习惯在老师审视的眼光下回答各种问题,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相当愚蠢的行为。
呸!听话的学生。把自己弄得像罪犯似的。在我看来,老师们大都喜欢学生出丑,然后,由他们现身说法,以此点化不开窍的傻瓜蛋。无论如何,灰溜溜的感觉太叫人扫兴了。虽说我依旧是接受教育的学生,但是我瞧不起他们,就像我瞧不起他一样。
因此,在学校,我不可避免地接受着他们指指点点的命运。甚至于在如此严厉的眼光注视下,我无可奈何地背诵着——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就像注定的命运,我必须习惯她那冷若冰霜的脸。她从来没有笑过,自从那小子进城以后,她的心像是深埋于南极洲的冰川下面。即使烈日当头,也休想解冻。
看得出,那是一副天生不求人的脸孔。从一开始,你就得忍受她冷漠的神态,既不能面对它,又不能摆脱它,活脱脱一个紧箍咒永远勒在脑袋上。她的冷冷的眼光如同唐僧那几句神秘的咒语。不久以后,我的自尊心活像一枚鸡蛋被千钧巨岩压碎了。
看上去她像是跟什么人赌气似的,她痛下苦功,让自己的全部身心淹没于XY的关系之中,
厚厚的坚冰。她的脸带着无法摧毁的面具。那可怕的冷漠正像漫长的冬夜一般。
她看着我。
就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是的,她碾碎了我男子汉的自尊心。在她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善于低三下四的小瘪三。
从火里逃出来的人虽说满脸狼狈相,内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该死!该死!
可怜的倒霉蛋。硬是离开荆州,跑到了麦城。
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记得,而且永远都应该记得——那是小学三年级的事情,他终于和那小子干了一架,正因为他无法忍受那小子开心的样子。
她笑了。
对着那个小子笑着,而且笑得非常开心。他却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
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着。最后,他把那个讨厌的家伙压在下面。而当她试图拉开他的时候,那小子狠狠地咬了她一口。
她的手淌着血。
她没有哭,而是静静地看着他脏兮兮的脸。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她似乎跟那个小子更加亲密了。
我只能站在远处,看着他们两个人开心地笑着。
如果我是那个放下经卷的和尚,就不必让自己像观看电影镜头中欢乐场面那样。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的整个心思老是围绕着他们,正如一条没出息的狗不停地打转。
在她面前,我男子汉的自尊心变得一钱不值。我清楚地记得——初三期中考试中,我取得了班上的第一名,她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