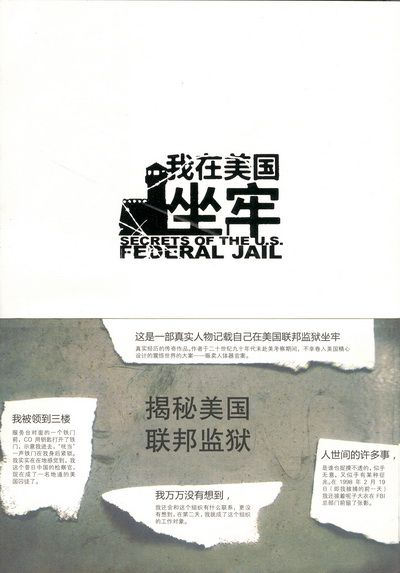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广泛信仰的真理,常常会随着时间成为谬误。简单的真理是索然无味的。太多这样的真理就会使真理失去其纯度。所以,一旦知识分子把握了确定的真理,马上就会变得不知足。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追求新的不确定性。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一种能够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
事实上,Hofstandter的上述两段话,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性两个层面。“为思想而活着”几乎把知识分子定义成了先知:知识分子成为启蒙主义击败了宗教传统后的现代社会中的牧师。而“游戏性”则描述着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固守传统价值的宗教形成截然的对立,暗示知识分子能够以其绝无仅有的探险精神指导人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这样的承担,并非没有原因。现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上的。但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二战”后,知识分子特别感到自己对专制主义的责任。如汉娜·阿伦特等等,穷其一生之力探讨专制主义的起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即所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作为世俗的牧师,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权力抗争,就对这一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知识分子常常觉得自己超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用自己的知识和道德判断,指导“下面”的各个阶层和集团的活动,把人类带入健康的轨道。所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动笔,就是人类未来、自由的前途、通向被奴役的道路等等包罗万象、高瞻远瞩的大题目。其中布鲁尔·二世(BertrandRussell)1963年的一段话非常典型: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他们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权。你,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将被少数几个残忍但有权力的人的共同决定所消灭。为了赢得这几个人的欢心,所有私人的感情,公共的希望,艺术、知识和思想的成就,以及以后可能有的成就,都将被永远地清除。”
今天你要是听人说这种话,你恐怕会觉得这个人喝醉了。但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他们对政治权力非常警惕,把自己看成是与这种邪恶的政治权力抗争的社会良心,是世界的最后拯救者,言行举止,充满了烈士般的英雄主义。
桑塔格正是被这样的传统所塑造。严格地说,她不是一个原创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的文化普及性作家。这样类型的作家,在世家子弟垄断大学的传统精英社会地位并不高。但19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小民百姓的子弟纷纷拥入大学,挑战传统的WASP(昂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阶层的世袭统治,拒绝因循既有权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反叛,造就了桑塔格的社会基础和她的成功。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2)
桑塔格的一系列公共行动,都代表了这一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新阶层的心声。比如她先到越南反对“越战”,成为左翼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但当人们已经把她定义为左翼人士和反共力量的敌人时,她又在1982年公开谴责波兰的戒严法是“戴着人的面具的法西斯主义”,让一些虔诚的左翼找不到北。1989年以后,当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全面推行国家社会主义时,她到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帮助组织抵抗运动,冒着实实在在的生命危险。她的作品,特别是“反对阐释”,预见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乃至匈牙利小说家贡扎ArpadGonz,在苏东解体后作为匈牙利总统访问美国时,出席白宫的宴席时特别邀请了桑塔格。
1989年,桑塔格作为美国笔会的主席,公开谴责伊朗悬赏追杀作家拉什迪。当时一些签名声援拉什迪的文化界人士在伊朗的威胁下已经开始恐惧和动摇,一些相关出版商和书店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但桑塔格的勇气则使西方文化界最终能够把自由主义的理念贯彻始终,对抗专制的暴力。无怪一些人士指出,伊朗宗教领袖悬赏跨国追杀一个“异端”作家,这是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的前奏。桑塔格是最早与之对抗的人之一。但是,在“9·11”后,她作出即时反应,称美国的媒体充斥着“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并说“9·11”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政策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如果要用“懦夫”一词的话,就要用在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在人家无法还手的距离杀人的人身上,而不是用在那些为了杀人自己也把命赔上的人身上。她呼吁公众反省美国的政策,而不是为廉价的爱国主义所蒙蔽:“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如笔者在《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当时的环境,使这样的言论很难被容忍。桑塔格本人立即受到舆论的围剿。ABC著名的晚间幽默谈话“政治不正确”的主持人BillMaher在9月17日的节目中重复了类似的言论,马上引来大公司撤消对该节目的赞助,被迫出来道歉。不久这个节目也关门。好在桑塔格是独立撰稿人,又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声望,没有人能够解雇她,文章还可以照发。
“二战”后,萦绕于对极权主义和战争的记忆,西方的知识分子,如萨特、罗素等,从书斋走向街头进行政治抗议,希望给社会提供一种道德的声音。桑塔格多少秉承了这一传统,成为反叛运动的一个偶像。不过,19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60年代的大学生,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享受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在里根主义之下,社会趋向保守。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从“主义”转向“问题”。那些出来为人类指引道路的,会被嘲笑为自以为是。所谓超越具体社会集团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被称为是一种“神话”。所以,桑塔格本人也不愿意自称为知识分子,而宁愿说自己是一位小说家、散文家。另外,多维媒体的迅速发达,使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再难垄断公共话语,她起家的《党派评论》因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关门。桑塔格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桑塔格不喜欢被人贴标签,不仅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也拒绝说自己属于1960年代。但是,观其言察其行,她是地道的1960年代知识分子的化身。她有着那种先知先觉的道义承担,拒绝被“左翼”“右翼”之类的标签所化约,保持独立的思想和立场,并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贯批评者。她属于笔者所谓的“波希米亚”式的独立不羁的文化人。
但是,到1980年代以后,她的读者,即1960年代的波希米亚式的不羁之士,率先结束了
“流浪”和反叛,在社会上安顿下来,成为“波希米亚中产阶层”。她却继续游荡。她没有博士学位,只能在大学临时代课,作独立撰稿人,日子颇为清苦,直到1990年代经济条件才有所改善。不过,那时她早已疾病缠身。她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向死刑宣战。这样的经历,使她在其读者已经成为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后,还能保持1960年代的反叛者的视角。说她是1960年代的绝响,恐不为过。
桑塔格之死,对中国的震动似乎比对美国还要大。这多少反映了她代表的那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情怀和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共鸣。在美国,左翼媒体对她虽然赞誉有加,但右翼媒体则几乎不置一辞,仿佛她已经是个过时的人物,不值得一提。客观地说,桑塔格取得了某种世俗的成功,享受着一个知名作家的盛誉。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看到了她的运动的失败。她究竟能够留下什么知识遗产,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是,她悲剧性的失败,多少反映了她这代知识分子的限制和弱点。
第一,知识分子是否能够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是否能够超越其他利益集团和阶层而有一种更具前瞻性的知识和道德特权、为人类提供方向?从美国草根民主的脉络看,答案是否定的。应该说,现代西方社会确实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上。那时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扮演世俗化社会的牧师的角色。但是,那些启蒙思想家,是旧的等级秩序生产的精英。他们所提倡的启蒙精神,是建立一个不同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来行动的平等社会。当这样的社会真正建成、公民能够根据自己的理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就用不着别人来启蒙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启蒙主义的胜利使启蒙者变成了多余的人。所以,桑塔格们的声音,早已被多元媒体中发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声音所淹没。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3)
第二,面对这种多元、平等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公共性寻找不同的渠道。桑塔格自称从来不在乎、也不看别人对自己的评论,但实际上她看得颇为认真。甚至有人说她在自我推销上精明过人,并且一直非常成功。她喜欢站在启蒙的殿堂向世界发布自己的宣言。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有时要向公众释放试探气球,见势头不妙就会改变立场,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她曾赞扬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1935年为纳粹制作的宣传片《意志的凯旋》。后来又修改了立场,开始攻击LeniRiefenstahl。她还宣称“白种人是人类的癌症”,后来又收回成言,因为那等于污辱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癌症患者。即使是在“9·11”后勇敢的言辞,也有明显的失误。她质问为什么公众不注意美国依然对伊拉克进行轰炸,等于像布什一样,把“9·11”和伊拉克联系在一起,虽然目的是截然相反的。
这一“社会良心”的自我意识,使她坚持站在社会之上,迷恋自己的公共知识权威。但是,长久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等于让自己脱离了社会,不知道社会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时,抢占能够俯视世界的道德高地,容易让人忽视社区的政治生活,忽视和基层社会的联系。而这也正是保守主义近年来的成功之处。美国的公众,大多数还是听信社区教堂中的牧师,而不是桑塔格这样超越基层社会的启蒙牧师。因此,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虚渺。《党派评论》即使仍然在世,其5000个精英读者也不足以转化世界。
在一个知识权威的分布越来越均质化的高科技、高教育的平等社会,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恐龙。人们要解决的是具体社区内的技术性问题,并对周围的人的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把自己摆得太高、太超出常人,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圈子知识分子”,只在自己的同仁中有些号召力。在这个意义上,桑塔格之死,并不应该仅仅触发我们的怀旧情绪,而更应该刺激我们思索:在这样一个非先知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具体地介入社会生活,重新建立自己的英雄主义精神传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1)
被称为“冷战”的“总设计师”的乔治·凯南,在享有101岁的高寿之后,终于撒手人寰。他的去世,不仅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