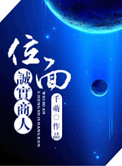患难与忠诚-第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看不出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赖克特说道,“至于线索么,如果你们把它叫做双股线,并且它的一端目前就在这个房间里的话,那么你们也错不到哪儿去。啊,女主人,我真奇怪你会坐在那儿装模作样。”
“天哪,原来是这样!”女主人的面孔变得和仆人的面孔几乎一样红,“原来是我把这傻姑娘赶跑的呀。”
“你有你的一份,女主人。她上次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招呼她的?你以为她会看不出吗?再说,她又没有朋友,孤孤单单的。你说:‘我已经改变主意,不打算画你了。’你一边说还一边把鼻了翘起来对着她。”
“我没有翘鼻子。我的鼻子不像你的鼻子是天生朝天长的。”
“啊,至于说这个么,我们每个人的鼻子都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长就怎么长。可怜的姑娘。她还走进厨房来看我。‘她不打算画我了。’她说道,眼里含着泪水。她也没多说。但我知道得很清楚她是什么意思,因为先前我就瞧见你们在讲话。”
“好吧,”玛格丽特·范·艾克说道,“这些我都承认。太太,我现在请您当个裁判。您知道这些年轻姑娘什么有独创性的东西也搞不出来,而最惯于模仿她们心爱的人搞的东西。你们的杰勒德对许多东西都相当擅长,其中包括饰字画的技艺。玛格丽特是他的学生,而且是个有耐心的学生。多美的事呀。既有女性对色彩的鉴赏力,又有个所爱的人可以模仿。但那玩意我打心里瞧不起,因为伟大的色彩艺术应该是意境清高而洒脱,但被这玩意一搞,便成了书法和印刷的可怜的奴仆,被禁铜,被搞得形体与精神都很渺小,以迁就那些书籍的渺小,并被有钱的蠢人装进口袋走进教堂。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大家都受感情的支配。每当那可怜的姑娘带着她那些长刺的叶子、百合花、常春藤、悬钩子。瓢虫、蝶蛹,以及大自然的一切糟粕来看我,我的确感到很生气。她把这些东西像黄蜂粘在蜂蜜罐上似的牢牢贴在金箔上,并且还带着她的日常画册,说明她每一页都花了一百、一百五甚至两百个小时。那么多小时的劳动,那么多的手艺竟浪费在大自然的糟粕,诸如树叶、昆虫。幼虫和干巴巴的字母这一类的东西上。不过人都有心肠,所以我勉强抑制住,或者说抵制住我内心的感情,而同情地瞧瞧她的作品,看如何能给它们做些修改。我说:‘既然上帝因为我们的罪孽注定我们要花时间、心血和颜料来画大字母和小甲虫,而忽略圣徒、英雄一类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业绩和豪情,那么干吗不把那些蹩脚东西画得自然些呢?’我告诉她,‘我在外面走的时候看到的葡萄都是悬在空中的,不是粘在墙上的。即使这些昆虫以及大自然的其他丑类,也并不是造孽地被夹在金属制的监牢里,像苍蝇在蜂蜜罐和胶水罐中那样度过它们可憎的生命,而是爬着或自由地在空气中飞翔着。’‘唉!我亲爱的朋友,’她回答说,‘我现在懂得你是什么意思了。但这是金底,在这上面我们没法打阴影。’‘谁说的?’我问道。‘教这手艺的人都这么讲的,’她又回答说,并且(我想是打算马上封住我的嘴)补充了一句,‘是杰勒德亲自说的!’‘那我就要做给杰勒德本人和他那帮子人看看。’我说道,‘给我把画笔拿来!’
“为了给她的水果和小爬虫画上阴影,我选了一种尽管在自然界里显得很不自然,但对那难看刺眼的金底还显得比较自然的色彩,只花了五分钟就画了一串连叶带茎的覆盆子,看起来就像要飞进你嘴里似的。同样,我还给她修改了一个蝶蛹。这东西她画得那么逼真,能使胃口最健康的人倒胃。我的好姑娘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说:‘啊!太好了!’”
“是吗?”
“多可爱的小姑娘!”丹尼斯终于想法插上了一句。
玛格丽特·范·艾克瞪了他一眼,然后微笑起来。接着她又告诉他们她怎样一步步地被玛格丽特吸引住,竟然同意重新拾起她兄弟死后她可惜地闲置起来的艺术,准备再次画圣母像——以玛格丽特为模特儿。附带说说,她甚至无意中说出姑娘们是怎样一画就成了圣徒的。“我说:‘你的头发很可爱。’她说:‘才不哩,我的头发是红的。’我说:‘不错,是红的,但这是多美的红色!多美的褐红色!多么富于光泽!大多数人的头发对我们油画家来说分文不值,但你的却正是画家要找的那种色调。你那紫罗兰色的眼睛原来还有点世俗气,现在却时而因失去杰勒德而哀怨,时而因企望杰勒德归来而燃烧,我有办法把它们表现为在圣洁的沉思中仰望天空。你的鼻子已经有点翘望天空了(不过还不像赖克特的鼻子那样虔诚),我会把它们画得稍低一点,同时把你的下巴画得平缓一点。’”
“把下巴画平缓一点?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女士,你简直使我莫测高深。”
“这下巴是个显示意志坚决的下巴。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说来,倒一点也不嫌过分,但要画圣母像怎么成呢?对不起,这可不成。”
“真没听说过。显示意志坚决的下巴。”
丹尼斯叫道:“真是个好姑娘!”
“现在问题出来了,当你告诉我她已经——她的情况使我大吃一惊。我放下了我的画笔。难道我打算在我这个年纪把一个不能回避情欲的姑娘画成纯洁的圣母吗?我仍然喜欢这可怜的傻姑娘,但我更敬爱我们的圣母。你会说:‘一个画家在这样一些事情上不应该挑剔。’不过,你要晓得,大多数画家都是男人,而男人都是好样的。他们什么都干得出。他们的圣徒圣女,恕我冒昧地说,都不多不少正是他们的情人。但你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一半艺术在我身上都不起作用,因为在他们画的小天使的白色翅膀下面,我所观察到的恰好是我曾看见在街上招摇过市的一些烂女人,满身珠宝,就像一个异教徒的木偶,穿戴得像一副纸牌里的王后。而我不是一个好样的男人,我只是一个女人。我的画只有一半是技巧,另一半是虔诚。现在你们可以理解我了。这可能是愚蠢的,但我没有办法。不过,我还是感到遗憾。”到此,年老的贵妇人便很感失望地结束了她以毫不在乎的口气开始的这一番辩解。
“女士,”凯瑟琳说道,“您当然清楚,也一定想到过,既然这姑娘那么喜欢您,您准会使她伤心。”
玛格丽特·范·艾克只是叹了口气。
那佛里斯兰姑娘不耐烦地咬了一阵嘴唇之后,把脸转向凯瑟琳说道:“太太,难道您以为仅仅是因为这个,玛格丽特和彼得才离开塞温贝尔根的吗?事情可不是这样。”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什么别的原因?哼,因为杰勒德一家人那么冷酷地瞧不起她。谁愿意生活在把自己的孩子赶到意大利的狠心人中间呢?而他走了之后,他们还不后悔,硬要做到底,从来不肯接近他那被遗留下来的爱人!”
“赖克特,我本来是要去看她的。”
“啊,不错,说要去,要去。但你应该要么少说些,要么多做些。你用你的话使她的心飞上了天,而你又用你的行动使她的心一落千丈。‘他们从来没来过。’可怜的姑娘叹着气对我说。好在总算有一个人能够同情她,因为我也是远离我的亲人。我刚来荷兰的时候,经常一个人躲起来痛哭。但我还是十倍地宁愿我仍然是赖克特,在我和我的亲人之间只不过隔着一个漫长的距离,也不肯像她那样置身在本应对她热情的亲人中间,却生活得跟我一样孤孤单单。”
“哎呀,赖克特,昨天我还去找过她。以前我本来也想去,只是总有这个那个倒霉事来打扰我,没有去成。”
“太太,难道有哪天有什么事妨碍过您吃饭吗?我想没有。要是您的心对您的骨肉亲人能像对您吃的骨肉那么有好感,那就没有什么考虑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使得您不去看她,让她孤独地坐着,望眼欲穿地等待您和您的安慰了。何况您孩子的孩子正在她胸脯底下颤动哩!”
这时,这出言不逊的年轻妇人被一个佣人的美好生活中并非罕见的情况所打断。范·艾克受到她佣人先前对她的攻击感到气恼,本已体面而策略地进入埋伏,这时便忍不住跳出来大声嚷道:
“你这么不尊敬我的客人,你去另找地方吧!”
“好得很。”嘴硬的赖克特说道。
“女士,那可要不得,”好心的凯瑟琳插嘴说,“老实人终归是要讲心里话的。她只不过是舌头带刺罢了。”这时,泪水已涌出凯瑟琳的眼睛来肯定她讲的话。“她说出来总比装在脑子里好。这样她就不会感到心里难受了。为了我的缘故而辞退她,那可要不得,这该死的丫头。她知道她是个好佣人,所以想占点便宜。我们这些管家的可怜虫还得为她们身价高而付出捐税。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个好佣人。天哪,她把我治得乖乖的。最后谢天谢地她嫁给了一个面包师,我才又挺起腰杆来。‘所以,’我曾经说,‘从今以后可别再有好佣人来对我耍态度了。’我干脆找来一个笨蛋,亲手教她。但一当她分得清左手右手的时候,她就对我狂妄起来。于是我把她一下子给撵了出去,另外找个蠢材来代替她。天哪,把着手一个个地教一连串的傻瓜可也真烦死人。好在我是主人,我说了算。”
这时她已经忘了她本是在为赖克特说好话。忽然她颇带恶意地转过身来对着她补了一句:“我想你在这里当家做主吧。”
“就像那板凳不当什么家,做什么主一样,”范·艾克高傲地说道,“她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佣人,而是被解雇的人。她被辞退了,也就被打发走了。怎么,您没听见我把这狂妄的家伙撵走吗?”
“是呀,是呀,我们都听见你说的。”赖克特满不在乎地说道。
#奇#“那么听听我的吧!”丹尼斯一本正经地说道。
#书#她们都像被安在轮子上似的猛转过身来,用眼睛盯着他。
#网#“赖克特小姐,”丹尼斯十分庄重有礼,以至显得有占荒唐地说道,“你被辞退了。如果仅仅初次见面我就能向你提出建议的话,我想说,既然你已经不再是个佣人了,你就做个女主人,做个王后吧。”
“说来容易。”赖克特粗率地回答道。
“一点不难。你瞧我这个男人,尽管那见鬼的英国人射了我一箭,使我只算得上半个弓弩手了,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在他的尸体上我也留下了同样一个纪念品。你瞧,我有二十块金币,”——他拿出来给她们看——“还有一只强健的手。再隔个把星期我就会有两只强健的手。结婚不是我的习惯,不过对这么多的美德我不能不十分倾心。你很漂亮,心肠又好,又直率,特别是你敢于袒护我的女同伴。那么请你做个弓弩妇吧!”
“这怪字是什么意思?”赖克特问道。
“我的意思是说,请做在座的勃艮第的丹尼斯的妻子、主妇和王后!”
在场的人一片沉默。
不过沉默并没有持续很久,继之而来的是爆发出的强烈愤慨。
凯瑟琳:“嘿,真没听说过!”
玛格丽特:“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
凯瑟琳:“竟然当着我们的面说!”
玛格丽特:“在可笑的男性的荒唐无礼当中,这可是——”
丹尼斯冷冷地指出,他讲话的女对象一言不语,而并不立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