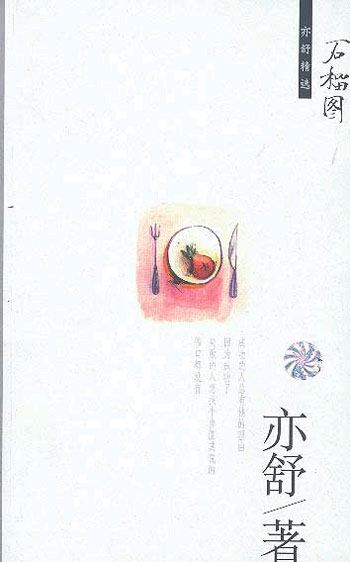十锦图-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几日来,他体内似乎起了极大的变化,蒲大松所贯注于他身内的精力,已和他本人融于一体,举掌投拳,威力无匹!
这时他试着如此施展开来,活像是一只大守宫,但见他身影摇动之间,已行出了丈许以外!
他爬身在棚角边上,用手指,轻轻分开一缝,就目向内一望,棚内一切全在目中。
只见是一个占地约在十丈见方的空场子,场内全铺以厚厚的一层黄沙。
蒲天河试看那沙的厚度,最少也在一尺以上,全场十丈见方的地方,全力黄沙铺满,怪异的是沙面是为什么东西砌过,看起来平如止水,其上竟连一些足痕都没有!
蒲天河这时才注意到,那丁大元正疾行于浮沙之上,他身形奇快,看来如同是狂风之下的一个纸人儿一般。
只见他身形时起时落,时上时下,每每落下之时,只凭着足尖一点,沙面上不过留下一个铜钱大小的圈圈,似如此,他试行了一周之后,最后他双手平着猛地一伸,像燕子似地平纵而出。
就在沙场左右两边,各树着一个高脚的凳子。
丁大元身子轻轻向下一落,落在一张凳于上。
蒲天河见他这时一张脸似乎很红,而且微微都见了汗,他坐在凳子上喘息了一阵之后,才见他用一支笔,试数着沙地上的足印子,然后记在了纸上。
这种情形,看在蒲天河眼中,不由暗自吃惊。
他知道这丁大元是在练一种至高的气功,这种凌气而行的步法,武林中名之为“太虚幻步”,是一种极难练的功夫!
因为施功人,必须具有极深的轻功造诣,才能初步开始着手。
这种功夫,练习之时,全在乎一口气之间,中途不能换气,而且这一口气,要平均地分配在丹田四肢,起伏于黄庭祖窍之间。
这几个步骤,如果一个弄错了次序,或是分配不均,就不能见功。
非但如此,一个处置不妥,练功本人就可能岔了气眼,以致于终身残废!
所以练这种功夫的时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要绝对的保持安静,不能为一点噪音干扰!
蒲天河看到此,才算明白过来,这正是为什么丁大元把练武时间,要选择在深夜,为什么在棚边设下铃网?而不许任何人干扰!
老魔手下一丁二柳小白杨,四大弟子盛名,蒲天河是久仰了。
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居四大弟子之首的丁大元,竟然会有如此的一身功夫。
他本来颇负自信的内心,在看过丁大元这种功夫之后,也禁不任有些动摇了。。这时就见丁大元坐在凳子上,歇息了一阵之后,再次站起了身子。
他由墙上取下一个“丁”字形的木牌,小心地在沙面上推着,方才为他足尖所踏过的地方,都为这木牌重新弄平了。
大棚内,原本只有两盏大灯,这时丁大元忽地飘身而下。
他仍然是提着一口真气,凌虚而行。
就见他用一支火把,来回地在场内点烧着,不一刻棚内光华大盛。
蒲天河才注意到,这竹棚之下,竟自悬有近百盏烛台,每一烛台之上,都有一截红蜡。。
这时丁大元把这百盏红烛点着,棚内骤然多了满空金星,衬以地上的黄沙,甚是好看。
蒲天河心中一动,暗付:“这厮莫非还有什么花样要玩不成?”
思念之中,那丁大元已把百盏烛台全数点燃。
他鼻息之间,发出了极大的呼声,等到他扑上了坐凳,又自喘息了一阵,头上又见汗珠。
可以想像出,这是一种多么吃力的功夫!
蒲天河看到这里,知道他对这种“太虚幻步”的功夫,不过是刚刚入门,否则不至于如此。
他掏出了一方汗中,擦着头上的汗渍,足足歇了有半盏茶之久。
蒲天河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正要腾身离开的当儿,就见丁大元再次飘身而下。
他仍然是提着一口真力,猛扑到墙角,自一个兵器架上取下一个皮囊。
看到这里,蒲天河也就知道,这丁大元是要练习暗器的打法了。
就见他身形不停地飞快在场内纵着,蒲天河留心看他每一落下之时,前胸都向前微微一弯,足下不免向上一提,这才沾地。
这种步法,是一种很特别的步子,可是蒲天河知道,这其中有一些偷懒的成份在内。
因为方才他是空手,现在他身上多了一个暗器袋子,无形中,就加重了一些重量!
而在他施展这种“太虚幻步”的轻功时,这一点点重量,显然也令他感到很吃力。
就在第二圈的时候,丁大元已把这暗器的皮囊紧紧系好腰上。
他身子较诸先前加快了许多,只是他口鼻间的出息之声,较诸先前也更大了。
忽然他左膝向前一屈,右手五指,由左腋之下穿了过去,猛地向后一甩!
就听见“嗤”地一声,由他五指之间,蓦地飞出了两线金光!
遂闻得“咝咝”两声细响。
棚下正中的一只吊灯,应声而灭。
丁大元身子猛地一个滚翻,这一次却是左手绕着向右面发出去,作“品”字形的,飞出了三点金星,靠右边的三盏灯座又发出了“噬”地一声,三灯一齐应手而灭!
丁大元身子一连跄出了四五步,足下的沙子,由不住踢得飞起了尺许,沙面上留下了很深的足印子。
他跄出了好几步,才慢慢又把身子保持住平稳,可是已由不住见了汗。
蒲天河可以看见,他身上的那一袭紧身黑衣,已为汗水所湿透了。
这期间,丁大元又陆续摆出了“抬头望月”和“左右穿棱”两种招式,分别发出了四五两组暗器,东西两边,应手熄灭了九盏灯。
他这种暗器的打法,使得蒲天河十分吃惊。
这时他才想起方才那白衣少女所说的“千手菩提”,看来这丁大元也真是当之无愧!
忽见他一声断喝,蒲天河心中一怔,正要拔身而起,却见那丁大无猛地一个倒仰之势。
就听得“铮”一声大响,自他双掌间,像是一窝蜂似的,暮地飞出了百十道金光。
棚内烛光顿时一黑,紧接着又是一明。
蒲天河才注意到,那原本还剩下八十余盏烛光,竟几乎全都熄灭,仅仅余了五六盏,在空中荡来荡去。
丁大元这一手“满天花雨”的打法,虽说是功力深绵,到底还不见火候,否则是不应该再留下这其它数盏灯光的!
蒲天河就听见棚面上劈劈剥剥一阵乱响,竟有十数枚铁菩提,穿棚而出,划空而去。
他如非当初有防在先,置身棚角,还真不敢担保不会为这些暗器伤在了身上。
如此一来,他也就没有意思再看下去了。
不过,由此,他却也看出丁大元武功的大概。
他的功夫相当的惊人,可以说是自己一个极大的劲敌,蒲天河由此也就对他存下了戒心。
他这时身子陡然腾起来,向着一棵巨树上落去。
谁知他身子方自向下一落,就见竹门一启,丁大元也走了出来。
蒲天河赶忙隐身不动,遂见丁大元一面擦着头上的汗,径自向后面内宅行去!
蒲天河暗自观察,不敢过于心急,目送他远去后,才转回自己住处。
当他推开了那扇破门的时候,却见门缝间,飘下了一张纸条儿,其上似写有字迹!
他不由心中蓦地一惊。
当时忙拾起那张纸条,把灯光拨亮了,就目一观,他由不住呆了一呆。
只见是一张浅绿色的素笺,其上写着一笔挺秀气但有力的草书,只有十几个字:
只可智取,不便力敌。
少惹风流债!
蒲天河心中不由一动,真有些气笑不得,这张纸条又是谁写的呢?
如果说是小白杨于璇,又不可能,因为她捉拿自己尚恐不及,又怎会暗示自己机要。
再想那个蒙面少女,虽较可能,可是她不是已经回去了么?再说她又怎么进来的?
尤其是看见了那“少惹风流债”这几个字,使他更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他确实也想不出这个人是谁,总之,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坏意,这一点似可断定。
当下他就把它藏好身上,关上了门窗,把背后的剑解下来,倒身在竹床之上。
这一句“少惹风流债”,使他想到了连日来所邂逅的几个姑娘,自己倒真应该注意才是。
他又想到了丁大元,这个人的确不可轻视,自己当今功力虽是可观,如果真要和他动起手来,可就不能确定一定能够胜得了他!
因此这“只可智取,不便力敌”的话,就有很深的含意在其中了。
他左思右想,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沉沉地睡了过去。
当他一觉醒转之时,天色已然大亮。
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在叩着门道:“喂!喂!钱来旺起来了!”
蒲天河先是一怔,可是随即心中一转,立即明白了是在叫自己,当下忙答应了一声,把门开了。
门外站着一个胖胖的老头,身上系着白裙,见了他龇牙一笑道:“你是新来的花把式吧!你可真能睡,怎么昨晚上做了夜工是怎么着?”
蒲天河含糊地笑了笑道:“第一天,不大习惯!老兄你是府上什么人呀?”
这胖子嘿嘿一笑道:“我姓周,是管大厨房的,我跟你妹子小娟顶熟,她关照过我,要我照顾你。来,吃饭去吧!”
蒲天河含笑点了点头,随他走出。
姓周的又说:“你以后叫我周胖子就行了,我还给你找了几套衣服,你对付着穿穿看!”
蒲天河连声道了谢,遂为周胖子带入到厨房进食。周胖子又取出了几套粗布青衣给他,并且告诉他说:“你的事很轻松,只要把花给整理好了,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你要是闲下来,你就来帮我作点杂活,我还能贴你点银子!”
蒲天河点头道:“我有空就帮你的忙,钱却不敢要,在这里钱有什么用?”
周胖子哈哈笑道:“你算看得开,不过这地方两年一放,你要是愿意走,也没有人勉强你!”
说着话,就见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妈妈走进来道:“开饭啦,大奶奶等着吃呢!”
胖子笑着站起来,把备好的一碟烫面饺,一碟千层松糕,另外还有一小碗桂花汤团,放在红木托盘里,交给那个老妈妈,道:“快拿去吧,覃妈!”
这个覃妈一副懒相的接过了盘子,向着蒲天河望了望道:“你就是新来的花匠吗?”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是的!”
覃妈就眯起一对小眼睛笑了笑道:“噢……长相还真不错,外面都在谈你,说你是四姑姑那边使唤丫鬟小娟的哥哥,方才大爷还说要见见你呢!”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暗忖道:“不好!莫非他已看出了我的底细不成?”
想着就含笑道:“大爷有什么事么?”
覃妈摇头道:“没什么事,听说是要你给小姐那边送花去!”
说着上房有人在叫覃妈,这个老妈妈吐了一下舌头,赶忙端起盘子就走了。
周胖子呵呵一笑,在蒲天河肩膀上拍了一下道:“小伙子听见没有?你算是出了名了,不过,年轻人走桃花运可不是好事,你要注意啦!”
蒲天河一笑道:“没有的事!”
说着他就走出厨房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不想身子才进,就见覃妈走过来,招呼道:
“喂!钱兄弟,大爷叫你呢!”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就关上了门,换了一套粗布衣裳,自己看看,倒真有几分像是一个穷小子的模样。
他出得门,见覃妈笑眯着他道:“你跟我来,大爷在书房里!”
她领着蒲天河一直穿过前厅,来到了书房,房门垂着厚厚的一层暖帘,二人来到了门前,覃妈揭起帘子道:“花把式来了!”
里面一人哼道:“叫他进来!”
覃妈回身指了一下里面,她自己就退了下去,蒲天河揭帘而入,就见丁大元正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用笔在练着字,神情甚是悠闲!
他穿着一袭宝石蓝色的短袄,头上戴着一顶便帽,正直悬着手腕在写字。
蒲天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