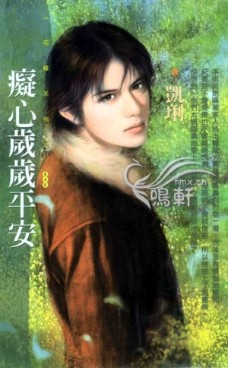战争与和平-第19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贝格和伯爵夫人不解而又惊吓地望着娜塔莎。伯爵则呆在窗旁听着。
“妈咪,这样不行,您瞧瞧院子里的情况!”她大声说,“他们要留下来!”……”
“你怎么啦?他们是谁呀?你要什么?”
“伤兵,就是他们!这不行,妈咪;这太不像话……,不,妈咪,亲爱的,这不是那么回事,请您原谅,妈咪……亲爱的,那些要运走的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嘛,您只要看看院子里面……妈咪!……这样不行啊!……”
伯爵站在窗户旁听着娜塔莎说话,脸也没有转过来。他突然鼻子哼了一下,把脸贴近窗户。
伯爵夫人望着女儿,看到她为母亲感到羞耻的脸,看到她的激动,明白了为什么丈夫现在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因此张皇失措地环顾周围。
“噢,你们想怎么办就去办吧!难道我妨碍谁了!”她说,还未一下子认输。
“妈咪,亲爱的,请原谅我。”
伯爵夫人却推开女儿,朝伯爵走去。
“Mon cher,你来管事吧,该怎么……我可是不知道这事啊。”她说,悔恨地垂下目光。
“鸡子……鸡子教训母鸡……”透过幸福的泪花,伯爵说出了这句话,然后拥抱妻子,妻子则高兴地把羞愧的面孔藏在丈夫怀里。
“爸爸,妈咪!可以由我来管吗?可以吗?”娜塔莎问。
“我们就只带上最要紧的……”她说。
伯爵赞同地向她点头,娜塔莎随即像玩逮人游戏一样,飞快跑过客厅,穿过前厅,跑下台阶到了院子里。
人们聚拢在娜塔莎身旁,一直不敢相信她传达的那道奇怪的命令,直到伯爵亲自出来以妻子的名义肯定那道命令,即把车辆拨给伤员,而把箱子搬回贮藏室,他们才相信。弄清楚命令后,人们高兴地匆忙地担负起这项新的任务。现在,奴仆们不仅不觉得奇怪,相反,还觉得不能不这样;就像一刻钟以前,不仅谁也不觉得留下伤员带走东西奇怪,而且还觉得正该如此。
所有的家奴,好像要补偿刚才没这样做的过失,利索地干起了安置受伤官兵的新任务。伤员们拖着腿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围住大车,苍白的脸上露出喜色。邻近几家也传开了还有车辆的消息,所以,其他家里住的伤员也开始到罗斯托夫家的院子里来。伤员中的许多人请求不用卸下东西,让他们就坐在东西上面。可是,已经开始解开绳索的情况再也收不了场了。留一半或留下全部都一样。院子里散放着不带走的装有武器、青铜器绘画和镜子的箱子,这是昨晚辛辛苦苦收拾好了的;人们仍在寻找,并且也找到了那些可以不带走的东西,腾出了一辆接一辆的大车。
“还可以再搭四个人,”管家说,“我把我的车也让出来,要不,把他们搁在哪儿呢?”
“把我运衣服的车也给他们,”伯爵夫人说,“杜尼亚莎跟我坐一辆车。”
他们又腾出运衣服的车去接隔壁第三、第四家的伤员。所有家奴和仆人干得都挺带劲。娜塔莎充满了兴奋而且幸福的快活情绪,这种热闹气氛她已久违了。
“把它捆在哪儿呢?”仆人边问边把箱子往马车后狭窄的踏脚蹬上放,“至少得再留一辆才行。”
“它装的什么?”娜塔莎问。
“伯爵的书籍。”
“放下。瓦西里奇来收捡。这个用不着。”
这辆轻便马车已坐满了人,彼得·伊里伊奇坐在哪儿都成了问题。
“他坐前座。你坐前座上吧,彼佳?”娜塔莎大声说。
索尼娅同样也在忙个不停;但她忙碌的方向正好与娜塔莎的方向相反。她把不带走的东西送回屋里去,并照伯爵夫人的意思一一登记,还尽力多带走一些东西。
17
一点多钟,装载停当的罗斯托夫家的四辆马车停在大门口,运送受伤官兵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了院子。
载着公爵安德烈的马车从台阶旁经过时,引起了索尼娅的注意,她正同一位使女布置伯爵夫人在车上的座位,夫人高大宽敞的马车正停在大门口。
“这是谁的马车?”索尼娅从车窗探出头来问。
“您还不知道吗,小姐?”使女回答,“受伤的公爵:他在咱们府上留宿,也同咱们一道走。”
“是谁呢?姓什么?”
“咱们先前的未婚姑爷。博尔孔斯基公爵!”使女叹气着回答,“听说快要死了。”
索尼娅跳下马车,跑着去找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已穿好了旅行服装,披着披巾,戴着帽子,疲倦地在客厅踱来踱去,等待家奴们关好门户坐下作启程前的祈祷。娜塔莎不在这里。
“姆妈,”索尼娅说,“安德烈公爵在这里,受伤了,生命垂危。他同咱们一道走。”
伯爵夫人惊吓地睁大眼睛,并抓着索尼娅的手朝周围看了看。
“娜塔莎呢?”她开口问。
对索尼娅,同时也对伯爵夫人来说,这消息在头一分钟内只有一个意义。她们是了解娜塔莎的,因而,害怕娜塔莎会出事的恐惧感,压倒了她们对一个人的同情,而这个人她们也是喜爱的。
“娜塔莎还不知道;但他是同我们一道走的。”索尼娅说。
“你是说他生命垂危?”
索尼娅点了点头。
伯爵夫人拥抱着索尼娅哭了。
“天意难解!”她想,感到在目前已造成的局面中,一只全能的手已从人们先前目力不及之处开始出现。
“呶,妈妈,一切准备完毕。你们在谈什么?……”娜塔莎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说。
“没谈什么,”伯爵夫人说,“准备好了,那就出发。”伯爵夫人俯身朝手提包弯下腰去,把凄惶的面孔埋起来。索尼娅抱住娜塔莎吻她。
娜塔莎想问个明白地瞪着她。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没有……”
“对我很糟的事吗?…什么事?”敏感的娜塔莎问。
索尼娅叹气,但什么也没有回答。伯爵,彼佳,肖斯太太,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瓦西里奇等都来到了客厅,拴好门,然后人家坐了下来,默不作声,谁也不看谁地坐了几秒钟。
伯爵第一个起立,长叹一声,对着圣像划十字。大家也跟着这样做。然后,伯爵开始拥抱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和瓦西里奇,他们要留守莫斯科;两人这时也抓住伯爵的手,亲吻他的肩上,他轻拍他们的背,说了几句听不真切的亲切的安慰话。伯爵夫人往祈祷室去,索尼娅发现她跪在墙上残缺不全的圣像前面(家传的最宝贵的圣像要随身运走)。
在台阶上,在院子里,要走的仆人带着匕首和马刀(是彼佳发给他们的),裤脚塞进靴子,裤带和腰带系得紧紧的,正和留下的仆人告别。
像临行前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许多东西拉下啦,放的不是地方啦;两个随从在敞开的车门和放下的脚蹬的两边已站立很久,等着待候伯爵夫人上车;同时,使女们抱着坐垫和包袱跑到几辆马车上(格式马车和大小四轮等),在从家里到马车之间的路上来回跑动。
“一辈子都是忘这忘那的!”伯爵夫人说,“你该知道,我不能这样坐!”杜尼亚莎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跑了过来重新整理座位,一脸的委屈。
“噢,这些人哪!”伯爵摇着头说。
专为伯爵夫人驾车的老车夫叶菲姆高高地坐在驭手座上,对他后边发生的事不屑一顾。积三十年之经验,他知道还不会很快命令他:“出发!”即使下了命令,还会让他停车两次,派人去取忘了拿的东西,这之后还会叫他停一次,伯爵夫人才会从车窗探出头来,以基督的名义哀求他在下坡时要小心。他知道这样的情形,所以比他的马(尤其是左辕的枣红马,叫雄鹰,此刻在踏脚和嚼马嚼子)更有耐心地静候事态的发展。
大家终于就座,脚蹬折拢收进车厢,车门关上,只等去取首饰匣的人回来。伯爵夫人探出头来说了该说的话。这时,叶菲姆慢慢从头上摘下帽子,画了十字。骑导马的马夫和所有仆人也画了十字。
“上帝保佑!”叶菲姆戴好帽子,说“驾!”导马夫随即启动马车。右边的辕马拉紧了套,车盘的弹簧吱扭地作响,车身摇晃了起来。一个随从跳上已启动的马车的前座。轿式马车从院子驶入不太平整的马路时颠簸了一下,其余马车随着也颠簸了一下,最后,车队全都驶上街道,朝前进发。轿式马车和大小四轮马车里的人们,都朝街对面的教堂画十字。留守莫斯科的家人在马车两旁夹道送他们。
娜塔莎从未体会过今天这样的愉快感觉,她挨着伯爵夫人坐着,两眼盯着缓慢向后移动的被放弃的惊惶不安的莫斯科的城墙。她常常探出头来或前或后地张望,看走在前边的受伤官兵的车队。她看到了走在最前面的车顶罩住了的安德烈公爵那辆四轮大马车。她不知道谁在车里,可每当想起她家的车队时,总是用目光搜寻这辆马车,她知道它在最前面。
在库德林诺,从尼基茨卡雅、普雷斯尼亚和波德诺文斯克等街道开出的与罗斯托夫家的车队同样的车队,汇合了,走到花园大街时,只好两队并排前进。
在苏哈列夫塔楼拐弯时,娜塔莎好奇地,目不暇接地观看着乘车和步行的人们,突然惊喜地叫起来。
“老天爷!妈妈,索尼娅,快看,这是他!”
“谁?谁?”
“瞧,真的,别祖霍夫!”娜塔莎说,同时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着一个穿马车夫长褂子的高大臃肿的人,从步态和气派来看,显然是化了装的老爷,他正同一个黄脸无须穿粗呢大衣的小老头一道,来到苏哈列夫塔楼的拱门下边。
真的,是别祖霍夫,穿着长褂子,与一个小老头儿走在一起。“真的,”娜塔莎说,“看哪,看哪!”
“那不是,这人不是他。怎么可能呢,胡说!”
“妈妈。”娜塔莎叫了起来,“您可以砍我的头,这是他。我会让您相信的。停,停。”她向车夫喊道;但车夫停不下来,因为从市民街又驶来大车和马车车队,并且朝罗斯托夫家的马车喊叫,让他们继续走,别挡路。
的确,虽然车队愈走愈远,但罗斯托夫全家人仍然看到了皮埃尔或极像皮埃尔的那个人,穿着车夫的大褂,耷拉着脑袋,面容严肃地和一个没留胡子的小老头并排走着,这个小老头像个仆人。他看到从车窗显露出来朝他们看的面孔,恭敬地碰了碰皮埃尔的胳膊肘,指着马车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皮埃尔好久都搞不明白他说的什么,因为他显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当他终于明白了他的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时,认出了娜塔莎,随即凭他最初的印象毫不犹豫地朝马车走去。但走了十来步,他似乎想起了一件事,便停了下来。
娜塔莎探出车厢的面孔,现出柔情的嘲笑。
“彼得·基里雷奇,来啊!我们认出您啦!好意外呵!”她大声说着,把手伸给他。“您这是怎么啦?您为什么这样?”
皮埃尔抓住伸过来的手,在走动中(因为马车在继续前进)笨拙地吻它。
“您出什么事啦,伯爵?”伯爵夫人用惊奇和同情的声音问。
“什么事?为什么?请别问我。”皮埃尔说,回头看一眼娜塔莎,她那喜悦的流光溢彩的目光(他不看她也能感觉到)的魅力吸引着他。
“您怎么啦,还是要留在莫斯科?”皮埃尔沉默了片刻。
“留在莫斯科?”他用问话的语气说。“对,留在莫斯科。
告别了。”
“唉,我要是男人就好了,我一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