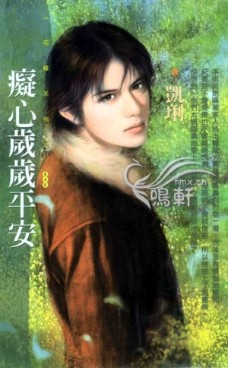战争与和平-第1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您怎么错过了好时光?”
“好家伙!这对落汤鸡!不要把我们的客厅弄湿了。”
“不要弄脏了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的衣裳。”几个声音一齐答道。
罗斯托夫和伊林赶紧找了一个不致使玛丽亚·亨里霍夫娜难堪的角落换湿衣服。他们走到隔扇后面好换衣服;但这间小贮藏全被挤得满满的,一只空箱子上点着一支蜡烛,三个军官坐在那儿玩牌,怎么也不愿让出自己的位子。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拿出一条裙子当帷幔,就在这张帷幔后,罗斯托夫和伊林在带来背包的拉夫鲁什卡的帮助下,换下湿衣服,穿上干衣服。
人们在一只破炉子里生了火,有人搞到一块木板搭在两个马鞍上,铺上马被,弄到一个茶炊、食品柜和半瓶罗姆酒,并请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作主人,大家围坐在她周围。有人递给她一条干净的手绢,让她擦擦秀丽的小手,有人把短上衣铺在她脚下防潮,有人把斗篷挂在窗户上挡风,有人挥手赶开她丈夫脸上的苍蝇,以免惊醒了他。
“不要理他,”玛丽亚·亨里霍夫娜含着羞怯的幸福的微笑说,“他整夜未醒,总睡得这么香甜。”
“不,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一个军官回答道,“应该巴结一下医生,将来他给我截胳膊锯腿时,可能会怜悯怜悯我。”
只有三只杯子,水脏得看不清茶浓还是不浓,而茶炊里只有六杯水,但是这样却更令人高兴:按年龄大小依次从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不太干净的留着短指甲的小胖手里接过茶杯。看来,今天晚上所有的军官确实都爱上了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甚至在隔壁玩牌的几个军官也感染上了向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献殷勤的情绪,受到它的支配,很快丢下牌移到茶炊这里来了。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看见身边这群英俊有礼的青年,高兴得容光焕发,虽然她极力不显露出来,尽管她显然害怕身后睡梦中的丈夫的每一动弹。
只有一把茶匙,白糖很多,搅不过来,因此就决定,她轮流给每个人搅和。罗斯托夫接过杯子,向杯中掺了罗姆酒,就请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搅和。
“可您并未放糖啊?”她总是微笑着说,仿佛她说什么或别人说些什么都很可笑,别有用意似的。
“我不要糖,只想您亲手搅搅就行了。”
玛丽亚·亨里霍夫娜同意了,开始找把被谁拿走了的茶匙。
“您用手指头搅吧,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罗斯托夫说,“这样更好。”
“烫!”玛丽亚·亨里霍夫娜高兴得红了脸,说道。
伊林提了一桶水,往桶里滴了几滴罗姆酒,走近玛丽亚·亨里霍夫娜,请她用手指搅搅。
“这是我的茶碗,”他说,“只要您伸进手指头,我全部喝干。”
当茶喝完时,罗斯托夫取来一副牌,建议与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一块儿玩“国王”。以抓阄的方式决定谁做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的搭档。按罗斯托夫建议的规则玩,谁做了“国王”,谁就有权亲吻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的手,而谁做了“坏蛋”,则要在医生醒来时,为他烧好茶炊。
“那要是玛丽亚·亨里霍夫娜当了‘国王’呢?”伊林问道。
“她本就是女王!她的命令就是法律。”
游戏刚开始,医生蓬乱的头就从玛丽亚·亨里霍夫娜身后抬了起来。他早就醒了,仔细听着人们在说些什么,显然,他认为人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没什么可乐、可笑和好玩。他的脸郁闷而颓丧。他没同军官们打招呼,搔了搔头,请挡路的人让他过去。他刚一走出去,全体军官就哄然大笑,而玛丽亚·亨里霍夫娜脸红得涌出了泪水,这么一来,在全体军官眼中,她更有吸引力了。医生从外面返了回来,对妻子说(她已经不再现出幸福的笑容,惊恐地看着他,等待着判决),雨已经停了,要去篷车里过夜,不然东西要被人偷光了。
“我派一个勤务兵上去守着,派两个!”罗斯托夫说,“就这样,医生。”
“我亲自去站岗!”伊林说。
“不,先生们,你们已经睡过觉了,而我可两夜未合眼。”医生说着,闷闷不乐地在妻子旁边坐下,等着玩牌游戏结束。
医生阴沉着脸,斜视着自己的老婆,军官们望着他那个样子更乐了,许多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赶紧尽力为他们的笑找一个无伤大雅的借口。医生领着老婆离开了并一起进了篷车,军官们也在小酒馆里躺了下来,盖上潮湿的军士衣;但是他们久久不能入睡,时而谈论医生刚才的惶惶不安和他老婆的兴高采烈,时而跑到外面,通报篷车里有什么动静。罗斯托夫好几次蒙上头想入睡,却又有什么评论吸引了他,就又开始谈起来,又传出了无缘无故的、快活的、天真的笑声。
14
两点多钟了,谁也没有睡着,司务长此时进来传达了进驻奥斯特罗夫纳镇的命令。
军官们仍然有说有笑,急忙开始做出发的准备;他们又烧了一茶炊不干净的水。可是罗斯托夫不等茶水烧好,就去骑兵连了。天已经亮了,雨也停了,乌云正散去。既湿又冷,特别是穿着没有干透的衣服更是这样。从小酒肆出来,罗斯托夫和伊林在晨光中端详了一下被雨淋得发亮的医务车的皮篷,车帷下面露出医生的两只脚,可以看见在车中间的坐垫上医生老婆的睡帽,听得见她熟睡中的呼吸声。
“真的,她太迷人了!”罗斯托夫对与他一起出来的伊林说道。
“多么迷人的女人!”十六岁的伊林一本正经地答道。
半小时后,排好队的骑兵连站在大路上。只听见口令:“上马!”士兵们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就开始上马。在前面骑着马的罗斯托夫命令道:“开步走!”于是,骠骑兵们四人一排沿着两旁长着白桦树的大道,跟在步兵和炮兵后面开拔了,只听见马蹄踩在泥泞的路上的噗哧声,佩刀的锵锵声和轻轻的谈话声。
在泛红的东方,青紫色的浓云的碎片很快被风吹散了,天越来越亮了。乡村道路上总是生长着的卷曲的小草,由于夜雨的湿润看起来更加鲜亮了;低垂的白桦树枝条湿漉漉的,轻风吹过摇摇晃晃,斜斜地撒下晶莹的水珠。士兵的脸孔越发看得清楚了。罗斯托夫与紧紧跟着他的伊林骑着马在两行白桦树之间的路旁行进。
征途中罗斯托夫无拘无束地不骑战马,而骑一匹奇萨克马。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又是一名猎手,不久前,他为自己搞到一匹顿河草原的白鬃赤毛的高头烈马,骑上它没有谁能追得到他。骑在这匹马上对罗斯托夫是一种享受。他想着马,想这早晨、想医生的妻子,就是一次也未想到面临的危险。
以前罗斯托夫作战时,常害怕,现在却不觉得丝毫的惧怕,不是因为他闻惯了火药味而不害怕(对危险是不能习惯的),而是他学会如何在危险面前控制自己的内心。他养成一种习惯,在作战时,除了那似乎最使人关心的事——当前的危险外,什么都想。在最初服役时,无论他怎样骂自己是胆小鬼,就是达不到现在的样子;可是年复一年,现在他自然而然地做到了。现在他与伊林并马行进在白桦树中间,时而随手从树枝上扯下几片树叶,时而用脚磕磕马肚皮,时而把抽完的烟斗不转身就递给身后的骠骑兵,如此从容不迫,一幅无忧无虑的样子,好像他是出来兜风似的。他不忍心去看伊林那激动不安的脸,就是那个话兴很多、心神不平的伊林,凭经验他知道这个骑兵少尉正处于等待恐惧和死亡的痛苦状态,他也知道,除了时间,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
太阳在乌云下一片晴空刚一出现,风就静下来,仿佛风不敢破坏夏日早晨雨后的美景;水珠仍然洒落,却已是直直落下,——四周一片寂静。太阳完全露出在地平线上,随后又消失在它上面一片窄而长的乌云里。过了几分钟,太阳撕破乌云的边缘又出现在乌云上边。一切都明光闪亮。好像响应这亮光似的,前方立刻响起了大炮声。
罗斯托夫还没来得及考虑和判定炮声的远近,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的副官就从维捷希斯克驰来,命令沿大路跑步前进。
骑兵连经过同样急速前进的步兵和炮步,冲下山坡,穿过一个空无一人的村庄,又上一个山坡。马匹开始出汗,而人满脸通红。
“立定,看齐!”前面传来营长的命令。
“左转弯,开步走!”前边又传来口令。
于是骠骑兵沿着长列的军队赶到阵地的左翼,在第一线的枪骑兵后停下来。右面是我军密集的步兵纵队——这是后备队;山上更高的地方,在一尘不染的明净的空气中,在朝阳明亮的斜照下,最远处地平线上,可见我军的大炮。前面谷地可见敌人的纵队和大炮,可听见谷地里我军散兵线的枪声,他们已投入战斗,欢快的与敌人互相射击的枪声清晰可闻。
罗斯托夫仿佛听到最欢快的音乐似的内心觉得很舒适,他好久没听见过这声音了。特啦啪—嗒—嗒—嗒啪!有时噼哩啪啦。枪声齐鸣,有时却又快速地一声接一声,接连响了好几枪。四周又沉寂了,随后好像有人放爆竹似的,又接连不断响起来。
骠骑兵原地不动站了约一个钟头。炮轰也开始了。奥斯特曼伯爵带着侍从从骑兵连后边驰过来,停下与团长交谈了几句,就向山上的炮兵阵地驰去。
奥斯特曼刚离去,枪骑兵们就听到口令:
“成纵队,准备冲击!”他的前面的部兵分成两排,以便骑兵通过。枪骑兵出动了,长矛上的小旗飘动,向山下左方出现的法国骑兵冲去。
枪骑兵刚冲到山下,骠骑兵就奉命上山掩护炮兵。骠骑兵刚在枪骑兵的阵地上停下来,就从散兵线那儿远远地飞来咝咝呼啸的炮弹,没有命中。
罗斯托夫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心里觉得比以前的射击声更使他高兴和兴奋。他挺直身子,察看山前开阔的战场,全心关注着枪骑兵的行动。枪骑兵向法军龙骑兵扑过去,在烟雾蒙蒙中混成一团,过了五分钟,枪骑兵退了回来,他们不是退回到他们原来呆的地方,而是退向左边。在骑枣红马的橙黄色的枪骑兵中间和后面是一大片骑灰色马、身着蓝色制服的法军龙骑兵。
15
罗斯托夫以自己锐利的猎人的眼睛第一个望见这些蓝色的法国龙骑兵追赶我们的枪骑兵,队形混乱的枪骑兵人群和追赶他们的法军龙骑兵越来越接近了,已经可以看见这些在山上显得很小的人们如何互相厮杀、追赶,如何挥舞胳膊或佩刀。
罗斯托夫像看猎犬逐兽似的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他以嗅觉感觉到,如果现在与骠骑兵一起冲向法军龙骑兵,他们会站不住脚的;可是,如果要冲锋,就得即刻冲锋,一分钟也不能拖,否则就迟了。他环视自己周围。大尉就站在身旁,也目不转睛地望着下面的骑兵。
“安德烈·谢瓦斯季扬内奇,”罗斯托夫说,“要知道我们可以冲垮他们……”
“是厉害的一着,”
大尉说:“确实……”
没有听完他的话,罗斯托夫就策马驰到骑兵连前面,没有等他发出出击的口令,跟他有同感的整个骑兵连,都随他之后驱动了战马。罗斯托夫自己不知道,他是怎样做的,又为何这样做。他做这一切,正像他在打猎时所做的一样,不假思索,不假考虑。他看见龙骑兵走近了,他们在奔驰,队形散乱;他知道他们会支持不住的,他知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