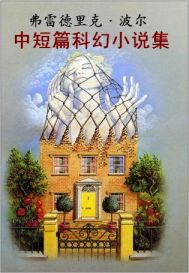小说月报-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度无限的光缆,它穿过旅馆的窗子和窗外的街道,穿过不远处灯火通明的维多利亚湾,抵达彼岸,抵达全世界。全世界的声音和图像都浓缩在马教授的手里。她崇拜他的手。之后她开始凝视自己的乳房,它们仍然丰硕而结实,看起来很性感,但是,那已经是一首挽歌了。她轻轻地抓住马教授的手,放在自己的乳房上,马教授沉在睡梦中,手先醒了,热情地揉摸一番,忽然惊醒,翻身坐起来,惊恐地瞪着她的乳房,说,对不起,瑞漪,对不起,我忘了。
她用枕头捂住自己的胸部,先是笑了两声,然后就哭起来了。
9
世界上只有马教授一个人,叫过她瑞漪。
她喜欢他用浑厚的男中音,叫她瑞漪,那声音传递出一些赞美,一些祝福,还有一丝温暖的爱意。但可惜,马教授后来改口称她为小段了。她质问他,你为什么不叫我瑞漪了?马教授的解释听起来很真诚,叫你瑞漪,嘴巴总是张不大,舌头很紧张,有点累啊。她知道那只是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另一半是合理的退却,是礼貌的躲避。那是他的权利。她清醒地认识到,段瑞漪这个名字带给她的不是幸福,只是一堆篝火,或者是另一只紫铜脚炉而已,仅供御寒之用,而所有的火,迟早是要熄灭的。
她不舍得浇灭马教授剩余的火苗。有一次她从医院跑出去,带上嫂子给她炖的红枣莲子汤,拦了辆出租车,直抵马教授的家。辛辛苦苦地爬到五楼,敲门无人应,她怏怏地转到南面,仰头观察马教授的阳台,一眼看见晾衣杆上有一只黑色胸罩,像一只巨大的黑蝴蝶,迎风飞舞。她愣怔了几秒钟,打开保温壶,对准花圃里的一棵月季花,把红枣莲子汤一点点地倒了个干净。壶空了,她又仔细看了眼五楼阳台上的那只胸罩。大号吧?她鼻孔里冷笑一声,自言自语道,我就知道,肯定是大号。
与马教授分手,是与幸福的假象分手,也是与段瑞漪这个名字分手,她很心痛。住院化疗的那段时间,护士叫段瑞漪的名字,她无端地觉得那声音缺乏善意,总是慢半拍才答应,不仅是抵触,她心里有一丝深切的恨意,不知是针对护士的,还是针对自己的名字。她对护士说,别叫我段瑞漪了,你能不能喊我段菲菲?要不叫段嫣也行,我原来叫段菲菲的,以前还叫过段嫣,姹紫嫣红的嫣。护士埋怨她说,你那么多名字,我怎么记得住?菲菲不是很好吗?又好记又上口,谁让你乱改名的?你这个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还去查了字典!她半晌无语,低头看着自己的胸部,说,是啊,这个漪字有什么好的?害你去查字典,害我丢了乳房。
她幻想以乳房换生命,但一切都晚了。再完美的乳房,切了就无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后来我们听顾莎莎说,她比医生估计的多活了半年,比自己期望的,则至少少活了半个世纪。
那年冬天遭遇罕见严冬,她的弥留之际,恰遇一场暴雪,亲人们都被困在路上,病房里只有她老父亲一个人陪护。她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认为是茫茫大水,说,这么大的水啊,都漫到三楼了。段师傅说,不是水,是雪,外面在下大雪。她说,不是雪,是水,我命里缺水,临死来了这么大的水,还有什么用呢。过后她看见有人蹚水来到了窗前,她对父亲说,她来了。段师傅以为她牵挂自己的孩子,说,你放心,小铃铛马上就来了,你哥哥去学校接她了。她摇头,说,不是小铃铛,是她来了,我看见她了。段师傅猜她看见了亡母的幽魂,你看见你妈妈了?妈妈跟你说什么了?她还是摇头,说,不是妈妈,妈妈不敢来,怕我埋怨她。是乡下奶奶来了,她蹚这么大的水来骂我,骂我活该,她问我呢,给我取了那么好的名字,我为什么鬼迷心窍,非要给改了?
段师傅以为那是糊涂话,他记得女儿只是在襁褓里见过祖母,怎么会认得祖母呢?所以他问,真是你奶奶?她什么样子?她说,干干瘦瘦的,黑裤子,打赤脚,右边眉毛上有一颗痦子。段师傅很惊讶,那确实是他乡下母亲的基本模样。然后他听见女儿叹了口气,说,算了,还是听奶奶的话好,我以后还叫福妹吧。
10
我们香椿树街居民后来送到殡仪馆的花圈,名字都写错了。即使是马教授和顾莎莎的花圈,名字改成了段瑞漪,其实也是错的。遗嘱需要尊重,一切以家人提供的信息为准,被哀悼的死者不是段瑞漪,不是段菲菲,更不是段嫣,她的名字叫段福妹。
段福妹。
听起来,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名字了。如果不是去参加这场追悼会,谁还记得她有过这个土气而吉祥的名字呢?
责任编校 孙昱莹
============================================================================
==============================================================
无边无际的尘埃
胡学文
1
那家旅店在南二环与西二环交会处,只有两层,不怎么起眼。名字挺有意思,叫爱人之家。上楼时,杜月碰碰我,我知道她担心什么,我抓紧她的手,让她放心。距旅店几百米远有一所技校,旅店的客源多半是技校的学生,安全应该没有问题。我白天踩点儿时,一对学生正登记入住。
房间不大,一张床占去一多半,但有什么关系呢?我和杜月需要的只是一张床。我反插了门锁,急不可耐地抱住杜月。杜月稍往后仰,问插牢没有,我说苍蝇也飞不进来。杜月说带了好吃的给我,我说最好吃的是你。杜月喊口渴,我知道她紧张,她紧张口就渴。我松开她,烧了一壶水,把她带的新疆切糕吞下去。其实我牙不好,怕吃甜食。
我和杜月上床。她担心地问,他不会找到这儿吧?路上已经说过多次,我不想再废话,用舌头堵住她的嘴。几分钟后,杜月突然睁开眼,满脸警觉。我明白她为什么如此,那声音我也听到了。我的头皮阵阵发麻,但竭力掩饰。杜月问我听见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啊,你太紧张了。可是,我没法堵她的耳朵。那声音开始还有些犹豫,此时由缓而急,由轻而重,然后就是猛擂。杜月变了脸色,狠狠瞪我一眼。我仍然不相信他会找到这儿。他已经在喊了。即使同时有一百种声音,我也能辨出他的嗓音。杜月发疯地套衣服,我则僵着,说不清是震怒还是惊恐。
小乐,我知道你在,你打开门,我有话说。
我猛拽开门,王大乐直栽进来。杜月从我身边挤过去。往常有类似遭遇,我选择和她一块儿离开。那天没有,我甚至没敢看她。我死死盯住王大乐,关节嘎巴嘎巴响。王大乐个儿不高,又佝偻着腰,越发显得矮小。他在我的逼视中渐渐后退,缩到墙角。他紧紧贴在那儿,像个干瘪的蜗牛壳。他的声音没有退缩,像没拧干的衣服滴答着,你不能学坏,我是为你好……你不能学坏,我是为你好……
我挥拳砸在他脸上。他苍白的脸凸起一团紫青,第二拳砸在他鼻子上,他的鼻梁发出一阵脆响。拳头次第落下,血从他鼻孔嘴巴往外喷,染透了我前胸。他开始求饶,声音拖着长长的血沫泡。拳头依然疯狂落下,直至他缩进墙体,成为墙壁的一部分。
你不能学坏,我是为你好……
我晃晃头,他的身子,他的脸,他的声音再次清晰。许多次了,我在臆想中出着恶气。我不能打他,他是我父亲。
半小时后,我和王大乐坐在公交车上。我租住的地方在东二环边上,回去要倒三趟车。就是说,我和杜月到爱人之家,倒了三趟车,单程一个多小时。一次艰难的来之不易的约会,就这样被王大乐破坏掉。王大乐坐在我前面,我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五十几岁的人,头顶已经谢光,脑后倒长得茂盛。他的头一颤一颤,不知是车的颠簸,还是为哼歌打节拍。王大乐如愿以偿,总要哼些什么。我没有生气,余怒在踏上公交车那一刻已经消逝。疑惧却巨浪般一波又一波拍打着我。我离开的时候,王大乐还在喝酒,罐装燕京啤酒,我特意买的。我说去火车站接朋友,王大乐嗯一声。出门,我没有急着走,照例躲在那辆货车后面等了十多分钟。王大乐没跟出来,我的心落到实处。杜月早就在8路车站牌等着了。上车的时候,我还往对面扫视。傍晚的街道望不了多远,但我确信,目光所及,没有王大乐的身影。他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就算跟出来,没与我和杜月乘同一辆车,怎么可能找到这家偏僻的旅店?他真能嗅到我身上的气息?我和杜月的许多次约会,都因王大乐干扰而夭折,我始终认为是没甩掉他。现在我有点相信他的话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心里轰的一声。
盘碗在桌上摆着,啤酒罐已丢到储物筐。里面躺着别的酒瓶子,还有王大乐从街上捡来的零碎,铁钉广告单之类。麻辣花生吃了一半,花生里的辣椒都不见了。我和王大乐都喜欢吃辣椒,我不想和他有同样的嗜好,但在这点上,我无能为力。每次,和王大乐同时大口嚼着辣椒,我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憋闷。
王大乐怯怯地望着我,问我饿不饿。他怕我,从我带他离开营盘镇那一刻,那眼神就长在他身上。他也疼我,用他的方式,我从不怀疑。可是……他一次又一次毁着我的幸福。
我不理他,坚决不理他。王大乐说有炒饼有面条,问我吃什么。随后,他自言自语,煮点面条吧,面条软。我第一次把杜月带过来,也是煮面条。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杜月。我给她发信息,问她回去没有。她没回复,拨过去,关机。她肯定生气了,涵养再好,也应该生气了。她回去了吧?石城虽然是省会城市,并不大,治安也说得过去。我终究不踏实,起身往外走。王大乐追上来,问我去哪儿,然后尾巴似的跟在后面。杜月在私立医院当护士,住在医院提供的三人宿舍,王大乐清楚。我一路小跑,到医院门口方停住。王大乐大张着嘴,呼着粗气。我厉声道,你也要上去?他往后缩去。
返回,我步子放缓许多。王大乐没与我并肩,距我几米远,盯梢似的。在谈固东街与槐安路交叉口,我站住了。路南路北有几家夜总会,整面墙都是灯饰,比赛似的吐着炫目的光。招牌架得极高,每个字都瞪着蛊惑的眼睛。我从未进去过,没那个消费能力。每次经过,目光只是随意扫过,从不停留。那个夜晚,我站着,凝望着一对对巨大的眼睛。王大乐噌地蹿过来,仿佛我站在高楼边缘,正准备跳下去。他扯住我,小声道,回吧。他央求的口吻夹着惊恐。我突然产生强烈的报复欲,猛甩开他,大步往灯光辉煌的地界走。王大乐追上来,再次抱住我,声音打着战,你要干什么?我掰着他的手,恼怒地说,用你管?小乐,不能去啊,你可别变坏。我一个个掰开他的手指,他又一个个扣住。我拖着他走。两人同时被台阶绊倒,我压在他身上。他肯定硌疼了,哎哟一声,环抱我的胳膊松开了。我跳起来,向前狂奔。刚到门口,又被他揪住。他手上的力气很重,爪子般深深嵌到我的肌肉里,语调依然是乞求的,不能去啊,不能去啊。
两个笔挺的保安上前询问,我说你们把这个疯子拖开,里面有朋友等我。一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