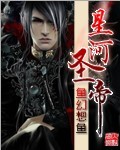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第26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干活儿用的那些牛,这些牛的毛色、身架和脾气都各不相同,甚至每头牛的角都有自己特别的样于、从前,麦列霍夫家也养过这样一头受过伤的、角歪到一旁去的公牛。这头公牛凶狠。狡猾,总是翻着布满血丝的白眼珠斜着看人,每当有人从后面朝它走过来时,它就要踢人;在农忙季节,夜里放它去吃草时,它总想乘机往家里跑,或者——更坏——藏到树林子里去,或者跑到远处的荒沟里去。
葛利高里时常要骑着马,整天地在草原上奔跑寻找它,等到已经认为不会找到了,——却又突然就在山沟深处,在难以通过的稠密的荆棘丛里,或者是在一棵枝叶繁茂的老野苹果树的阴凉里找到了它。这头独角魔王还很会脱掉笼头,夜里用角顶开牲四院子的门环,跑出去,袱过顿河,跑到草原上去游荡。这头牛曾给葛利高里带来不少的麻烦和苦恼……。“这头断了犄角的牛怎样,老实吗?”葛利高里问。
“很老实。怎么样!”
“没啥,随便问问。”
“如果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没啥’——倒是句好话,”赶车的小娘子冷笑着说。
葛利高里又沉默不语了。回忆往事,想想和平的生活。工作,以及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事情,都使他很高兴,因为这场拖了七年之久的战争使他厌恶到极点,只要一想到战争,一想到任何与服役打仗有关的零星琐事,他就感到钻心的恶心和一股无名的怒火。
他再也不要打仗啦。打够啦。他现在要回家去,终于可以干庄稼活儿,跟孩子们和阿克西妮亚一起儿过几天太平日于啦。还是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就打定了主意,要把阿克西妮亚接到家里来,叫她来照料他的孩子,永远留在他的身边、这也不能再那么不明不白地拖下去啦,解决得越快越好。
葛利高里很有滋味地幻想着,回家以后,脱下军大衣和皮靴,穿上肥大的布靴子,照哥萨克的习惯,把裤腿几套进白毛线袜筒里,把家织的粗呢棉袄披在暖和的上衣上,到田地里去手扶着犁柄,踏着湿润的犁沟,跟在犁后头走,使劲吸着翻耕起来的泥士潮润的、淡淡的气味,吸着犁烨切断的草茎的苦味,该有多美啊。在异国他乡,就是泥土和青草的气味也都不一样。在波兰、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他曾多次把灰色的苦艾梗子放在手巴掌上揉碎,一闻,就不禁伤心地想:“不,不是家乡的味道,这是异乡的……”
可是赶车的娘儿们很无聊。她想说说话儿。她也不赶牛了,坐得舒服一些,手里玩弄着鞭子的皮梢,偷偷地端洋起葛利高里,把他那聚精会神的眼神和半睁半闭的眼睛打量了半天。“虽说有了白头发,可是他并不太老。八成儿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她心里想。“而且总是眯缝着眼睛,他为什么要眯缝眼睛呢?你看他,累得那个样子,简直像拉着千斤重的车似的……他的相貌还可以。只是白头发多了一点儿,你看,连胡子也几乎全都白啦。不过模样倒还漂亮。他总在想什么呢?起初他似乎还想逢场作戏,可是后来又不吭声啦,只问了一句什么有关牛的话。他是没有话可说了吧?也许胆怯了吧?不像。他的眼神很坚定。不,他是个很漂亮的哥萨克,只是有点儿怪脾气。好吧,那你就闭着嘴吧,罗锅儿鬼!你以为我就那么需要你呀,去你的吧!我也不张嘴!到看到你老婆还早哪。好吧。你愿意闭嘴就叫你闭个够吧!”
她把脊背靠在车厢边上,小声地唱起歌来。
葛利高里抬起头来,看了看太阳,无还早得很。愁眉苦脸地守在道旁的去年的蓟草的影子才有半步那么长;看来,至多也不过是下午两点钟。
草原像着了魔似的,一片死寂。太阳并不暖和。微风无声地吹动着晒红了的野草。四周连一声鸟儿叫、一声金花鼠的鸣声也听不到。冰冷、苍白的晴空中也没有老鹰在盘旋飞翔。只有一次,一片灰色的影子掠过大道,葛利高里还没来得及抬起头来,已经听见巨大翅膀的沉重煽动声:一只翅膀腋部在阳光中闪闪发光的灰色大雁飞了过去。落在远处的一座古垒边那里的一片太阳照不着的洼地与暗紫色的远景融合成一色。从前,草原上,只有在深秋的时候,葛利高里才会看到这种使人伤感的。深幽的寂静,他仿佛觉得听见被风卷起的风滚草沙沙地从衰草上滚过,在遥远的前方,横过草原。
道路好像是没有尽头的。它婉蜒曲折,时而下到深谷去,时而又爬上高岗。极目远望——四周围依然是那么一片沉默的大草原。
葛利高里在欣赏着沟坡上的一丛鞑靼树。械树的被初霜染过的叶子闪耀着烟灰色的光泽,很像是在叶子上撒了一层正在熄灭的火堆的炭灰。
“怎么称呼你呀,大叔?”赶车的娘儿们轻轻地用鞭杆触着葛利高里的肩膀,问道。
他哆嗦了一下,转过脸来朝着她。她却往一边看着。
“我叫葛利高里,你叫什么呀?”
“我叫‘无名氏’。”
“你还是闭上嘴吧,‘无名氏’。”
“我闭嘴都闭烦啦!闭了大半天,闹得嘴都干啦。你为啥这么不高兴呀,葛利沙大叔!”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呀?”
“回家去,就应该高兴嘛、”
“像我这样的年纪,高兴的时候已经过去啦。‘”
“瞧你,倒装起老头子来啦。你怎么年轻轻的,头发就白啦?”
“你什么都要问问……显然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好,所以头都白啦。”
“你结婚了吗,葛利沙大叔?”
“结婚啦。你呀,‘无名氏’,也要赶快再嫁才好。”
“为什么——要赶快呢?”
“因为你太贪玩啦……”
“这难道不好吗?”
“有时候不好。我认识一个这样放荡的娘儿们,也是寡妇,她只顾放荡啦,可是后来她的鼻于就塌啦……”
“哎哟,主啊,太可怕啦!”她玩笑地惊叫一声,立刻又一本正经地补充说:“我们寡妇的事儿就是这样;你要怕狼,那就别到树林于里去。”
葛利高里瞥了她一眼。她咬着细白的牙齿,无声地笑了。往上翘着的上嘴唇哆嗦着,眼睛在低垂的睫毛下顽皮地闪烁着。葛利高里不由自主地笑了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热乎乎的滚圆的膝盖上。
“无名氏‘,你真是个命苦的女人!”他惋惜地说。“你才活了二十岁,可是生活却已经把你折磨成这样子啦……”
突然她脸上喜悦的神色烟消云散。她严厉地推开他的手,皱起眉头,气得满脸通红,连鼻梁上浅浅的雀斑都看不出来了。
“等你回到家里,去怜惜你的老婆吧,没有你,可怜我的人已经够多啦!”
“你别生气嘛,你听我说!”
“好啦,见你的鬼去吧!”
“我是可怜你,才这样说的。”
“你带上你的可怜见他妈的鬼去吧……”她像男人一样熟练习惯地骂道,变得暗淡的眼睛眨了一下。
葛利高里扬起眉毛,不知所措地嘟嚏说:“你骂得太狠啦,没有说的!看你这个放荡劲儿。”
“那你呢?穿着长满虱子的军大衣的圣人,是的,就是这样的玩意儿!我看透你们这些家伙啦!嫁人吧,这个那个啦,你变成这么规矩的人已经很久了吗?”
“不,没有多久,”葛利高里笑嘻嘻地说。
“那你于吗要跟我谈这些清规戒律呀?这种事儿自有我婆婆来管。”
“好啦,够啦,你生什么气呀,胡涂娘儿们?我不过是随口这么说说罢啦,”
葛利高里用妥协的口气说。“你瞧,我们只顾说话,牛都离开正路啦。”
葛利高里在车上躺躺舒服,疾眼瞥了这位快乐的寡妇一下,只见她的眼睛里泪水盈眶。“这真是莫名其妙!这些娘儿们总是这样……”他感到某种内疚和惋惜之情,想道。
他就仰面躺在车上,用军大衣襟蒙上脸,很快睡着了,直到天快黑了才醒过来。
天上闪烁着苍白的、暮色苍茫中的星星。一股令人感到新鲜、喜悦的于草气味。
“该喂喂牛啦,”她说。
“好吧,在这儿停下吧。”
葛利高里亲自卸下牛来,从背包里掏出一个肉罐头和面包,折了一堆干艾蒿抱过来,在离车不远的地方燃起火堆。
“好啦,‘无名氏’,请坐下吃晚饭吧,别生气啦。”
她坐到火边来,一声不响地从口袋里抖出来一块面包和一块由于日子太久长了毛的腌猪油。吃饭的时候,他们说的话很少,而且很和气。后来她躺到车上,葛利高里为了不让火堆熄灭,往火里扔了几块于牛粪,像行军的时候一样,就在火旁躺下。他枕着背包,躺了半天,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胡乱地想着孩子和阿克西妮亚,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是被女人温柔的声音惊醒了:“喂,老总,你睡了吗?
睡着没有呢?“
葛利高里抬起头,只见他的同伴正用胳膊撑着身子,从车上探下头来。她的脸被逐渐熄灭的火堆摇晃的红光一照,显得那么鲜艳。清秀,牙齿和头巾的绣花白边闪着耀眼的白光。她又笑了,就像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口角似的,她抖动着眉毛说:“我怕你在那儿冻坏了。土地上很凉啊。如果冷得厉害——就到我这儿来吧。我有一件非常非常暖和的大皮袄!你来不来呀?”
葛利高里想了想,叹了口气回答说:“谢谢啦,姑奶奶,我不想去。如果是在两年前……别担心,在火旁边大概不会冻坏的。”
她也叹了口气说:“好吧,随你的便吧,”然后用皮袄盖上了脑袋。
过了一会儿,葛利高里站了起来,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他决定步行回家,要在天亮以前赶到鞑靼村。他,作为一个复员回来的指挥员——白天众目睽睽,坐着牛车回来,简直是不可想像的。这么回家会引起多少嘲笑和议论……
他把赶车的娘儿们唤醒:“我要步行走啦。你一个人在草原上不害怕吗?”
“不怕,我又不是胆小鬼,而且这儿离村子很近。怎么,你受不了啦?”
“你猜对啦。好,再见,‘无名氏’,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原谅!”
葛利高里走上大路,支起了军大衣领于。初冬的小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又刮起了北风,吸着冷冽的寒气,葛利高里闻到了熟悉的、沁人心肺的初雪的气味。
傍晚,科舍沃伊从维申斯克回来了,杜妮亚什卡从窗户里看到他来到大门口,急忙把头巾被到肩上,跑到院子里。
“葛利沙今天早晨回来啦,”她站在板门日,担心、期待地望着丈夫说。
“祝你快乐,”米什卡矜持地略带着玩笑日吻地回答说。
他紧闭着嘴唇,走进厨房、颧骨下面的小瘤子直颤动。波柳什卡坐在葛利高里的膝盖上,姑姑给她换上了干净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葛利高里把孩子轻轻地放在地。上,走上去迎接妹夫,他含笑把黝黑的大手伸给科舍沃伊。他本想拥抱米哈伊尔,但是一看米哈伊尔那没有笑容的眼睛里的冷漠和敌视的神情就变了主意。
‘叩阿,你好啊,米沙!“
“你好。”
“咱们有多么久没有见面啦!好像有一百年啦。”
“是啊,好久啦……祝你平安到达、”
“谢谢。咱们成了亲戚啦,啊?”
“真是,天意如此……你的脸上怎么有血啊?”
“没什么石U 脸划破的,太性急啦。”
他们在桌边坐下,默然相视无语,彼此都感到很尴尬、疏远。他们需要进行一次重要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