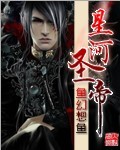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第20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尼库什卡啐着、骂着,走开了。
他俩的争吵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但是总的来说,连队过得和和气气。除了司捷潘。阿司塔霍夫以外,全体哥萨克都吃得饱饱的,情绪满不错。
司捷潘不知道是听同村人说的,还是心里觉得,阿克西妮亚在维申斯克常跟葛利高里见面,但是他突然苦闷起来,无缘无故地跟排长争吵了一场,而且坚决拒绝去站岗放哨。
他整天地蜷伏在土屋里的打有烙印的黑车毯上,唉声叹气,拼命地吸自家种的叶子烟。后来,听说连长要派阿尼库什卡到维申斯克去领子弹,他才两天来第一次走出了土屋。他眯缝着泪汪汪的、由于失眠而红肿的眼睛,疑疑惑惑地打量了一下摇曳着的树上乱蓬蓬的。鲜艳夺目的叶子,看了看被风吹得涌立起来的、镶着白边的云彩,听了听树林子的风声,就走过一间土屋去寻找阿尼库什卡,当着哥萨克们的面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把阿尼库什卡叫到一边,央求道:“到了维申斯克替我找找阿克西妮亚,把我的话告诉她,叫她来看我。就说我浑身长满了虱子,衬衣和脚布都没有洗,顺便再告诉她……”司捷潘沉默了一会儿,胡子里隐藏着难为情的笑意,说道,“就说,我非常想她,盼她快点儿来。”
夜里,阿尼库什卡到了维申斯克,找到了阿克西妮亚的住所。自从跟葛利高里发生口角以后,她又住到姑母家去了。阿尼库什卡好心地把司捷潘的话转达了,但是为了加重话的分量,他自己又加上了几句,说司捷潘讲啦,倘若阿克西妮亚不到连队去,他就要亲自到维申斯克来。
她听完丈夫的训示,就收拾准备起来。姑妈急忙发了一块面,给她烤了些奶油点心,过了两个钟头,阿克西妮亚——听话的妻子——已经跟着阿尼库什卡坐车去鞑靼村连队的驻地了。
司捷潘暗自高兴地迎接了妻子。他用探索的目光仔细观察她那瘦削的脸,小心翼翼地问她一些话,但是一句也没有问及她是否看见过葛利高里。只有一回,谈话的时候,他垂下眼帘,略微扭过身去,问道:“你为什么走那岸去维申斯克呢?为什么不就在村边过河来呢?”
阿克西妮亚冷冷地回答说她不能跟外人一块儿过河,可是又不愿意去求麦列霍夫家的人。等到回答完了,她才发现自己说的话很不得体,好像她认为麦列霍夫家的人不是外人,成了自己人。她怕司捷潘也会这样理解,不由得窘急起来。而他大概也正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眉毛下面哆嗦了一下,脸上仿佛掠过了一片阴影。
他疑问地抬起眼睛看着阿克西妮亚,她也明白了这个无声的问题,突然由于窘急和恼恨自己,脸涨得鲜红。
司捷潘可怜她,装作什么也没觉察的样于,把话题转到家务事上去,开始询问她在离开家以前,把家里的东西藏起了些什么,藏得保险不保险。
阿克西妮亚看到丈夫对自己如此宽宏大量,回答了他的询问,但是总觉得内心很尴尬,于是为了向他表明,他们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很无聊的,而且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故意把话说得慢条斯理,露出一副正经、矜持和冷漠的神情。
他们坐在土屋里谈话。总有哥萨克来打扰。忽而这个进来,忽而那个又进来。
赫里斯托尼亚走进来,就地打铺睡起觉来。司捷潘看出要想单独跟老婆说说话儿不成了,就很不情愿地停止了谈话。
阿克西妮亚高兴地站起身来,匆匆解开包袱,拿出从镇上带来的奶油点心请丈夫吃,然后从司捷潘的军用背包里拿出脏衣服,走出土屋,到附近的池塘里去洗。
黎明前的寂静和蓝色的雾笼罩在树林上空。露水很重,压得青草都贴到地面上。
青蛙在湖沼里哇哇乱叫,离土屋很近的一丛浓密的枫树林后面,有只长脚秧鸡在吱吱地鸣叫。
阿克西妮亚穿过树丛。树丛,从树顶到深藏在茂密的野草里的树于上,都结满了蜘蛛网。凝结在蛛丝上的露水珠,像宝石似的闪闪发光。长脚秧鸡一时不叫了,可是立刻,——阿克西妮亚的光脚踏倒的草还没有来得及挺直,——又叫了起来,一只从湖沼里飞起的田枭伤心地回应着它的鸣声。
阿克西妮亚把短上衣和紧身的背心脱下来,走进没膝深的、温暖的湖水里,洗起衣服来。蠓虫在她头上飞舞,蚊子嗡嗡叫着。她不住地用弯起的丰满、黝黑的手臂在脸上抹抹,驱赶蚊子。她断断续续地想着葛利高里,想着在他去连队视察前他们之间发生的最后一次口角。
“也许,他现在正在找我呢?今天夜里我就回镇上去!”阿克西妮亚下了决心,心里想着怎么跟葛利高里见面,而且立刻就会和解,不由得心花怒放。
怪得很:近来,她想到葛利高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她眼前出现的不是现在的这个葛利高里:身材高大、英气勃勃,一个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哥萨克,他疲惫地眯缝着眼睛,黑胡子尖已经有点儿发红,两鬓有了过早的白发,额角上布满了粗纹——这都是在战争年代受到摧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而在她眼前出现的却是从前的那个葛利什卡。麦列霍夫,一个粗卤的、不会体贴人的小伙子,生着孩子似的圆圆的细脖子,嘴唇上总是挂着乐观的、无忧无虑的笑容。
正因为这样,阿克西妮亚就更加爱他,几乎是一种温柔的母爱。
就是这会儿,她脑子里仍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张令人无限爱怜的脸,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笑了笑,挺直身子,把没有洗完的丈夫的衣衫扔到脚下,觉得喉咙里有一股突然涌上来的、要尽情地哭一场的热气,低声自言自语道:“该死的东西,你附到我身上了,一辈子也甩不开你!”
眼泪使她心里轻松了一点儿,但是在这以后,她周围蔚蓝的清晨世界,仿佛黯然失色。她用手背擦了擦脸颊,从泪水满面的额角上把头发撩到后面,脑子里空落落的,用黯然失神的目光,呆呆地注视着一只灰色的小鱼鹰从水面上滑过,消失在被晓风吹得上下翻滚的粉红色晨雾中。
她洗完衣服,晾在树枝上,然后走进了土屋。
已经醒来的赫里斯托尼亚正坐在门口,拼命缠着和司捷潘说话,而司捷潘躺在车毯上,默默地抽着烟,根本不回答赫里斯托尼亚提出的问题。
“你以为红军不会过河到这边来吗?你不做声?哼,你就不做声好啦。不过我以为他们一定要从浅水地方胜水过河……一定会过河!除此以外,他们再没有法子过河啦。也许你以为他们会用骑兵过来?司捷潘,你怎么不说话呀?要知道,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可是你还像傻瓜一样,躺在那里!”
司捷潘一下子跳起来,激动地回答说:“你没完没了地瞎缠什么呀?真是个怪物!好不容易老婆看我来啦,可怎么也甩不开你们……死缠着你,说蠢话,不让人家跟娘儿们说句话!”
“倒了大霉啦,找了个你这样的人说话……”赫里斯托尼亚扫兴地站起身,光脚穿上破靴子,脑袋撞在门框上,疼得够呛,走了出去。
“没法儿在这儿谈话,走,咱们到树林子里去,”司捷潘提议说。
他也不等到同意,就朝出口走去。阿克西妮亚驯顺地跟着他走出去。
中午,他们回到土屋里来。第二排的哥萨克们正躺在赤杨树荫里乘凉,一看到他们,都放下手里的牌,一声不响,会意地互相挤眉弄眼、窃笑,故意唉声叹气。
阿克西妮亚很轻蔑地撇着嘴,从他们面前走过,一面走,一面整理着头上揉皱的白绣花头巾。哥萨克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她从身边走过去,但是等跟在后面走的司捷潘刚走到哥萨克们跟前,阿尼库什卡就从躺着的人堆里站起来,走出几步。他假装恭而敬之的样子,向司捷潘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声嚷道:“恭喜您……开荤啦!”
司捷潘高兴地笑了。哥萨克们看见他和妻子一同从树林子里回来,这使他高兴。
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些说他们夫妻不和的流言不攻自破……他甚至还很潇洒地耸了耸肩膀,得意地显摆着背上还没有干的、汗湿的衬衣。
直到这时候,受到鼓舞的哥萨克们才哈哈大笑着,热闹地大谈特谈起来:“弟兄们,这个娘儿们可真够劲啊!你们看,司乔普卡的衬衣像从水里捞出来……全都沾在肩肿骨上啦!”
“她已经把他弄得筋疲力尽,浑身冒汗……”
一个年轻小伙子用模糊、赞赏的眼神一直把阿克西妮亚目送到土屋前,失魂落魄地嘟哝道:“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娘儿们啦,真的!”
阿尼库什卡不无道理地质问道:“你可曾去找过?”
阿克西妮亚听到这些下流话,脸色微微发白,想起刚才跟丈夫亲热的事儿,再听到丈夫同伙的淫秽的说笑,就厌恶地皱起眉头,走进土屋。司捷潘一眼看透了她的心事,就宽慰说:“克秀莎,你别生这些公马们的气。他们这都是因为太寂寞啦。”
“我生谁的气啊,”阿克西妮亚在自己的麻布口袋里翻腾着,闷声回答说,急急忙忙把带给丈夫的东西都掏了出来。然后,声音更低地说:“应该生我自个儿的气,可是,没有心气啦……”
他们话不投机。过了十来分钟,阿克西妮亚站起来。“现在就对他说,我要回维申斯克去,”她心里想,但是立刻又想起晒干了的司捷潘的衣服还没有收进来。
她坐在土屋的门口,缝补了半天丈夫沤烂了的内衣,不断地抬头看看渐渐偏西的太阳。
……这天她竟没有走成。下不了决心。但是第二天早晨,太阳刚一出来,她就准备上路了。司捷潘试着挽留她,央求她再住一天,但是她那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使他死了心,只是在分别的时候,才问道:“你打算在维申斯克住下去吗?”
“暂时还要住在维申斯克。”
“你是不是可以留在我这儿呢?”
“在这儿我可受不了……这些哥萨克。”
“话是不错……”司捷潘虽然同意她的说法,但是却很冷淡地跟她分别了。
刮着强劲的东南风。这是从远方刮来的风,刮乏了,夜里风势减弱了些,但是到清晨,又把里海以东沙漠上的热气吹来,吹倒了左岸河滩地上的青草,吹干了露水,刮散了晨雾,顿河沿岸的灰白色的山峰笼罩上一层令人气闷的粉红色热气。
阿克西妮亚脱掉靴子,用左手撩起裙襟(树林子里的草上还有露水),轻松地走在林中荒芜的道路上。湿润的土地凉丝丝的,使她的光脚很舒服,但是旱风却用到处乱伸的热嘴唇亲吻着她那丰满的光腿肚和脖颈。
在一片开阔的林间空地上,她在一丛盛开的野蔷薇旁坐下来休息。几只野鸭在不远地方的一片还没有干涸的池沼里的芦苇丛里啪啪叫着,一只公鸭正在沙哑地呼唤母鸭。顿河对岸,虽然不是连续地,然而几乎是不停顿地打着机枪,偶尔还有大炮的轰鸣声。炮弹在这边岸上的爆炸声像回声一样轰隆轰隆地响着。
后来,枪炮的射击声减弱了,时有时无,一片充满了神秘声音的世界展现在阿克西妮亚眼前:背面白色的白蜡树绿叶和像铁铸的、镂花的橡树叶子被风吹得哆哆嗦嗦地沙沙作响;从小白杨树林里飘来混杂的嗡嗡声;远处有一只布谷鸟正在模糊不清地、伤心地对谁诉说着自己未来的凄凉岁月;一只从地沼上空飞翔的凤头田枭不停地叫着,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