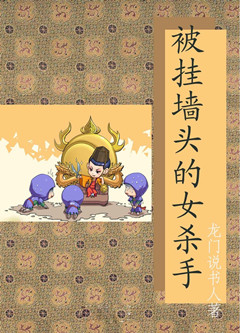杀手-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会意地点点头,将礼帽戴上。
她将放在茶几上的手枪递给他,他不接:“这东西我用不着的。”
她看了他一眼:“它的有效射程三十米。”
他说:“白小姐,各种兵器的性能,相信我比你清楚。”
她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上前挽了他,走出化妆室。
后门有几个便衣巡捕(也称侦探)在把守着,他们一见白光与李坚相挽而来,便迎上去搭讪:“白小姐,这么早就退场了?”
白光见巡捕凑过来,便挥手说:“不许靠近!都躲我远点!”
巡捕见李坚步履蹒跚,便讨好地说:“白小姐,这位先生是喝多了吧?我来帮你扶他上汽车,好吗?”
白光挥手制止:“不用!都闪开!”她快步出了后门,走向停在一旁她的银色福特牌轿车。先将李坚送入车内,再坐上驾驶座。
几名便衣巡捕远远跟着,眼见白光驾驶着轿车绝尘而去。
轿车来到静安寺路一幢花园洋楼门前,一个印度人门卫出来拉开铁栅栏大门,轿车开进花园,直抵小洋楼前。
一女佣人从楼内迎出,拉开车门。白光和李坚下了车。
白光领着李坚登楼,进入小客厅。她对女佣人说:“先弄一壶咖啡来,再去厨房弄夜宵——要多弄一些。”
女佣人很快端来托盘,一壶咖啡、一听炼乳、两只玻璃杯。她将托盘放在茶几上,倒了两杯咖啡,并在每杯里加了一些炼乳。
白光对李坚说:“她叫阿兰,有什么事吩咐她去做。阿兰,这位是先生,以后你就专门侍候先生吧。”
阿兰朝李坚鞠躬:“先生!”
李坚颇为尴尬,只“啊”了一声。
阿兰走后,白光对李坚说:“你大概要在家里住些日子,等我去向领事说明,撤销对你的通缉令,你才好外出活动。”
李坚说:“我并没有违犯租界法,又不承认我们是战俘,他们通缉我是没有道理的!”
白光笑道:“孤军营在租界当局软禁中,你脱离孤军营,他们自然要找你,抓回去继续软禁;你在华界杀了人,就成了危险人物,他们更有理由通缉你了……天锋,这是强权时代,没有公理可言。
“你离开孤军营二十余日了,都怎么过来的?能告诉我吗?”
李坚叹了一口气:“说来话长……啊,时间不早了,你要休息了吧?我们明天再说……”
白光笑道:“我是过夜生活的。每晚华灯初上我去百乐门,拂晓才回来睡觉。一觉睡到过午……周而复始,天天这样。现在还是午夜,遇见你更是精神亢奋,哪里睡得着啊?
如果你还不困,就陪我先聊聊吧。”
李坚点头说:“也好,就先聊聊吧。”
“我离开孤军营,并没有落脚处,只在街上闲逛,晚上露宿在街头。过了两天,得知工部局在寻找、搜捕我,在租界待不下去了,我只好进入华界。
我在老西门发现一个叫张小毛的汉奸,在讹诈一家商店,气焰十分嚣张,我就决心先锄掉这个汉奸!
我尾随这个汉奸,摸清了他的落脚处,准备好当夜动手……”
①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八百壮士,最后孤立无援,被迫退入租界,被租界当局软禁于上海胶州公园。称之为“孤军营”。
②指租界外的华界。因为租界是在原上海城外郊区建设发展起来的。
二、黄埔锄奸队
子夜。
在小南门一条弄堂里,两侧是旧式的矮楼房,弄堂没有路灯,深夜住户都已熄灯就寝,没有半点光线,幽长的弄堂漆黑。
一条黑影悄悄在弄堂里移动着。
有一户二楼的窗户还透出灯光。黑影来到灯光楼下,一纵身抓住了晾台边缘。一个倒提,翻身进了晾台,身手矫捷,动作无声。
此时室内正是张小毛在与姘头阿桂一边吃喝,一边说着话。
张小毛边喝酒边自夸:“现在上海滩是东洋人的天下;南市区就是阿拉张小毛的天下。明朝我带侬去老面门银楼,侬随便挑好了,只要我讲句言话,伊就勿敢要钞票!”
阿桂似信非信:“会有这样好事情啊?”
张小毛拍拍放在桌旁的盒子枪:“伊倷(他们)勿识相,我就捉伊老板去宪兵队!”
阿桂大喜过望:“真的?明朝一定要带我去的,勿兴黄牛啊!”
张小毛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金牙。“想去吧?侬今朝让我白相①适意了,明朝我就带侬去。”
阿桂笑骂:“侬这只死鬼呀,求侬一眼眼②事体,就要讲条件!好,就依侬。”
张小毛说:“侬脱光了去跪在床边上,我今朝耍白相新花样!”说着他脱着衣裤。
阿桂嘴里还在骂着:“侬这只死鬼呀,花头精③蛮多的,日日要翻新!”虽这样骂,她还是脱光了,去床沿上跪着,趴下身去,将肥臀撅得高高的。
张小毛走上去,先在女人身上摸捏一阵,将女人弄得浪笑怪叫……
翻进晾台的人正是李坚,他趁二人正在忘情之时潜入室内,来到正在疯狂冲击的张小毛身后,举刺刀扎进张小毛的后心,刀尖从前心透出。张小毛猛地朝前一扑,将趴着的阿桂扑倒,那透出前心的刀尖,扎入阿桂的后心,但并不深,所以她喊叫起来。
李坚向刺刀砸了一拳,趴在张小毛身下的阿桂一阵抽搐,不再动弹了。
李坚奋力拔出步枪刺刀,一股黑红色的血从张小毛背部喷出。李坚闪身躲过。少顷,他将刺刀上的鲜血,在床单上抹干净,撕了一块布,蘸上张小毛和阿桂的血,在床头墙上写了两行大字:
汉奸下场!
黄埔锄奸队
写完后他将刺刀还插在绑腿内,转身将桌上张小毛的盒子枪从盒子内拔出,别在腰间。又见张小毛的腰带上拴着一个钱袋,翻出一大沓钞票,这就是张小毛日间从店铺里讹诈来的。他现在正需钱用,就将这不义之财揣入兜内。
他仍然从晾台回到弄堂里。正要举步往外走,忽听开门声,他忙闪身藏在黑暗处。只见从一扇门内,走出一个人来。此人叼着香烟,一点火星在移动着,移动至墙边。火星移动的同时又听见一阵洒水、咳嗽、吐痰和关门声。
李坚知道,上海一些巷子里都有小便池,附近居民乃至路人男士,都可以公然在此小便,即使有女士路过,对此也熟视无睹。刚才那人,就是附近起夜的居民。
他走出弄堂,来到大街上。
南市区老西门一带原本比较繁华,可在鬼子的铁蹄下,恐怖气氛弥漫,入夜市民便不敢出门口。所以深夜街头不见人影。
他尚无固定住处,多是露宿在一些石窟的门洞里。今夜如何度过?他茫然四顾,信步往前走。
他走了一阵,发现一块路牌“陆家浜路”。他曾经随部队在这一带作过战,还记得地形。不远处是海潮路,那里有一座庙,叫海潮寺。他听老百姓说,上海开战前,有位姓金的在庙里办了一个“金龙武馆”;开战后此庙遭日寇轰炸,已是残墙断壁。他想那里倒可以暂且栖身,于是朝海潮路走去。
这一带是平民区。马路两侧都是矮房,还有一些草棚子。居住着工人家庭。
虽是黑夜,李坚的军人素质练就了他对地形的记忆力,便沿着马路走去。
万籁俱寂的深夜,忽然传来女子的呼救声。李坚站住了,迅速辨明喊救声的方向,便毫不犹豫地循声奔过去。
李坚奔近一看,只见两个头戴钢盔、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鬼子兵,正架着一女子,往庙里拖拽。他从后面冲上去,左手臂扼住一鬼子兵脖子,右手一掰鬼子兵的脑袋,嘎巴一声,折断了脖子,他一松手,鬼子兵坐倒下去。另一鬼子兵对这突然出现的情况尚未反应过来,他扑上去将鬼子兵扑倒,铁钳般的手,卡住了鬼子兵的脖子;鬼子兵挣扎了几下,蹬蹬脚,再也不动弹了。
李坚站起身来,见那女子在发愣,便提醒道:“啊,这里是是非之地,你快走吧。”
那女子这才清醒过来:“先生,这两个鬼子兵死在这里,明天被鬼子发现,会给这一带居民带来祸事的呀。”
李坚说:“我将他们拖进庙里埋起来吧。”
女人说:“没有工具怎么埋呢?请你在此等候片刻,我家就住在海潮路,我回家叫我的丈夫拿了工具来帮你吧。”
李坚说:“好吧。我将鬼子兵尸体先弄进庙去,我在庙里等你。”说罢将鬼子兵的两支步枪挂在脖子上,一手一个,抓住两个鬼子兵的腰带,提了起来,走进庙去。
女人看了李坚的神力,惊呆了半晌。
李坚将两具尸体扔在遍地瓦砾的院子里,去坐在廊下休息。
这座庙大殿遭到炸弹轰炸,已经倒塌,但两侧厢房,还有部分是完整的。
李坚在四周转了一圈,见两侧尚有两间房间,虽门窗都已损坏,墙壁、屋顶倒还完好。他想:这里倒是夜间安身之处,虽无门窗,也能遮风挡雨,比露宿街头强多了。
那女人带着两个男人进庙来了。
女人向李坚介绍,高个子身材魁梧的叫沙志超,是她的丈夫;另一个叫陆阿根,是她的表哥;她叫杨佩云。她问李坚姓名?
李坚含糊地答道:“我姓张,单名强字。”
沙志超和陆阿根对李坚说了些表示感激相救的话。
沙志强说:“这院子的中间,原有一个花坛,土质较松软,比较好挖掘。就在这里挖个深坑,把鬼子兵埋下吧。”
李坚同意。
四人将中心地上的瓦砾清除,果然露出土地。沙志超带来铁锨和镐。三个男人轮流挖掘,很快挖成一个两米长、一米多宽、一人深的坑。
李坚说:“这俩鬼子有两支步枪、八枚手榴弹。步枪太长,不好收藏,就都埋下吧。”
陆阿根说:“都交给我吧,我能收藏好。”
李坚没说什么,就将俩鬼子兵的尸体扔进坑去。三人一起填土。为了填实,他们几乎填一层土,便跳下坑去一阵踏踩,达到夯实的目的。
填完坑,再将瓦砾撒在上面,恢复原貌。
李坚说:“现在不露痕迹了,三位请回吧。”
杨佩云问:“张先生,你要去哪里?”
李坚说:“我就在这庙里忍一宿,明天再说吧。”
“那怎么行呢?我家离此不远,请到我家去住下吧。”
李坚再三推辞,那三人固请。李坚想自己在上海无亲无友,去认认门也是好的,就随主人来到海潮路。
杨佩云家住在海潮路十七弄二号。这条弄堂只有一号、二号两个门牌。二号战前是南洋印刷厂的厂房,是一幢三层楼房。一号是厂主方寿山的住宅两层楼房。抗战爆发,印刷厂倒闭,厂房搬进十几家住户。
十七弄这两幢楼房,是这一带最突出的建筑物,周围都是矮平房或草顶房。
杨佩云家住二楼两小间。
杨佩云的母亲陆雅菊是位中年妇女,战前在服装厂当女工,现在弄堂摆摊,为附近居民做衣衫兼缝补。她已知道李坚是救她女儿的恩人,所以热情招待。
众人坐定交谈。杨佩云在灯光下仔细观察李坚,忽然说:“张先生,我觉得你好面熟呢……我越看你越像一个人……”
李坚暗暗吃惊:“不会吧……”
杨佩云:“我去孤军营慰劳十多次了——我看你像孤军营的李连长!”
沙志超和陆阿根听了,也都仔细端详,竟然异口同声:“是的——你是李连长!”
李坚被对方识破,也不便否认。又因在庙里挖掘干活时,一边聊着天,他已知道沙志超和陆阿根战前是翻砂厂工人,战后工厂倒闭二人以踏三轮车谋生;杨佩云是纺织厂女工,也失业在家。这些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