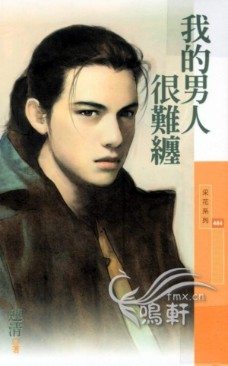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天,妙妙带着她自己烤的蛋挞来看我。我宿醉醒来,正饿得两眼发绿,捻指间吃掉半打。
妙妙目瞪口呆:“你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 “我过得挺好的。”我顺手开了一罐可乐。 “好什么,跟猪似的。”妙妙说话从来不留情面。 我脸一红。
“一个我认识的姑娘去世了。”我低声说,好像隔墙有耳一样。 “啊! Sorry。” “没什么,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我还骂过她呢。”
“我听不懂——那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我笑了:“你不用懂。我也不懂你,每天忙得跟三孙子似的,你怎么反倒比我精神?”
“我哪儿有时间不精神?贺岁档是大役。” 贺岁档。又是一年年末了。
妙妙给了我一张入场券,是一部下个月上映的片子:“请你看电影, 今晚的媒体看片会。”
“我又不是媒体的人。” “帮帮忙不行吗?这个片子是我负责发的,我需要十篇影评,可我实在没时间写。” “十篇!”我喊出来,“写不动。” “别装蒜,上学的时候你没赶过影评作业?” “那也是十部片子写十篇,没有一部片子写十篇的。” “给你稿费。”
“不缺。” “千字五百。” “谢谢。”
“哎,市价是千字三百的,差价可是从我的奖金里补!” “你千字二百去雇个学生嘛,还能省下一百呢。” “他们没你写得好。”
“真的?” “你以为我牺牲宝贵的午休时间来看你,是跟你逗闷子呢?” 我吃饱了,可乐也下肚,精神开始抖擞起来。我打量着妙妙因为劳累过度而积下的黑眼圈,似乎她不是在开玩笑。
当天晚上的看片会和路雯珊的生日聚会的时间是重合的,我没有去路雯珊家。因为刚好赶上晚高峰,我挤了七站地铁赶到在金宝街的电影院, 吃着英总发的汉堡,听说隔壁路家的宴会排场十分奢华。路家的酒店上市了,庆功宴和生日宴一起做,城中名流都在,电影里的男女一号也在。
看完电影,上百个人挤在路边等出租车,我穿得太少,冷得受不了, 一路小跑进地铁站。经过路雯珊家的酒店门口,一排超跑刚好亮起雪亮的前灯,晃得我睁不开眼睛。盛装的路雯珊送客人出来,她见到我,喊我的名字,说宴会还没结束,快点儿进来喝一杯。我一面怕错过地铁的末班车,一面惦记着十篇稿子,摆摆手又跑了。
我熬夜写稿,到凌晨五点写完了五篇,打包发到妙妙的邮箱里,告诉她剩下的五篇二十四小时之内给她。甩着酸疼的胳膊站起来,看到东方的天蒙蒙地发了白,往常这个时候,我刚刚睡眼朦胧地从梦会所走出来。
妙妙迅速回了邮件,叮咚一声:“辛苦。天亮了,快去睡。” 我一头扎在枕头上,黑甜一觉,踏实无梦。
~3~
我当然不肯要妙妙的稿费,作为答谢,她请我喝下午茶。 说是请我喝茶,其实是帮她忙中偷闲。她当天在采访一个演员,演员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离开,这一个小时她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吃着点心聊聊天。 我看着妙妙整理着采访录音,心里不是没有羡慕的。这个演员是梦会所的常客,我们熟悉到见过对方大醉呕吐的样子。 可是也仅限于此。
我听着录音里她逻辑清晰、活泼乐观的声音,那是工作时的状态, 她只会展现给妙妙,我和她再熟悉,也无缘听到。
后来我听到一阵尖叫,回头看,一行人簇拥着一个高个子的黑人从包厢里走出来,然后我也叫出声来:是马布里。
我和妙妙扒着咖啡厅的窗子,眼巴巴地看着马布里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商务车。他身后的人们返回咖啡厅,打开电脑开始写稿,看样子是一群刚做完群访的记者。
“妙妙,我要老马的签名。” “阿拉是电影圈儿的,不是体育圈儿的。” “都是媒体圈啊!”我特不忿地看着那群记者,他们也在整理录音呢。 “隔行如隔山哪!” 那群记者回头看我们,然后一个人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是小周。
是了, 他上次 还把陈 白露带 到工体的 媒体席 上看足 球, 他是体 育记者。
小周把马布里给他签了名的球衣送给我,又把同事那一份要来送给妙妙。妙妙要赶回公司,我们同他们告别,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然后小周追出来,站在我面前欲言又止。
妙妙嘻嘻地笑:“告诉你同事,甭心疼,我回头还他一个林志玲用过的杯子。”
小周窘得满脸通红:“不用不用。”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呀。” “我想送陈白露一个新年礼物,可是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我心里一动。两年前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那个人眼中的迷恋胜过小周十倍,可是他现在在哪儿呢?在法国的葡萄园里整修酒窖,漂洋过海,费尽周折,只为了离她越远越好。
“别傻了。”我笑笑。妙妙拦下了出租车,在我们上车之前的一秒钟, 她把两件球衣都塞回小周怀里,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拉着我坐进去,关上车门。
车一路滑过街道拐角,小周的身影消失在后视镜里,我不解:“为什么把球衣还回去?”
“早知道这小哥对陈白露有意思,我当时就不会要。陈白露才不会看上他,别替她拿人家手短了。”
“小周挺好的呀。” “陈白露那眼睛长到头顶上的样子你看不到?” “那是很久以前。她现在讲话柔声细气,不是以前咄咄逼人的德行。” 妙妙笑起来:“二十多年的棱角,哪里那么容易被磨平?那是因为伤透了心。” 我把妙妙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转眼到了平安夜,我请陈白露来我家住一天,她答应了。
~4~
我像准备王妃省亲一样准备迎接她久违的回归,打电话给付师傅, 让他送一些吃的过来。付师傅有些激动,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办过party, 也很久没有找过他了。他问我要准备多少人的吃食,二十个还是三十个, 要不要多备上一倍,因为从前的经验是每个客人都会呼朋唤友,无论准备多少都嫌不够。
“只有两个人,不用多,也不要新花样,只要新鲜就好。” “哟,陈言回来了?”付师傅在电话里压低声音,好像在打听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我很讨厌八卦的人,尤其是八卦的男人,尤其尤其,是八卦的中年男人。可是和一个厨师有什么道理好讲?我挂了电话,到楼下的超市买了一块牛腩,切成小块扔到锅里煮着,煮到满屋飘香,加了一把香菇和莴笋片,然后陈白露来了。
我边搅动着汤边看到一辆黑色阿斯顿马丁停在楼下,在灰扑扑的冬日黄昏里显得十分扎眼。陈白露从车上下来,穿着黑色的齐腰羊绒上衣, 领子敞着,修长的脖颈裸露在北风里。她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一样朴素而干净,只是面色更加苍白了。
“送你来的人是?” “薛先生。” 我没再问,她想告诉我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
她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眼神阴郁地看着我淘洗一把大米。
“他找过你吗?”
这个“他”只可能代指一个人。我摇头:“我前天见到了他妈妈,他们以为他在伦敦,他伦敦的朋友以为他在北京,其实他买下了酒庄以后, 住在里面不肯走。”
陈白露撇撇嘴:“纨绔公子,眼高手低是改不了的毛病。葡萄酒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
我沉默了。我没告诉她,这酒庄不是用来经营的;我没告诉她,它本来是要送给她的礼物。那些动人的许诺早就随着一次令人心碎的变故而变得没有意义,如今它同小汤山的别墅一样,成为他们流放自己的地方。 谁说陈白露是这场变故里唯一的受害者呢?我知道远在那座陌生酒庄里的陈言,并不比陈白露开心一分。
“我梦见很多人。”她的薄嘴唇颓丧地垂着,“我梦见高中时候的初恋男友,他教我投篮,可我一个也投不中;我还梦到勤务兵抱着我看装甲车训练,一辆黄色,一辆绿色;我梦到我的孩子,他长得很像我。可是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海棠,我厌倦了。”
我转身看着她,她乌黑的长发打着卷,披在苍白的脸颊上,长睫毛垂下来,覆着她微微斜吊的眼睛。
“你与世隔绝得太久了。再淡泊的人也不能一个人在郊外长年累月地住着。”我说。我咽下后半句:“何况你根本不是。”
“你的抱负呢,白露?”我感到惋惜。“你不知道我多怀念从前的你。 那时候你名声不好,路雯珊都敢当面骂你‘婊子’,可是你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现在呢,人们提到你,都说你是个可怜的姑娘,一片真心却遇上了不懂得珍惜的人。你的名声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过,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无精打采的好姑娘。” “我毁了。”她低声说,眼圈一红,“我振作不起来,海棠,我振作不起来。我不是没努力过。刚搬到郊区的时候,我的状态比现在还好一些, 那时候我以为时间能治好我,可是现在看来,大半年过去了,我只有一天比一天消沉。日子过得越清淡,往事就沉淀得越清楚:我自命不凡地过了二十二年,然后老天突然告诉我,不是每一个真心都有真心来回报, 也不是聪明和野心加在一起就能生成好结局,这些所谓的好品质都是一厢情愿地给自己贴金罢了,你瞧程雪粟,好好的一个姑娘,死后连葬礼都没有。对了,我去看过她一次。”
“什么时候?” “秋天。我去了她内蒙老家,你知道她是蒙古族吗?我是才知道,他们可以土葬。她埋在锡林郭勒草原上。” 我心里涌起无限悲凉。“没想到这么多朋友,最后有心去拜祭她的人竟然是你。” “人死如灯灭。活着的时候千好万好,死了也有人哭上一阵子,可是能哭多久呢,人人都忙着活自己的,也只有我这样没什么正事可做的人能记得久一些。我在她老家的村子里住了三天,还遇上一件奇事。”
“什么?” “村子里有一个老光棍,穷得很,种了两亩地的向日葵,我拜祭完程雪粟回来,刚好遇上警察把他带走,说是向日葵园子的中间种的都是大麻,被卫星拍到了。听说每年都有人从北京来提走,老头子干这一行有年头了。”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破事儿。”
陈白露低头一笑:“你还和以前一样。” “珍爱生命,远离黄赌毒。” “黄赌毒还不是你身边这些人捧起来的?那些挤地铁的小白领、卖菜的老阿姨还没资格呢。”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吃过饭我们去打牌好不好?” “刚说过远离黄赌毒。”
她哈哈地笑了起来:“好,干净人儿,快点儿把我从你的客厅里赶走吧。我身上的污点太多了,别连累了你。”
夜幕降临后,我和陈白露去了工体一家酒吧楼上的德州扑克擂台。 它是公开的、合法的,我一直很好奇在禁止赌博的内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外之地存在。它的布局是微缩的澳门赌场,连装修风格都很类似, 只是不以现金交易,赢家的回报是手机或者各种奢侈品——也许它正是因此而不算在赌博里面。
我德扑玩得很差,很快就输光了。我坐在陈白露身后看她玩牌,她的运气实在不好,但她把把使诈,使得不动声色。
陈白露所向披靡。 我猜如果陈白露不是一个年轻文静的姑娘,而是一个虬髯大汉,是绝不敢一路诈下去、随随便便把筹码推上去说“all in”的。她的欺骗性来自她瘦弱的外表。被她迅速榨干的对手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