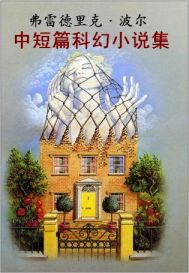博尔赫斯小说集-第5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我的作品,”他宣布说。
我察看那些画布,在最小的一幅前站停,画布上的图形大概是日落景色,意境无限深远。
“你喜欢的话可以拿去,作为一个未来的朋友的纪念,”他平静地说。
我向他道了谢,但是别的画布使我觉得别扭。我不能说它们是空白的,但和空白相差无几。
“你用老眼光是看不出上面的颜色的。”
他细长的手指拨弄竖琴琴弦,我几乎听不出什么声音。
那时候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高大的妇女和三四个男人进了屋。可以说他们是兄弟,或者年龄相仿,我的主人先对那妇女说话:
“我料到你今晚准来。你见过尼尔斯没有?”
“有时见见面。你还老画画。”
“但愿比你父亲画得好一些。”
手稿、图画、家具、器皿;家里什么都不留下。
那个女人和男人们一起搬运。我没有气力,帮不了他们的忙,觉得惭愧。谁都没有关门,我们搬了东西出去。我发现屋顶是双坡的。
走了十五分钟后,我们朝左拐弯。远处有一座塔形建筑,圆拱顶。
“那是火葬场,”不知谁说道。“里面有死亡室。据说发明者是个慈善家,名字大概是阿道夫·希特勒。”
守门人的身材并不叫我吃惊,他为我们打开铁栅栏。
我的主人嘟哝了几句话。他进去之前举手告别。
“雪还没有停,”那个妇女说。
我的坐落在墨西哥街的办公室里保存着那幅几千年后某个人画的画布,画布和颜料是当今世界通用的。
………………………………………………
阿韦利诺·阿雷东多
事情发生在蒙得维的亚,时间是1897年。
每星期六,几个朋友总是占着环球咖啡馆靠墙的那张桌子,正像那些正派的穷人一样,他们知道家里太寒碜,不能招待客人,但又想逃避自己的环境。他们都是蒙得维的亚人;一开始他们就觉得很难和阿雷东多搞熟,阿雷东多是从内地来的,不愿推心置腹,也不多问多说。他年纪二十出头;瘦削黝黑,身材要算矮的,动作有点笨拙。他的眼睛似乎睡迷迷的,但咄咄逼人,除此之外相貌十分平凡。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一家杂货店的店员,空余时间在学法律。当别人谴责战争,说战争替国家带来灾难,并且和大多数人一样说总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拖延战争时,阿雷东多一声不吭。当别人取笑他,说他吝啬时,他也不言语。
白山之役后不久,阿雷东多对伙伴们说他有事去梅塞德斯,要离开一个时期。这个消息没有使谁感到不安。有人提醒他,对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的高乔兵要多加小心啊雷东多笑笑回说他不怕白党。提醒他的人支持白党,不再说什么。
他同女朋友克拉拉告别时难分难舍。他说的还是那些话,不同的是,他说此去很忙,不会有空给她来信。克拉拉本来不喜欢写信,对这也没有意见。他们两人感情很好。
阿雷东多住在郊区。有个黑白混血女人伺候他,大战时期①,那女人的父母是阿雷东多家的奴隶,因此沿用了主人的姓。那女人十分可靠;阿雷东多吩咐她,不管有谁找他,就说他在乡下。他已经领了杂货店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①指乌拉圭总统里韦拉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1839至1852年间的战争。
他搬到后面泥地院子的一个房间。这个措施毫无用处,不过帮助他开始了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幽禁生活。
他恢复了午睡的习惯,躺在狭窄的铁床上有点悲哀地望着空空的搁板。他把书全卖了,连法学入门的书也没有保留。他只剩一部《圣经》,以前从未看过,这次也不会看完。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有时很感兴趣,有时又觉得腻烦,他强迫自己背出《出埃及记》的某些章节和《传道书》的结尾部分。他不想弄懂所看的东西。他是自由思想者,但每晚睡觉前必定要念祈祷文,来蒙得维的亚之前,他向母亲保证这样做,违反当儿子的诺言可能会给他带来厄运。
他知道他的目标是8月25日上午。他知道还要熬过的日子的确切数目。目标一旦实现,时间也就停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后发生的事就无关重要了。他像期待幸福或者解脱那样期待着那一天。他拨停了钟,以免老是去看,但每晚听到黑暗中传来的午夜钟声时,他撕掉一张日历,心想:又少了一天。
最初,他想建立一种生活规律。他喝马黛茶,抽自己卷的烟,阅读浏览一定页数的书,当克莱门蒂娜给他端饭来时试图同她聊天,晚上熄灯之前复诵和润色某一篇演说。克莱门蒂娜上了年纪,同她攀谈不很容易,因为她的回忆停留在乡间和乡间的日常生活。
他有一个棋盘,自己胡下,从没有下完一盘。棋子缺一个车,他就用一颗子弹或者铜板代替。
为了打发时间,阿雷东多每天早晨用抹布和扫帚打扫房间,消灭蜘蛛。混血女人不喜欢看他干这种低三下四的琐事,这是她分内的活,再说阿雷东多也干不好。
他很想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但已经养成了天亮就起身的习惯,改不过来了。
他十分想念朋友们,由于他以前落落寡合,朋友们却不记挂他,不免使他伤心。一天下午,有个朋友来找他,没进门厅就给回绝了。混血女人不认识那人;阿雷东多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以前他很喜欢读报,现在当天的大小事情一概不知,使他难受。他不是善于沉思冥想的人。
白天黑夜对他说来没有差别,星期天却不好打发。
7月中旬,他发现把时间划分成小块是个错误,不管怎么样,时间不分昼夜,总在流逝。于是他海阔天空,任凭自己的想像驰骋,他想如今在流血的乌拉圭广袤的上地,他放过风筝的圣伊雷内沟堑纵横的田野,一头现在多半已死掉的两色矮马,赶牲口的人驱赶牲口时升腾的尘土,每个月从弗赖本托斯运来杂货的疲惫不堪的驿车,三十三人登陆的阿格拉西亚达海滩,他想起飞瀑,山林,河流,想起他曾爬到灯塔所在的山顶,认为普拉塔河两岸再没有更美的风景了。有一次,他从海滩的小山翻越到后山,在那儿躺着睡熟了。
海风每晚带来凉爽,催人入睡。他从不失眠。
他全心全意地爱他的女朋友,但告诫自己说男子汉不该想女人,尤其是没有女人的时候。乡村生活使他养成洁身自好的习惯。至于另一件事……他尽量少想他憎恨的那个人。屋顶平台上的雨声陪伴着他。
对于被囚禁的人或者盲人来说,时间仿佛是缓坡上徐徐流去的河水。阿雷东多不止一次地达到那种没有时间概念的境界。第一个院落有一个水池,池底有个蛤蟆;他从未想到与永恒相连的蛤螟的时间正是他寻觅的东西。
那日子临近时,烦躁的心情又一次冒头。一晚,他实在无法忍受,便上街走走。他觉得一切都变了样,比以前大。他拐过街角,看到灯光,走进那家杂货铺。既然进去了,便要了一杯白酒。有几个士兵胳臂肘支在木柜台上在聊天。其中一个说:
“你们都知道散布打仗消息是明令禁止的。昨天下午,我们遇到一件事,你们听了肯定会笑。我和几个伙伴走过《正义报》馆门口。我们在外面听到违反命令的声音。我们当即闯进去。编辑部办公室一片漆黑,我们朝说话的人开了一阵枪。他不再做声时,我们想把他拖出来示众,可是发现讲话的是一架叫做留声机的玩意儿。”
大家哈哈笑了。
阿雷东多在旁听着。那个士兵对他说:
“你觉得好笑吗,伙计?”
阿雷东多仍旧不做声。士兵把脸凑上来说:
“你马上喊胡安·伊迪亚尔特·博尔达①,国家总统万岁!”
①伊迪亚尔特·博尔达(1844—1897),乌拉圭1894年总统,1897年遭暗杀。
阿雷东多没有违抗。在嘲笑声中,他出了门。到街上时,他还听到侮辱的话。
“那个胆小鬼不敢发火,一点不傻。”
他表现得像是胆小鬼,但知道自己不是。他慢慢走回家。
8月25日,阿韦利诺·阿雷东多睡醒来时已过九点。他首先想到克拉拉,过后才想到那个日子。他舒了一口气说:等待的任务已经结束。这一天终于到了。他不慌不忙刮了脸,镜子里的模样还是原来的他。他挑了一条红颜色的领带,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很晚才吃饭。天空灰暗,像是要下雨;他一直想像应该是晴朗天气。他永远离开那间潮湿的屋子时有一丝悲哀。他在门廊里碰到那个混血女人,把身边剩下的几个比索全给了她。五金店招牌上的彩色菱形图案使他想起有两个多月没有注意到了。他朝萨兰迪街走去。那天是假日,行人很少。
他到马特里兹广场时三点的钟声还未敲响。感恩礼拜已经结束;一群绅士、军人和高级神职人员从教堂的台阶上缓缓下来,乍一看,那些礼帽(有的还拿在手里)、制服、金银丝绣、武器和法袍造成人数众多的幻觉;事实上一共不到三十。阿雷东多没有胆怯,却有一种尊敬的感觉。他打听哪一位是总统。回答说:
“就是那个戴法冠、握法杖的大主教身边的一位。”
他拔出手枪,扣下扳机。
伊迪亚尔特·博尔达朝前踉跄几步,俯面倒在地下,清晰地说:我完啦。
阿雷东多向当局自首。后来他声明:
“我是红党,我自豪地宣布自己身份。我杀了总统,因为他出卖并且玷污了我们的党。我同朋友和情人都断绝了往来,以免牵连他们;我不看报纸,以免人说我受谁唆使。这件正义之举由我一人承当。你们审判我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尽管还要复杂一些;在我想像中是这样发生的。
………………………………………………
沙之书
……你的沙制的绳索……
乔治·赫伯特①
①赫伯特(1593—1633),英国玄学派诗人,牧师。著有诗集《寺庙》和散文集《寺庙的牧师》,均系宗教作品。“沙制的绳索”是指靠不住的东西。
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不假。
我单身住在贝尔格拉诺街一幢房子的四楼。几个月前的一天傍晚,我听到门上有剥啄声。我开了门,进来的是个陌生人。他身材很高,面目模糊不清。也许是我近视,看得不清楚。他的外表整洁,但透出一股寒酸。
他一身灰色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灰色的小箱子。乍一见面,我就觉得他是外国人。开头我认为他上了年纪;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只是他那斯堪的那维亚人似的稀疏的、几乎泛白的金黄色头发给了我错误的印象。我们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从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奥尔卡达①群岛人。
①奥尔卡达,苏格兰北面的群岛,其中最大的是梅因兰岛,首府为柯克沃尔。
我请他坐下。那人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他散发着悲哀的气息,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卖《圣经》,”他对我说。
我不无卖弄地回说:
“这间屋子里有好几部英文的《圣经》①,包括最早的约翰·威克利夫②版。我还有西普里亚诺·德瓦莱拉的西班牙文版,路德的德文版,从文学角度来说,是最差的,还有武尔加塔的拉丁文版。你瞧,我这里不缺《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