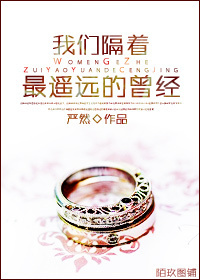那里并不遥远-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的腹痛已经有好几天了,每次月经来的时候,总是伴着几天的痛疼。以前在队里,每月的这段期间,她总要歇上几天,可来到这建桥工地,情况就不一样了。
由于建桥的工期定得短,便显得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对劳力的控制与安排就严格起来了。来工地的人分成三个班,每班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然后休息十二小时,一天四个班次轮流不停。大队还做出规定,来工地的人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一律不许请假,更不许无故旷工;确实生病需经赤脚医生证明。
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兰可真感到有点苦不堪言了。要说这也算是病,那哪个女人没有那么几天?而且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几天过后就自然而然的好了。如果把这当病看,工地上这么多的女人,岂不是天天有人请病假?
如果这不算病,可落在石兰的身上,却是那么的痛苦不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痛起来连腰都伸不直,不是病又是什么呢?
然而,在革命的热情与严格的纪律下,女人的这这种似病非病的状况及必要的保护被完全忽视了——报上的那些“铁姑娘们”们,哪个曾因此而提出休息?你没见她们月月出满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没撂下?而且,这事又是张扬不得的,说出去面子往哪搁?所以,石兰也就唯有暗自忍耐,只望着时间快点过去,让痛苦与时间一起消失。
石兰终于拿起饭盆,强迫自已无论如何要吃点,然而,那阵痛牵扯着她的神经,使她感到那面条有如草梗,难以下咽。她勉强吃了一点,又把饭盆放下了。
“怎么不吃了?”石红看着石兰的脸色,有点担心地问。
“吃不下。”石兰有气无力地说。
石红心里完全明白石兰此时的状况,然而,作为姐姐的她,却是一点帮助妹妹解除痛苦的办法也没有。看着妹妹那受的样子,她不由心里也感到不是滋味,便悄悄地问:“是不是又痛了?”
“嗯。”石兰用手按住小腹,腰也稍稍地弯了下去。
“要不……跟金发说一下,今天就别出工了。”石红说着站了起来。
“啊……不……别去。”石兰拉住石红说。
“你……”石红疑惑地看着石兰。
“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了。”石兰直起身子说。
石红看得出,石兰是硬撑着说这话的,她还是有点不放心,仍盯着石兰:“真的不要紧?”
石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再次弯下身子,一句话也不说了。
出工的时间到了,石兰挑起畚箕,随着大家慢慢地来到了工地。
江面上,已经筑起了两个巨大的四方形围堰,靠近两岸的地方,也各筑起道两头与岸相连的长长的围堰。经过人们十多天日夜不停地挖掘,各个围堰里的沙石被挑到围堰外边,形成四个巨大的深坑。再过几天,就要在这些坑里砌桥墩了。
石兰顺着围堰的斜坡下到坑底。坑底的水有一尺来深,尽管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把水抽出,可水不断地渗进来,永远也抽不完。而且坑挖得越深,水就渗得越快,有时抽水机需停上一会儿,水很快涨了上来,挖掘工作只好暂停。
坑里的水非常的冷,走进水里,不由使人产生一种把烧红的铁块放入水中淬火的感觉,身上的毛孔顿时紧缩起来。石兰走到坑的中间停下来,卸下畚箕,一旁的吴莲英便用锄头把沙石扒进畚箕里。待两头畚箕都装满了,石兰便挑起担子,又顺着斜坡走上围堰,把沙石倒向外面的江水中。
围堰里的沙石被不停地挖起挑走,时间也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石兰又一次的把沙石倒掉,然而,肩头的负担减轻了,小腹的痛疼却加剧了,并且饥饿也向她袭来。寒风吹在她那湿漉漉的双脚,使她感到从脚底到头发都是一片冰冷,而腹中的痛疼却使她感到火烧火燎,像是怀端一盆火。她感到有些坚持不下去了,她真想一步跨到床上,在被窝里卷缩成一团。
然而,她知道此刻离收工的时间还早了点,她起码还得再坚持一个小时。透过那些刺眼的电灯光,她看到四周空圹的山野还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山里的冬夜,显得是如此的漫长。
石兰在围堰上站了一会儿,然而她不敢站得太久,她怕被人认为是有意怠工或是什么的,她忍着痛疼又一步一步地走下斜坡。就在将要趟进水里的时候,一股莫名的恐惧突然袭来,似乎一脚下去,她的整个身子都要被吞没似的。她站在那里迟疑了一下,但不下去却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她终于迈了下去,来到吴莲英身边。
吴莲英回过头,见石兰的脸色显得特别苍白,便关切地问:“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没什么,就是肚子有点痛。”石兰的身子微微偻着,声音里有点颤抖。
吴莲英感到有点不对劲,刚才她就看见石兰在上坡时显得特别的吃力,她抓着石兰的手:“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厉害吗?要不要歇一下?”
石兰慢慢地抽回手,她的脸上显得既茫然又无奈:“不用了,再过一会就收工了。”
吴莲英见石兰不回去,只好又把沙石扒进畚箕,不过,她这一回扒得更少了,只有那么的半畚箕。扒好后,她还是不放心地问:“你行不行?不行最好还是先回去。”
石兰摇了摇头,一声不吭地挑起担子,又向坡上走去。阵痛突然又加剧,她的腰更弯了。她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上走。她突然感到心头一紧,头脑一阵晕眩,双脚一软,连人带担扑倒在斜坡上,“哗啦啦”地滚了下去。
“啊——”一直留意着石兰的吴莲英一声惊叫,扔下锄头,冲上前去,将石兰扶起,其它的人也急忙围拢过来,一惭忙乱。
石兰很快清醒过来,在石红与吴莲英的搀扶下,慢慢地向竹棚屋走去。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喇叭里传出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悠扬的歌声。窗外的风虽然小了点,可雨却大了起来。雨水从屋檐下一串串地落下,把地上的泥土冲成一个个小小的水坑。
天气真冷!白晓梅站起来,搓了一会手。透过蒙蒙的雨幕,可以看到工地上人们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冰冷的雨水中不停地忙碌着。虽然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但从那些显得迟缓的动作中,就能感受到他们此时的艰辛。
自从来到工地后,白晓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间广播室里度过的,她无须像其它人那样的在风雨中拼搏,她甚至还没有真正挑着担子到那坑里走一回。与他们相比,她可算得上养尊处优了。然而,这一段时间来,处在这个令人羡慕位置上的她,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的优越,甚至连刚来广播室时的那种意外重逢般的兴奋也渐渐的淡薄了。有时,她甚至想离开这屋子,到他们中间,在无尽的劳累中把一切烦恼都忘掉。
当然,她也觉得这种想法有点不切实际——安排你在这里,你就必须把这里的事做好,你没有理由离开这里的。可是,在这屋里,她分明又感到一种困扰,闪闪烁烁又隐隐约约,使她总想离开这里。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白晓梅听着这熟悉的歌声,脑海里顿时浮现出《白毛女》里面喜儿那欣喜的笑容。是呀,穷人的日子虽然苦,可也有那短暂的欢笑。她从红头绳想到白纱线,从白纱线想到白小松的衣服,天气这么冷,得赶快把他的衣服织好。她知道,这时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将持续一个多小时,只要这段时间里没人来打扰,她完全可以利用来织衣服。弟弟的衣服已经快织完了,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织好了晚上就能让他穿上。
白晓梅走到门前,将开着的门扇掩了一下,留下一道仅容一个人侧身而过的间隙。她不想被人知道自已在这里织衣服。尽管她已经在这里织了好多回了,可从来没有被人发觉过。她走到竹床前,从被子底下把快织好的衣服拿出来,然后坐在竹床,背微靠着棉被,一针一针地织起来。
隔着的谷席屏风挡住了外面的视线,白晓梅用不着担心别人会从窗口看到她在干什么,然而,她仍用耳朵注意着外面的动静,以防有谁突然走进来。她时刻做好准备,只要那半掩着的门发出声响,就迅速地把衣服塞到被子底下,再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来。
喇叭里传出来的乐曲,时尔悠扬委婉,如泣如诉;时尔低沉跳跃,如虎啸狼嗥;时尔高昂明快,则显得奔放豪迈。白晓梅随着乐曲的节奏,在心里默默地跟着唱,那从针头处挑起的一圈圈白色的纱线,像一串滚动着的音符,不断地融入那乐谱似的衣服中。她有点忘乎所以了,此时,除了那连绵起伏的旋律和手中不断滑过的纱线,她的心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了。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光芒万丈……”喇叭里响起嘹亮的合唱,同时伴着解说员用那激动人心的声音所插播的解说词:“太阳出来了,阳光照进了山洞,喜儿终于得到了新生……”舞剧已近尾声,白晓梅手中的衣服也快织成了,而她的心情也似乎随着剧情的发展而渐渐明朗了。她加快了速度,终于在音乐节目结束前织完了最后一针。她把织针抽出来,把衣服摊在竹床上,然后,张开手指量了一下。
衣服显得比较宽,也比较长,要是给小松穿,明摆着是大了些。可他还在长个子,而这衣服却是要穿好多年的,总要预先放大些。白晓梅看着衣服,心里感到了一种欣慰。她把衣服拿起来,低下头,用牙齿把线头咬断。
正当白晓梅为弟弟晚上能穿上衣服而感到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觉得眼前的光线暗了许多,抬起头一看,不由一愣,浑身上下在这一瞬间泥塑木雕般地僵住了。她看到,兰忠林正站在竹床与谷席屏风中间,胖胖的身子把这窄窄的过道堵个严严实实;背着光线,他脸上的表情神秘莫测。
尽管白晓梅利用转播节目的时间织衣服并没有妨碍她的工作,然而在这紧张繁忙的工地上,出工时间做自已的事情却是不允许的。她不由怨恨起自已,怎么只顾织衣服,却忘记了对外面的注意,连门被推开,兰忠林怎么进来的都不知道。她知道兰忠林发起火来是很暴烈的,来工地的这些日子,已经不止一次见到他对别人的训斥,那模样,实在有点吓人。对她来说,即使兰忠林不发火,但一顿批评显然是免不了的。她把衣服放在竹床上,默默地低下头。
兰忠林看出了白晓梅内心的惶恐。要是换个别人偷偷干私事,他完全可以就此对其大批小斥一阵。可是,眼前他所面对的是一张令他感到愉悦,惜都来不及的脸,那微垂的眼皮,那抿着的小嘴,看上去比平时更为动人。而且,他还发现,在这里不管做什么,外面的人是看不见的。他不由为这一发现而惊喜。此时,这近在咫尺的漂亮脸蛋,早已令他心旌摇荡,哪里还会拉下脸去批评她?
自从兰忠林把白晓梅安排在广播室,他就被她那迷人的脸给弄得神魂颠倒,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了。这可比不得家中的黄脸婆。尽管他的妻子当初也算得上大队里的一枝花,可生了孩子后,那腰身,那模样,完全变了,让他老是感到不能尽兴。虽然,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大队妇女主任那身段也不错,时不时与他一阵颠鸾倒凤,但毕竟是一介村姑,虽野趣十足,却是根本不能与眼前的这个美人坯相比拟,更无法满足那不断膨胀的欲望。他甚至把自已



![[综漫]两百万光年遥远之星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34/3456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