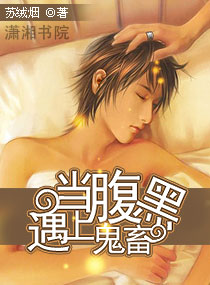当腹黑遇上鬼畜-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换在这儿,感谢上帝,能让五六好运到全身而退。
那个男人,真是一种恐怖的存在。
按理,我也该回家才对。可私心里,又觉得不甘心。自诩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台面上不是。可台下面,花非花三个字这些年里也算响当当。没有人见过我真正模样,也没有人能打探到我丝毫底细,就是凭着这些个保密到家的功底,才能在贼界里一帆风顺勇往直前。
可如今,对着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居然就能被他轻松识破了身份底细,除了怄气,更多的还是一种被盯上的感觉。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是?
所以,我决定,从这一刻开始,那个叫那时的男人,正式列入我的调查名单中。
保不准哪天小爷我不开心了连他家祖坟都给掏干净。
也是因着没走,才让我瞧见了更多不得了的东西。
在等待拍卖开始的时间里,除了喝酒,好像也没别的事可做。打探情报什么的,这会也完全没了兴趣。我的兴趣,早就被那个该死的男人给勾了去。中间也有些莺莺燕燕的凑过来,丰乳肥臀外加满身熏香,真是坏我喝酒的好兴致。
尤其是当我再一次被某个白痴女人装醉踩到脚后,我其实很想也装醉踩回去来着。该死的,我这张脸这身皮这把骨的就那么有吸引力?就算对我有性趣,上帝啊,你可不可以回去换张五六的脸五六的身子五六的体香后再回来?
淡定。
感谢上帝,在我灌掉大约两瓶酒的分量并且脚差点被踩烂并且身上无辜沾染了各种果汁饮料后,拍卖会总算开了场。开始摆出来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物件,大家伙也意思着举举手抬个价凑个份子交水酒钱。中间还摆上条长得跟尿布样的黄巾子,张口拍五万,我差点笑岔气。
真该让五六瞧瞧,约莫他那张面瘫脸上也能露出点滑稽笑来。
一个钟头后,压轴的锅终于上了台面。底价二十万,送拍者真是毫无悬疑地属那时那个家伙。本来就是他发起的慈善拍卖,又是自家摆出的东西,大伙也是给足了面子往上加价,一口老得快要掉渣的锅,短短几分钟就给抬到了九十万。
这会,我反倒安静下来。既然偷不得,干脆就光明正大的买回去得了,大不了今年换我被种进地里。也只是想,没等我抬手的,那时开了口。
他站在大庭广众之下,微笑着开口。
他说,各位,我出价一百二十万,拍下这口锅。
哈,天下奇闻。
自家的东西自愿贡献出来拍卖,然后花掉一百二十万再买回来,疯子吗?
其实,不光我这么想,在场的所有人都这么想。甚至还有人大着胆子开口问原因。
原因?
那个男人站在台上举杯,他冲我微笑。
他说,因为我心爱的人想要这口锅,所以,我需要拍下来送给他。
我听到的,是自己脑子里一根唤作危险的弦噼里啪啦碎成满地渣。
、章回 二十
那晚,我是带着满肚子酒精顶着一颗失魂样的脑袋挪回了家。虽然不意外五六早就回了家,也真没料到他会坐在玄关上等我。推开门的一刹那,我很确定自己从他脸上看到了某种类似茫然的表情。
下一刻,他回过神来又变成从前那个表情都懒得摆的五六。
其实,我有一肚子的疑问想要问的,结果在瞧见他不经意里摆出的不在意后,再多的疑问也胎死腹中。强打了精神俯身去抱他回房,甚至还能逼出几个冷笑话来,真是佩服死我自个儿的抗压能力。
自始至终,他也没提关于遇见那时的半个字。
回到床上时,像过去的几百个夜晚样,看着他的背影,自己臆想。不幸的是,这次我的臆想变成了恐怖片,来势汹汹的差点吓死自个儿。实在撑不住了,一把捞过他身子塞怀里,只恨不得干脆揉骨里。
我说,五六,你谁都不能爱。这辈子你是我的,就不准你跑。
五六没搭腔。
早就该习惯了他的沉默,连带着习惯他沉默后显而易见的不爱。这一晚,却莫名就怕了他的沉默。
到最后,他也没搭腔。
我装不下去了。一颗小心脏就跟被人狠狠攥了一把再额外搓两下样,疼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撑不住了。
松开他,自觉地滚到一边闭紧眼睛装睡,顺便压住娘们样澎湃的悲哀。
然后,他睡着了,我睁眼到了天亮。
隔日一早醒了,帮他做好早餐后就出了门。没地方去,干脆躲进了咖啡屋。说起来,当初偶然路过咖啡屋时,五六犯懒不走了,就拖着他进来休息顺便喝点东西。也是出乎意料的,他居然就喜欢上这家的咖啡跟装修来。难得见他主动表示喜欢一件东西,我一激动,隔天就把咖啡屋给买下来做了私人财产。也得亏那会的一时激动,才从此多了个能让我整理头绪又相对隐蔽的窝。
就在咖啡屋里,坐了大半日的光景后,脑子里开始有了清晰的纹路。
那时那时,一个能稳坐商会头把交椅并且稳稳扎根四九城的主,城府有多深,脚趾头都能猜得出。头天夜里敢当着众人面把一口锅说成定情信物样,还公然冲我挑衅样的笑,摆明在说,他的目标是五六。而五六这些年基本上变成一只堪比楷模的宅家米虫,交际圈什么的是一千零一夜,所以,他不可能背着我出门去结交一个里子面子都不是善茬的主。至于那种五六走路上恰巧被经过的那时瞅见然后一眼惊为天人从此深入调查研究之类的屁话,更是笑谈。
推翻种种不可能,剩下的,就是可能。
五六跟那时认识,并且能让那时这种人上了心,渊源该是长久地很。
但是,五六来到我身边时不过四五岁的光景,牙都没长齐,哪里来的外交?
第一个Bug,就此出现。
当年那场病,抹掉了我五岁前的所有记忆。醒来后孤单地过了一年,那期间,大抵因为脑子被格盘,之后的记忆就开始变得异常清晰起来。整整一年,花娘总会无端地怔神,偶尔瞧着我时眼里还有说不出的情绪。小时候猜不透,现在想想,总觉那些个情绪里有愧疚有哀伤甚至还有隐约的怨恨。
花娘,为什么要恨我?
第二个Bug,来了。
没过多久,花娘突然消失了几日,再回来时,身边就多了个孤儿院领养的五六。嘴上说着是为怕我孤单,可她眼里的晶亮是要溢出来的。几日后,她再度回了孤儿院,却是偷了五六的领养记录回来一把火烧个干净。
为什么?
所有的事情凑到一起,像是一道是非题。假设不可能的情况,推断出可能的结果,答案是错的。可如果假设不可能的情况推断出不可能的结果,双重否定后,答案?
当年送五六去孤儿院的人,是那时。
而花娘,就算与那时没有多少交集,但至少,他们之间,打过交道。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寒意生了满背。秘密,很多的秘密,或许,还有阴谋在中间。冥冥中,好像有一张巨大的网开始兜头扑来,生死难测。
惊悚之余,心头压不住的是更大的疑惑,五六,到底是谁?
我又是谁?
可惜,没等我消了震惊的,就瞅见五六跟这世上我最不愿见到的人一前一后进了咖啡屋。我躲在暗处,看他们两个相谈甚欢,牙根都差点咬碎。虽然一直在告诫自己,要淡定淡定,只是聊天,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结果,理智还是被烧得一干二净。
像个妒夫样冲出去,理所当然地被五六呵斥着滚蛋。继续带着一肚子的火气回到家,最终衍生了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争吵。
说来可笑,明明是真正动了怒来争吵的,到最后也不过变成我自演自唱的滑稽戏。从头到尾,五六都是用一种冷静到残酷的态度面对我的怒火三丈,甚至在他看着我时眼里投射出的居然是悲悯?
哈,从头到脚,都是我一个人在垂死挣扎而已。
不算争吵的争吵过后,开始了无意义地冷战。明知道以他的性格是不会主动来认错服软的,却也在真正被漠视后又一次凉了心。
到头来,我也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也好。伤得狠了,就能硬下心来不把满腔子心思都放在他身上。冷战的几日里,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与手段去搜集关于那个男人的一切信息,得来的也不过是能摆在台面上的大众谈资。
身家干净,手段超群,底下人也忠于职守,面上是经商,根系强壮却也能真正做到不沾污秽。如果这个世上还存在神祗,那个男人恐怕当之无愧。
可越是无懈可击的表象,内里肯定会有更加无法告人的秘密。我偏不信了,那个男人,能做到天衣无缝?
这么想着,再去搜集情报后我就换了条路。查他查不出门路,那就从他祖上查。查来查去的,倒真让我摸出点东西来。
百年前一支荣耀长存的家族,繁衍至今成了三支。近二十年前的一场惨剧,让三支变成两支,现在,两支也在向一支靠拢。我不经商,可商场上那家与赫家的明争暗斗还是多少耳闻了些。至于早已销声匿迹的叶家,所有的秘密早以随着二十年前的一场火深埋地下。
但,至少,让我查到一点,当年叶家,曾经有两个少爷。
秘密,很多的秘密。
冷战,持续地冷战。
我唯一能感觉到的,是风雨欲来时的平静。
然后,周游世界的花娘突然回来了。
、章回 二十一
花娘来了,不光来,还带来了一身的麻烦。
一场莫名其妙的暗杀,我奇怪的是自己居然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花娘讲事情的前因后果。她的理由很充分,也够完美,让我的心能轻松接受了她的道歉。
可是理智在说,同样完美到无懈可击的理由,往往都藏着猫腻。
事实证明,我没猜错。
借着外出买菜的机会跑到了后山的暗杀现场,找到遗落的弹壳的同时也一并把狙击手藏身的地方摸了个透彻。从那个位置看回去,只能瞧见家中的摆设跟偌大的沙发,独独不会瞧见当时我们三人的落座情况。
就像我说的,莫名其妙的暗杀,算计味道明显强过花娘所谓的警告性。
所以,当花娘提出要我独身南下帮她善后时,我毫不犹豫地点头应下来。就算感觉在隐约提醒着那会是一场阴谋的开端,我还是会去。
只要任何有可能威胁到五六安危的事存在,花非花会第一时间解决掉,在所不辞。
临走前,五六总算跟我冰释前嫌并且在床上滚了整夜。当他因着体力不支而沉沉睡去时,我能做的,只有贪婪地看着他的睡颜一直到出发的前一刻。
日后会生什么变故,我猜不到,但至少,眼下仅存的一点温存时光,我还能厚着脸皮收纳。
后来,我上路了。
感觉没有错。自踏上南下路的那一刻起,被监视着的感觉就开始如影随形。那双藏在暗处的眼,似是吐着信子在伺机而动。待到一路畅通地过了国境线潜入那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庙宇中顺出花娘口中珍贵无比的佛像时,我想笑,到底没笑出来。
一尊铜铸的佛像,面子上连点装饰的心都懒得动,一点金漆还喷得不匀乎,纯粹粗制滥造的流水品。那一刻,我忽然就纳闷起来,花娘费尽心机把我支到南疆到底是唱得哪出?
我甚至忽地就确定了,家里上演的那一出莫名的暗杀,很大可能是花娘在自编自演。
我们两个,到底是谁在发神经?
想明白了,就愈发地不明白了。晚上躺在脏兮兮的小旅店里,强迫着自个儿闭了眼假寐顺便等待暗中监视我多日的某些人出现,结果等来的却是当地警方。
那些个说着鸟语破门而入的人半夜里出现在我面前时,说不惊讶是假的。等到在众目睽睽下看他们从砸烂的佛像中掏出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