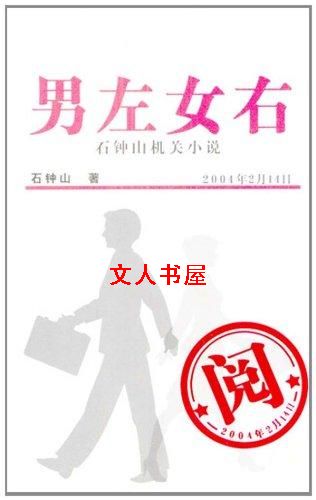男左女右-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就不再说什么了,想了想说:那就去公园。
这次她没再说什么,对马萍微妙的变化他并没有察觉。在睡觉之前,他就想,明天抽空给韦晓晴打个电话。
4
马萍一下子疏远了文君,这种疏远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究其原因,还是半年前她与常冶的相识。
马萍在文联机关门诊部当医生,文联嘛,大都是一些文人。在这之前,常冶的名字她是知道的,常冶是作家,写小说也写电视剧。常冶是这座城市的名人,和文学、艺术沾点亲带点故的人都知道常冶的名字。马萍因为在文联机关门诊部工作,常冶这名字听得自然比别人多了一些。
那一阵子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编剧就是常冶。门诊部里的医生护士一上班就议论那部电视剧和常冶。议论来议论去,常冶这个人在马萍的心里就亲切起来。因为她也很喜欢常冶写的那部电视剧,在这之前,她还读过不少常冶写的小说,在她的印象里,常冶是个很细心的人,描写的男女情感也是那么感人。
常冶不经常来机关上班,他是作家,工作就是在家里写作。常冶只是偶尔来机关开一次会,或者别的什么事才匆匆地来一趟,然后就走了。常冶似乎从来也没到门诊部来过,仿佛常冶从来不生病。
那一天,她听同事说常冶来了,就在二楼的会议室里开会,不少没见过常冶的人都去上楼看常冶,他们的门诊部在一楼。她没有去,不是不想见常冶,而是觉得那样看人家有些不好,扒着门缝看人家像什么话。其实她很想看常冶,她想象不出一个能把一部爱情故事写得让人肝肠寸断的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直到中午时分,会议结束了,常冶从楼上走下来,她隔着窗子在人们的指点下,认识了常冶。常冶四十多岁的样子,脸孔很白,不像一般文人似的都戴着眼镜。但在马萍的眼里常冶是最像作家的人了。如果,只是这么认识常冶也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有一天,常冶突然来到了门诊部,另外两位医生去领劳保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坐在桌后,他别无选择地来到了她的面前,不知为什么,她竟有几分紧张,睁着眼睛望着他。
他坐在那里,也很认真地望着她看了几眼,然后声音柔和地说:我叫常冶,就是文联的,我来开点药。
为了让她相信,还要去兜里掏工作证。这时她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作家。
常冶就笑了笑,笑得很腼腆。常冶就说了自己的病情,她又问了问有关情况,便给常冶开了几种药,常治拿完药,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常冶走后,她坐在那发了半天呆,她突然想起来,有一味药开错了,应该是另一味药才更适合常冶的病。如果换了别人,马萍不会担心也不会着急,反正不对症的药也吃不死人,不管用,下次再来开就是了。而对常冶她就担忧了起来。她认为常冶的工作很重要,病一时半会治不好,就会耽误他写作,在她的心里,写作是很重要,很神圣的事情。于是,她就急三火四地去了楼上的办公室,查找常冶家的电话号码,于是打通了电话,过了半天,常冶才接电话,她把情况在电话里说了,希望常冶能来一趟,她给换一味药。常冶就说:算了,又不是什么大病,不吃药过几天也许就会好了。
常冶越是这么说,她越是感到对不住常冶。她回到门诊部,就是忘不了这件事,心里七上八下地老是想着那味药。终于,她忍不住又上了一次楼,查到了常冶家的住址,不是文联宿舍,文联宿舍她熟悉。中午的时候,她带上那味药找到了常冶的家,常冶见到她很吃惊,她说明了来意,并把那味药拿出来时,常冶就更吃惊了。接下来就是万分的热情,拿出水果让她吃,她没有吃,只是打量了一下常冶的房间。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住人,一间是常冶的书房,书房的门开着,一台打开的电脑放在书桌上。她知道,常冶在工作,忙起身告辞了。
常冶一直把她送到楼下,并要开车把她送回机关,在马萍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没有送她。但他还是一再说:马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了。
他叫她马医生让她感到有些吃惊,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见过面,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姓名呢,一路上她都在琢磨这个问题,直到回到门诊部她才恍然明白,原来在常冶开药的处方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看来他真是个有心人,为了他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她竟感动了好几天。
不久后的一个中午,常冶突然给她打来一个电话,说是为了上次的事情,中午要请她吃饭。还没等她推辞,他就在电话里说:马医生,你别推辞了,二十分钟之后,我去接你,你在机关马路对面等我就行。
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马萍的脑子乱成了一团,她做梦也没想到常冶会请她吃饭,面对那么有名气的一个作家,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站在马路对面,还没有想清楚,常冶开着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她坐上车,一直到下车,走进一家饭店,脑子仍然很乱。
那顿饭,她吃了些什么,她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说了什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常冶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并不停地让她吃这尝那的。直到常冶开着车又把她送回到机关门口,她才清醒过来说:谢谢你请我。
常冶笑着说:是我谢你才是。
接下来,她就是兴奋。几天之后,她突发奇想,应该回请一次常冶,礼尚往来嘛,人家请你了,怎么着也得意思一下呀。这一想法一经产生,便不可遏止了。她偷偷跑出去,用公用电话给常冶打了个电话,有些语无伦次地把意思说了。
常冶就在电话里笑着说:你请我?这怎么行,要不你来我家,咱们一起做饭吧。
她说什么常冶就是不同意让她请客,没办法,她只好妥协了,去他家做饭。这是第二次走进他的家门,她赶到的时候,他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那顿饭,两人吃得都很愉快,常冶不住地夸她做菜的手艺,并说自己许久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菜了。直到这时,她才知道,常冶的夫人在国外已经学习工作几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的迹象。平时,常冶不是吃方便面,就是速冻饺子。她就从医生的角度说了许多营养的重要性,他表示赞同,但还是总结性地说:不是没时间,一个人懒得做。
她听到这,心里沉了一下,竟鬼使神差地说:要不,中午我来帮你做饭。
他听了她的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就表示了欢迎,还说了许多谢话。她说完这句话,自己都感到吃惊。平时,中午她不回家,一是家离机关较远,二是机关有食堂,每顿饭只要交一元钱,其余的机关给补贴。文君也在机关食堂吃。
第二天,她就如约前往了,从机关到常冶家不用换车,坐车四五站,十几分钟就到了,很方便。她来到时,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饭做得也愉快,吃得也愉快。吃完饭,两人就坐下来聊天,渐渐,她觉得常冶和平常人也没什么两样,说的都是普通人说的话。一下子,她觉得和常冶近了许多。她在他书柜里发现了许多常冶写的书,他看见她在书柜前留意,便打开书柜随便抽出了两本说:愿意看就送给你了。这是她第一次拥有了一个作家的两本书。以前在上大学时,她也曾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大学的文学社参加了两年活动,也写了一些习作,可惜一篇也没有发表。那时,她喜欢读小说,把自己的青春幻想移情到小说中。毕业不久,先是恋爱、结婚,渐渐就没时间读小说了,是常治又一次焕发了她读书的热情。那一阵子,她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常冶小说上。文君就奇怪地问她:这是谁写的书,让你这么上心。
她就说这是她们文联的一个作家写的,还介绍了常冶的一些情况。文君没往心里去,随便翻了翻就放下了。
从那以后,每天中午她都准时地出现在常冶家中,刚开始,常冶每次都把菜准备好。后来她为了让常冶安心创作,菜什么的她来时买好带上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渐渐就有了许多理解,这种理解再往前走一步,就产生了感情。马萍在和常冶产生感情时,不是没想过后果,但她控制不住自己。她就像自由落体一样,向常冶那片大地跌落而去。后来她觉得这种感情不能自拔了,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作家常冶。如果说刚开始走近常冶时,是崇拜、好奇,但现在已经变成彻底的爱了。这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是一个已婚女人的婚外情,马萍和所有婚外情的女人一样,面对着痛苦的煎熬,在矛盾着,困惑着。
5
马萍和文君谈恋爱时感情也是很好的,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知道没有感情的婚姻是可怕的。现在马萍经历了两个男人的情感,她有了对比,情感在她心里便分出了优劣。
马萍和文君谈恋爱之前也曾和两个小伙子谈过恋爱,没有撞出什么火花,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分手了。直到马萍和文君相识,两人才碰撞出火花,最后走向了婚姻,于是他们又有了快满四岁的女儿。
遇到常冶,马萍觉得已经不是火花了,而变成熊熊大火了。这种高热度的大火,烧得她几乎窒息。这是马萍在文君身上所没有感受到的,刚开始她并没有完全地投入,和常冶这样不明不白的约会,她一想起文君和女儿,便有一种犯罪感。随着和常冶接触的加深,他们有了肉体关系之后,马萍那种犯罪感在心里渐渐淡去了。
每天中午之后,常冶开着车把马萍送到机关外马路旁,然后他就开着车走了。马萍一直望着常冶的车远去,才拖着疲倦、兴奋的身体向机关门诊部走去。此时,她浑身上下的每个细胞仍洋溢着快乐,这种快乐让她浑身通泰,从肉体到灵魂,她都感受到了变化。
她和文君热恋的时候,似乎也有这么一点点感觉,但随着进入婚姻,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她以为,所有男女都是这样,结婚,生儿育女,忙忙碌碌地过日子,所谓的爱情就是过日子,两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现在她遇到了常冶,这种想法才得以改变。
常冶不仅唤醒了她沉睡的肉体,而且唤醒了她的灵魂。在床上,常冶的温柔,以及疾风暴雨,她都喜欢,肉体上的快乐,让她对常冶流连忘返。她喊叫,挣扎,最后又像退潮的海水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又一次潮涌的来临,波峰、浪谷,让她体会到了晕眩、颤栗。这是她以前从没有体验过的。
因为常冶给她带来了全身心的变化,她不可能不透彻地感受着常冶,每一寸肌肤,甚至常冶掉在她身上的一根发丝都让她感到心旌神摇。她想,这大约就是爱情。
她尝到了失落和渴望。当常冶把她送到机关门口,又消失之后,她一下子觉得心里空空落落的,一下午的时间,她坐在门诊部里,经常发呆,想象着和常冶短短的两个小时幽会中,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一切都让她怀念,神往,接下来就是渴望了。仿佛他们已分别了许久。
于是,马萍的日子里多了期盼,先盼晚上,然后盼天亮,又盼中午,一到中午,有时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她便早早地走了出来,有几次她等公共汽车,等得她不能忍受,而干脆打出租车,急三火四地奔向常冶居住的楼门。门刚一打开,常冶似乎也等她许久了,一见面两人就抱在一起。以前,两人
![[火影]男左女右by飞樱雪鸢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