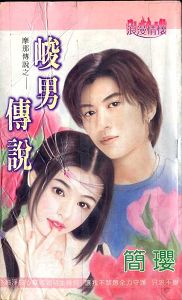蓝衫传说-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商议之下,便欲给他换个所在看押。哪知肖遥却是赖在那里,就是不肯挪窝,直言当日来时,便是为了配合办案而已,这住处就当让自己满意才是。今日既是已然安排进了大牢,虽是条件不太好,但这许多时日,倒也是生出了感情,不愿离开了。
杜公与暗暗咬牙,何曾听过在大牢里住出感情来的。这厮此刻放赖不走,软骨散又未见效,他一身本事,何人敢强逼于他。便是碍着种家的势力,也不能没定其罪前,将他如何了。无奈下,只得好言相劝,只说为了照顾经略相公颜面,当给他安排个更好的处所才是。
肖遥每日里与众牢犯狱卒相处的融洽,早听闻杜琼那个别院雅致,当下便言,若要换地,只要那个别院,其他地方一概不去。
杜公与听的暗怒,却是没法发作,只得跟杜琼讲了,让他先将别院让出,总叫这厮安静下来,等到再过几日,他们寻不到证据,便以指使他人投毒处置。届时,便是种师道也说不说什么了。到那时,一刀下去,便甚么恨也解了。
杜琼无奈只得应了。只是怎么也想不到,这厮在自己别院内,竟是如此折腾。将一个好好的优雅之处,糟践的面目全非。
眼见肖遥自在水中仍自游着,毫不理会。只得先压住怒火,往小亭中来坐,只是走不几步,忽的立住,看着左边一丛丛的物事发呆。
那里原本是种植的几棵冬青,秋冬常绿。杜琼爱其不似松柏类那般高大,又易栽植,用作点缀庭院,甚有画龙点睛之妙。故而嘱咐下人收拾之时,极尽呵护。只是此时,那些冬青已是不复原先郁郁葱葱之像,而是被人削枝去叶,修剪的奇形怪状。打眼看去,似是猫,又似是狗,凌乱之间,似是而非。
杜琼怒不可遏,面色铁青。也不再进,回头传喝下人来问。不一会儿,下人跑进来见礼,偷眼看看杜琼盯着的那些冬青,心中忐忑,不敢多言。
杜琼怒道“我叫你仔细照看,如何竟变成这般模样!”下人身子一哆嗦,方才无奈的道“回禀少爷,这不是小人做的,乃是那个肖二郎所为。”
杜琼大怒,骂道“你个狗才!他要做你便让他做?他若让你去死,你倒是死不死!”下人大恐,跪倒哆嗦着不敢多言。
杜琼欲要再骂,却忽听的一个懒散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杜衙内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须知气大伤身,还应常加制怒才是。”
杜琼大怒,回转身来,却见那池中的肖二爷,不知什么时候已是上来。此时裹着一件袍子,正自抱臂站在身后,满面笑容的看着自己。
杜琼暗暗咬牙,挥退下人,指着那一片冬青怒道“肖二郎,你如何作践我那常青树?它们又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肖遥转头看了一眼,诧异的道“怎么,杜衙内难道看不出来吗?想以杜衙内学富五车,风流儒雅之士,又怎会看不懂其中奥妙,定是欺我来着。”
杜琼怒极,指着肖遥咬牙道“好好,你说!你说!这究竟是做什么?”肖遥点点头,围着那从冬青转了转,才道“我见衙内这小院甚是雅致,只是太过死板。花草虽是茂盛,但却无形。正好我对园艺略有心得,念着府尊大人厚待,便动手给衙内将这些花草修剪了一番,衙内却也不需谢我的。”
说着,也不理杜琼欲要杀死人的目光,指着其中一丛如同狗啃过的冬青道“喏,你看,这便是猛虎下山之型。”又指着另一丛道“这个便是金鸡独立,那边那个便是灵猫戏鼠了。”
眼见杜琼双目喷火的望着那所谓的灵猫戏鼠,干笑了两声,又加了一句道“呃,衙内应当知道,那个老鼠实在是太小,这灵猫对面这丛冬青又偏生太大。没办法,小弟又没有刀剪之类的,只能徒手而做,费了好些功夫,尽去其枝叶,才得这般境界的。”
杜琼浑身抖着,指着那个只剩下一个树根的所在,颤声道“那便是你说的鼠了?”肖遥正色道“然也!不过衙内当以抽象的眼光去看,只要你心中念着那是鼠,它自然便是鼠了。”
天啊!打雷吧!打雷劈死他吧!杜琼望着满地的惨像,心中疼的直抽。望着肖遥那满面的笑容,直恨不得上去狠狠的踩上两脚。只是知晓他身手了得,也只能是心里意淫一下罢了。
他立在当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然转身走进亭中,自己坐下努力的平复心中怒火,一遍一遍的告诫自己,自己来是来打击这厮的,决不能让他倒把自己打击了。只要将这厮治了罪,自己再重修便是。
张洞王禹二人早看的傻眼,相对望了望,俱是为杜琼可怜。见杜琼进了亭子,也跟了进去坐定。肖遥嘴角噙笑,自顾施施然的汲拉着一双步履,随之而入。找了根柱子一倚,双眼微眯,自顾自在。
杜琼心中好容易稍稍平复,抬头欲要将郭盛被拿住的消息说出,打击打击肖遥。只是抬目所触,登时浑身俱颤,霍然立身,指着肖遥,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张洞王禹见他如此,不由一惊,眼见他双目死死盯住一处,便移目看去,一看之下,登时啼笑皆非,相对摇头。
原来那玉石雕彻的亭柱上,此时竟是一片斑斑驳驳,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自上而下写着:元符三年,嘉陵肖二到此一游!
二人转目四望,却见四根柱子上,无一不是如此,心中不由一声哀叫。这个肖遥简直就是个极品混账!所过之处,无一不是一片狼藉。杜衙内这小院落入他手,要想恢复旧观,怕是要比重建都费工夫的。
肖遥睁目看见杜琼模样,转头看看柱子上那一行行大字,笑道“杜衙内乃是方家,看小弟这刀石之术,可还入眼?只是此地又无刻刀,也只能用石块一点一点的敲了,其中定是有些拙漏之处,杜衙内不妨明言指点便是。”
杜琼满面怨毒,死死瞪着肖遥,良久突然仰天大笑,哈哈道“肖二郎,你如此作践于我,也不过是想激怒我,打击我。我却偏偏不让你如愿。你尽管折腾便是,看看某可能被你击倒。”话虽如此说,那笑声中却满是愤懑之气。
肖遥眼珠一转,微笑道“杜衙内何出此言?小弟可是真心求教的。既是这里的字迹入不得衙内之眼,想必衙内屋中收藏的字画上,小弟的题跋当能使衙内满意。不若前去一观如何?”
杜琼笑声戛然而止,双目瞬间瞪大,面上肌肉抽动,声音却是平静的道“你给我屋中藏品都做了题跋?”
肖遥笑容可掬,连连点头道“正是正是。原来衙内果然是对字画较为感兴趣的,吾道不孤,吾道不孤啊。小弟不但做了题跋,对于其中一些字画,还做了些修改。想来定会使衙内欢喜赞叹的。”
杜琼直直的瞪着他,半响,突地怪叫一声,已是拔腿便往屋中跑去。张洞王禹面面相觑,眼见杜琼奔跑的身子都有些哆嗦,怕他有什么闪失,看了肖遥一眼,急忙跟上。
肖遥自顾含着微笑,倚柱而立。不多时,便听的屋内一声大叫,随即噗通、哗啦之声连续响起。肖遥低低笑道“此番气不死你,也要让你大伤元气!也报一报下毒害我之仇!”
原来那软骨散之毒虽是未能向往常那样发挥效用,但对肖遥还是造成了伤害,一身辛苦凝聚的内气,此时竟是空空如也。丹田内再无往日那般充实之感,便是原本那内丹之气,也是不见了踪影。
只是他内气虽然失去,但身体却陡然变得强悍无比。一举手一抬足间,莫不带着巨大的力道。身体骨骼内,总是热烘烘的有一种肿胀感。似是原先那内气,都一股脑的钻入了骨头缝里,让他时不时的有一种燥热感。
今日他又感到一些燥热,眼见那池水碧绿喜人,便忍不住跳进去洗洗。只是进去之后,被莲藕细茎牵绊,心下烦躁,这才尽数拔了,扔到岸上,却被杜琼刚好进来看到。
他倚着亭柱,自顾偷笑低语,却见房门蓦地向两边爆开,杜琼帽歪衫斜的跑了出来。手中拎着两副画轴,直直冲进亭来。此时的杜琼往日一副温文尔雅之态半丝也无,满面狰狞,青筋暴跳。两颊上闪着不正常的潮红,口中牙齿咬的咯吱吱作响。对着肖遥呼呼直喘,嗓中呼噜噜的怪声不断。浑身抖成一团,将两副画轴对着他直晃。
后面张洞王禹二人急急跑来,待要上去扶住,见他那副如颠如狂的模样,不由的愕然止步,不敢上前。
肖遥抬手将额前一缕黑发拨开,微微一笑道“杜衙内怎的如此激动?小弟涂鸦之作而已,当不得衙内如此敬拜。哦,还是平静些好,平静些好。”
杜琼如若未闻,双目通红,抖索着又低头去看手中画卷。这两幅画皆是唐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画圣吴道子所作。一副乃是天王送子图,一副却是一副仕女图。俱是刻画细微,极尽精妙之作。
只是此时,那图上人物个个被加上了无数零件,或是多了两撇八字胡,或是头上多出几个肉疙瘩。仕女图中的女子,原本飘拂的大袖下,却被画了几只脑袋低垂的鸡鸭,似是被那女子拎在手中。
于是乎,天王送子图原本的敬神尊仰之气,顿时便成了几个贩夫走卒在乡间闲步;那副仕女图原本是一个飘逸出尘的宫女,此刻,却已经如同从菜市场,刚刚买菜回来的大妈了。
杜琼刚刚进房之后,只见自己珍藏的字画,几有一半被肖遥尽情涂抹,画的面目全非。这些字画,他不知用了多少手段,花了多少银钱,才搞到手的。哪成想当日一时疏漏,忘了收走,竟被一朝毁之。
手足冰凉之际,转头间却猛然看到这两幅画。画圣吴道子的真迹,此时便是万金也难求。这两幅画,还是当日他暗暗施展诸般手段,害死一个外乡人后,方才辗转所得。向来视若拱璧,珍爱异常,平日便是旁人欲要一观都不可得。
初时他尚未看出,实是那胡子、肉瘤、鸡鸭画的太过传神所致。待到反应过来,登时胸间一股闷闷的感觉直涌而上,口中大叫一声,双眼翻白,已是昏倒过去。
等到张洞王禹二人手忙脚乱的将他唤醒,睁眼再看到那两幅画后,一股勃然怒火却是怎么也压不住了,整个人便如同疯了一般,霍的崩起,提着那两幅画,踹开房门,便要来找肖遥拼命。
只是他气的委实狠了,到了肖遥面前,胸中气血翻腾,却是一字也说不出来。耳中鸣声大响,头脑昏昏的。见肖遥满面含笑,嘴巴一张一合的,实是一句也没听见。心中痛惜之际,又来看那画卷。越看越气,越看越痛之下,只觉嗓子眼一甜,双眼一黑,“哇”的已是一口鲜血吐出,身子直直向后便倒。
旁边张洞王禹大惊失色,急忙抢步上前,将他扶起。只是这会儿,任凭二人如何喊叫,杜琼也是不醒。二人惶急之下,也顾不得再去管其他了,抬着杜琼急急向外奔去。不多时,外面便是一片大乱。
肖遥倚柱满面微笑,心下大爽。他本是爱画之人,如何肯做那焚琴煮鹤的勾当。他所涂抹的画卷,俱皆是赝品。就是那吴道子的两幅画,也不过仿真程度极高的而已。眼见杜琼收拾的甚是仔细,料他定是不知,便着意的描画了一番。那杜琼一看之下,果然受不住,竟是吐血而倒了。
肖遥侧耳听着外面的混乱渐渐息了,这才转身往房中走去。他在这一呆十余天,心中也是焦急,不知家中郭盛等人如何了。料得只要他们不参与进来,自己又身在此处,官府也定不敢轻易动他们。只要墨砚等寻得那赖七,一切自是迎刃而解。若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