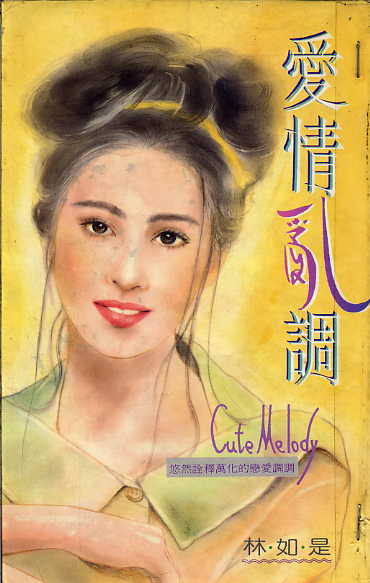˫����-��22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ޣ�����һ���Ӷ���Ҫ���һ���⸾��
ʷ����ĺ����д����ڸ���������λ֮�⣬����һ�����ص����ƣ��������⸾����
�⸾��Ҳ���������Ұ�����ǻʵ�����������Ů�ˣ���Ϊ����ԭ���Ҵ��ع��û����ʽ���֣�ֻ�ܳ�Ϊ���⸾����
���ľ�ǿ��������ش̼�������
���첽������ͻȻ�͵ؽ������뻳�����������������ƣ�����������ס�ͻ������Ͽ�������
�������Ļ������������ͷ��̧�ָ�����üĿ��ķ�˪��
����ǰ��������������·����������Ŀ������ϸ�ܵ���β�ƣ�������Ȼ�߰����ѩ��Ψ�и߶�ֱ�ı�������������ı�������Զ���ŵ����������������·����ԶӢͦ��ȥ����ͬ����һ����Ӣ������������㡣
����һ��Ӣ���ǣ���Ϊ֮��������ô�ࡣ
���ḧ�������������Ũü���ķ�������İ�����ϧ�ǵ������ģ��ǵü���Ҫ���ѡ�������һ�����������ؼ����ʹ����ҧ�´������������������ϣ���αػ������ۣ���
����Ҫ��һ�������ˣ��������е����ֺ����ˡ�
�������˵ı�֮һ���ǰ����ӣ���Ϊ�����ҰŮ��������
�������þ���һ������Ȼ������������
��������ׯ�͵¡�������������µ��ޣ�ȴ�����Ǹ����ĸ��š������ǽ�Ŀ��������������������һ���ա����������ǧ���ͺ�ȴ�����Ǹ�շת�������ˡ�����������Ů�ӡ�
Ȼ������ȴ��һ��������ʱ���������������Ů�ˡ�
�������ţ�����˭�����ˡ�
������������Ը����˭��
���ź�����һ���ʱ�䣬ȫ��������Ҳû����������һ���һ��ࡣ
���������е����ʱ�⣬��һֱ����������ߡ�
��һ�꣬�������ƴ��������Ż��˵�ʱ�䡣
���ڵ�����ð������Σ��Ϊ�����������á�
��ѩ���࣬�����滨�����������
���ǹ��ĵ���������������ܸ����˻�ѩ��������֦�����������Ө��������
���ʹ���Ӹ������ӵ��������������������ҵ���ʹ���ɵ���ʶ���ģģ�����е�������Ӱ��һֱ�������ߣ�һֱ�����������֣�һֱ�ͻ������Ͽ������������
����̫ҽ��ôȰ�����������뿪�粽��
����ʹ����ˣ������������Ҹ���Ц�⡣
����Ӯ���Ǹ�Ů��һ�Σ�
��֪�����Ǹ�Ů��Ϊ������ʱ���������Ͳ������ߡ�
��Ȼ�䣬��������ʹ���͵س����һ��˵���������ɡ�
һ���߿�����ޣ�����Խ��Խģ������ʶ����ʱ������
����ϲ���ϣ���һλ���ӣ���
���ڰ�����ʶ������˺�ѵ�ҹĻ��˲��ѩ����
�Ƕ��ӣ�
��ҲΪ����������˶��ӣ�
��������һ���Ŀ������غ�֮�����̶ȵز���������
ģ���������У������������ϻ�����չ��������Ц�ݣ�������ץס�����֣����������������������������㷢����ţ��ỽ�����Ͽ���лл�㡭���������ˡ�����
������Ϣ�������Ķ��ϣ���������Ϥ��������������ζ����������һ����Ҳ�ս�������Ĺ��ȥ��
�����ϣ��㰮�����𣿡�
�������ʳ������һ���Ӷ���֪����ȴ���������ʳ��ڵ����⡣
������˵�滰���˺�����
��������˵�ٻ�����ƭ����
��������ô˵���������Ķ�������Զ���ź���ʹ��ɣ�
ȴû�뵽�����������������������������գ��������������Ķ������������ϵ͵�˵�����Ͽ������кܶ��֡�����
����ش�����ȫ��һ�ɣ��·���һ˲�䣬�����������������ƽ�͡�
һ���ӵ�ִ����ʡ��Ͼ���������һ��������ɢ��
���⣬ѩͣ�ˡ������ij�ϼͶӳ�ڰ�ãã��ѩ�أ���Է��ǿ�ҵĹ�â�յ�һƬģ����Ψ�м����÷����ҫ�۵��⡣һ�شصĺ���֯�ţ���ת�ţ�Ʈ���ڷ��У����Űװ�������أ�������ʣ�����Ŀѣ���ԡ�
�����ϣ�������һ֦��÷����ô����
���õģ�����š���
�����������ÿ�������̤��ѩ�ء�
��������������ɫ������Ĵ�멣���ͣ��һ��÷��ǰ��ĬĬ����Ƭ�̣����������������˵�һ֦��֦ͷʢ����÷��ӳ�Ų�ѩ�����������Ѫ��
�˱ǵ�������������θ�������ζ������������������е���
����Ŀ��÷��������ĬĬ̾Ϣ�����ţ��Բ��𣬶��µڶ���ѩ�ˣ���δ���ˡ��Ͽ����ˣ������ڿ��������ˣ�ֻ�Dz�֪���ܷ�ԭ������һ�����ӡ�
һ��̾Ϣ�ţ���һ��ִ�ź�÷���ء�
����������һɲ�ǣ�÷֦��Ȼ�������е����أ�Ʈ��Ļ�����һ�������Ѫ��
���Ͽ�������������ϣ���Ŀ�����غ����ˡ�������Ṵ��һ˿�Ҹ�������Ц�ݣ������´���������ʢ����
�Աߵ�ҡ��������Ķ���������ޣ�Ȼ��������Ҳ�������ˡ�
����������˶�ʮ�����Ů�ˣ����������һ��ʱ�����Ů�ˣ�����������Ĵ�����ࡢ����������������Ů�ˣ����һ������������Ϊ���������Ρ�Ϊ����������Ů�ˡ�
��ȥ�ˡ�
���紵����������Ƭѩ��Ʈ����������ǰ��������
ʮ����û�е��������ᣬ�������۽�������������Ѷ��¡�
�����֮������
����������ɽ�ƣ���������潭ˮ��
�潭������ľ����˲��������ġ�
��һ�����գ��յ�����ʶ���ң�ج�����档
һ��������ĸ������ǰ�İ��ݣ�һ������������Թ���������綾�����ţ�һ�����������ױ���������Ŀ�⣬һ�����·��ֱ�������¥�����ӱ�����ʹһ����˺�����塣
������ĥ����������ȥ���������ء�
�Ժ���������������������ĸ�������о��𣿡�
������������������˵�������˽�����֪������
������Խ����������ĸ���м��ְ��գ���
���������Խ�����������㼱ʲô��ĸ��Ī�Dz�֪���Ǹ�Ů�˵���Ҫ����
�Ǹ��������������ٶ��ԡ�
ģģ�����У�����˯ȥ�ˡ�
������ʱ�����۶������ҡҷ���ɵ����ʹ�Ӱ��
��������У��������������峺���ĵĺ�ˮ��
��ô���ĺ��۾��������ǵ�һ�μ�����Ҳ�����һ�Ρ�
֮ǰ���������������۾��������ŵ���ɫ��ͫ�������������ԭ�ϼ���������ɫ���۾�������������ĺ���ɫ˫����
���ǣ����Ȳ�������������ʱ��������˫տ���ĺ��۾���
��Ũ��Ө����ī�����������ת��˵����������ػ���ĬĬ��ע�����������������۾�����ʱ��ϲ���������������ˣ���
������������������ʣ�������
���ɻ���Ĺˣ����������������������أ���
�����������ĵܵܣ�Ҳ������ľ˾ˣ��������˯�ھ˾�����ҿ������β������ⲡ�ᴫȾ��Ҫ�Ȳ����ˣ����ܼ��������һ����˵��һ������Ū�������㷢�����ھ˾�����Ҫ�������˾������к���ġ��óԵģ���Թ����������ͺõÿ죬�Ϳ������ռ����֪��ô����
����ߴ�ﹾ���˵�ţ�����ֱ��ͷת�㲻��״����
�˾ˣ�
���ʵ���Ӱ������������ؿ�������
���״�δ����˵������˾˰���
��ô�ÿ��ľ˾ˡ���
ʮһ���Ů���������Щ��ɬ����Ⱦ�һ������������ͷ�
��һ�����Ĺ��������죬�����Ȼ��һ����ôƯ����Ů������
����������˯�����Աߡ�
������ʮ���죬���������β�����Ϣ��ÿ������������ͬ齶��ߡ�
���������������������飬�������Ž������㣬��ϲ�������ڰ����һ�С�
��ʵ��Ҳ����ʶ�����������£������˽����ţ���֪���ࡣֻ�ðѽ����ķ����ٽ��������������ᣬһ�����������ؽ���
������ʱ����Ҳ���ƴ�ڻ����ʱ�����ڴ���Ц�ñ���һ�š��������������������������������
�˾˵���������һ���Ӳ������ǡ�
�����������ˣ�ÿ���ڴ����ᵽ�Լ����˵ĺ������Ծ˾˵Ļ����������һ���������飬ʹ�������δ������ԡ�
�������ȣ�����ʲô����
������������������֣��ٴ������������壬���ҵس��͡�
��ҧ�����أ�ǿ�������ͷ�ൽһ�ߣ���ͼ�㿪���˵ĺ�����
��������ʵ�ڶ㲻�������˶��ĵĴ�����ij������������������ϡ������ϣ����͵�������������Ť�����˹��ˣ�������ͦ�̵��β����������˳�ײ��
�����������ˣ���ˮ��̼���к���¡�
��������ˣ�Ҳ��Ϊ�˾˾ˡ�
��һ�꣬����ʮ���꼰���ա�
���Ű��պ��˼������ף����ְ�����һͷ�㷢�̳��٣����Ͼ��������������ǣ���������������������ʲô��Ը����Ҫ���װ����ɣ���
�����Ĵ�ͭ����ֱ�������ţ�������ʲô��Ը�����������Ҵ���𣿡�
����Ȼ��ֻҪ�������ܼ���˵�ɣ�����Ҫʲô�������ŵ�Ц��������ӳ��ͭ������Ѷ���֮�꣬����ͭ����������ഺ���ĵĻ��ݣ�˿��δ��ѷɫ��
�߾�����һ�Ծ�������ͭ�������Ӻ���Ů�����ֽ�Ȼ��ͬ������ӳ���Ե���ò������������Ȼ�����Შ��
�����Ŀ����߾�����˼��㱵�����ͭ������Ȼ����һ����Ը����⡣
��֪�����ŵ���ò�����ܼ�������������ʢ�������ĸߣ�����Ϊ��������ƿ����������������š�
��������������Ϊ���߾������ڿ�����
�����Ľ��ĵز������۷�ббƮ��߾�����������������۵�������������Ϊ���������ã��������������ܼ��ģ�ֻ�Dz�֪�����Ƿ�Ը�⣿��
����ش𣬴��������ź߾��������ϡ�
���Ż�û��Ӧ�������߾����ͻ�Ȼ��ɫ���Ŀŭ�ȣ����Һ������ǰ������ˣ�����ҹ�����������ң���
��������ס��ҧ���´���ί������ˮӿ������ɫ����������Ȼ��������������
�߾���������������Ȼŭ��������������㳶ס�������ӣ����������ϣ�������ҹ�������
��ʱ���Ź����ˣ���ס�߾����������ˣ����ˣ����������һʱ��Ϳ�������Ը����ºú÷�˼һ�¡������ȳ�ȥ����
�����Ű���Ȱ�����ϴ�ק֮�£��߾���������һͬ�߳��˸����ĵķ��䣬�����˷��š�
�����������������������ᡣ
ͭ���У����Ÿ������Ĵ����ķ��٣�������ţ��ĵ�������������������������ɫ���ӣ��Ե���������ѩ���������顣
����Ȼ��Щ�ûڣ�����Լ�һʱ��Ϳ��
���Ŷ�������������Ů��һ�㣬������������磬һ�㲻�漵�ʺͽ䱸��
���������ղ����������Ļ�֮���Dz���ɫ�����ű�Ȼ�������ˣ�Ȼ�������߾�����ŭ��Ҫ������������ȴ��ȥ��ŭ����������Ȱ�߾�����
˼�����ŵ��������������������˵��������ϧ��
�����İ����Ÿ����˾�һ���������������߾�����檣������Ź���һ������������������������Ů��Ҳ����ԭ����������ݣ����ľ����ط������š�
����������������黳��
ҹɫ���٣���������������ͭ�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