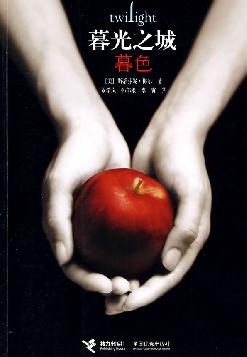无水之城-第7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水平高低看年薪
见人们拍手叫好,邸玉兰又扭着身子唱道:一代工人王进喜不怕苦来不怕死
二代工人忙革命
不搞生产搞运动
三代工人忙建设
工资福利都姓铁
四代工人忙改革
砸铁换泥饭碗破
五代工人忙竞争
论了年龄论文凭
六代工人忙下岗
饿着肚子乱上访
七代工人谁来干
再小也要当老板
……
62
此后一连几天,李木楠突然没了消息。沈佳到处寻找,家里没人,手机关机。沈佳急坏了,生怕他一时想不通,会出什么事。
人真是奇怪,自己不是恨他吗,怎么突然又多情起来?沈佳说不清,也不想说清。这个世界,有什么能说得清呢?自己不也恨陈珮玲吗,还不照样给她当了副总经理。
也许这就是生活,爱和恨交织在一起,又怎么能断然分得开呢?
哦,木楠,你在哪儿?≮我们备用网址:。。≯
夜,漆黑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西北风凄厉地叫,那声音好恐怖,好狰狞。沈佳睡不着觉,索性披衣来到窗前。城市的灯光星星点点,仿佛夜的眼睛,望着这伤心的城市,她突然生出想大哭一场的欲望。
这时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叫昌灵山的尼姑庵里,一位尼姑正盘腿而坐,默默诵经。
她看上去很平静,尘世里发生的那一切,早已烟消云散,随风而逝。她活在佛的慈光里,宁静,安详,美丽动人。
她法号惠云。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她过去叫什么,仿佛一朵无名的山花,清香宜人,一尘不染。
常来看她的,是苏万财老婆姚桂英。寺里的人发现,每次姚桂英来,惠云都关在屋里不出来。
尽管姚桂英至今还没跟她说上一句话,但她坚信,惠云就是女儿苏小玉。
炸楼的日子终于到了。
这是一个跟平日根本没啥两样的日子,唯一的区别是前一天夜里三点多钟突然起了沙尘暴。风力不大,但沙尘密度很高。当时人们正在梦里,并没有对这场突然而至的沙尘暴做出什么反应。一大早起床后,才发现屋里屋外全是厚厚的沙尘。
河阳城一夜之间又变得土头土脸,好在人们已对沙尘暴早已见惯不惊。看看风止了,浑黄的天也在渐渐转晴,太阳像是患了肝炎一样乏乏地从东边尘雾中渗出来,人们的心情便又很自然地恢复到对炸楼的期待中去了。
一切都没有先兆。就连一向料事如神的河阳四大名人“神娃娃”,这一次竟也没能预知到什么。事后有人据此断定,“神娃娃”的气数已尽,再也不灵了。可“神娃娃”却恼羞成怒地骂道:“懂个地瓜,天机不可泄露。”这是人们多少年来从“神娃娃”嘴里听到的第一句脏话,这句脏话加上他恼羞成怒的神情一下子使他的形象一落千丈。
人们还是想不通,事情过去很久,人们还在窃窃私语,发生这么大的事咋就一点预兆也没呢?狗日的楼,真叫怪。
一场飞来的横祸给这个日子罩上神秘的颜色,使它成为河阳人心中永远的痛。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河阳人谈楼色变,谈陈天彪色变。仿佛陈天彪和他的河化大厦,是这块土地上无法破解的一个谜。
炸楼出事了!天大的事!
早晨,人们顶着沙尘而来。离炸楼还有两个小时,广场四周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两天前就布好的安全警戒线阻断了人们冲进广场的欲望,人们的目光越过警察,齐齐地聚在河化大厦上。
这一天的河化大厦看上去格外孤独,它像个傲慢而绝望的外星人。神秘,肃穆,隐隐约约还透着几分恐怖。但没有人理会这些,人们争相争论着大楼身上到底有多少个炮眼,炸药是不是从美国进口的?听说负责炸楼的工程师是个女的,而且也姓陈,会不会跟陈天彪是本家?争论声鸦叫一样噪成一片,空气里充满唾沫星的味道。
广场西头,一幢三层小楼的平台上,端坐着应邀前来观光的市上领导。车光辉听从专家的意见,将这个简易平台布置成主席台的样子。为示隆重,台上还临时铺了红色地毯。
市长夏鸿远端坐在主席台正中,他的心情激动极了。昨天夜里,从省城打来的一个电话让他兴奋得一夜没合眼,半夜里还跟陈珮玲通了一次话。当然他不可能把电话的内容告诉陈珮玲,他只是平静不住自己的激动,想把这喜悦的心情传播得远一些。
电话里说,他在河阳的工作已得到省里全面认可,只要新广场建起来,年底调整时就可……电话尽管只有短短几句话,很含蓄,很委婉,但他却分明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一种能让他马上飘起来的声音。
尽管一夜未眠,但他毫无倦意。一股被希望燃烧着的火苗从心里跳出来,盛开在他的目光里。他的脸已接近太阳的颜色,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包括副市长刘振先,也是那么激动。确切消息说,他很快将到临市任代市长。之前,他还在恨上面,为什么举报信寄出去没一点动静,难道夏鸿远真的扳不倒?昨天晚上,上面有人给他透信,有关人员已秘密进入河阳,一张网已经撒开,就等着大鱼自投罗网。包括林子强,包括陈珮玲,这次全进入了视野。河化收购可能要翻盘,所有黑幕将一一抖出来。他激动得一夜未眠。想想,这些工作多亏了陈珮玲那个助理沈佳,没她,他还拿不到那些机密资料呢。可沈佳为了什么,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好,不知道心才能静,才能咬着牙去做某些做不出的事。
一股风吹来,暖洋洋的。刘振先斜眼瞅瞅台上的夏鸿远,看他还那么张牙舞爪,还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心里的笑更猛了。
人们热烈地交谈着,急切地盼望着,仿佛每个人的前程都在大楼那面,只要轰一声,大楼坍塌了,似锦前程就会真实而亲切地展现在眼前。
刚刚提升为电视台台长的林山独辟蹊径,选择了一个极为刁钻的角度,带着他的两个得意弟子,站在人们不注意的一个楼顶上,扛着刚刚从日本进口的摄像机。他要摄录下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这可是河阳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呀。
包工头子车光辉也是一宿未眠。昨夜他陪专家组详细察看了大楼的每一个点,直到专家们确信准备工作万无一失才回到宾馆。说不清是兴奋还是疲惫,心里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响。睁开眼那声音不在了,一闭上眼那声音又响起来。怪怪的,从没听过这种声音。后来他披衣下床,给黄大丫拨了个电话,电话通着,却没人接听。一连拨了几遍,最后,手机竟关了。
车光辉的心也像是被人关上了。接下来他变得六神无主,不知道是该醒着还是该回到床上睡觉。隔窗一望,才发现天色昏暗一片,一场未经预报的沙尘暴铺天盖地袭来。坐在窗前,他从头到尾观看了沙尘暴袭击河阳的过程。
今天他完全可以陪坐在主席台上,炸楼的事全权由对方专家组指挥,他的任务只是照顾好首长。但他毫无陪坐的欲望。他觉得自个血管里钻进了蚂蚁,坐哪儿都不舒服。有一瞬,他忽然想离开现场,离得越远越好,到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地方,美美地泡个热水澡。他几乎都要付诸行动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位领导打来的,说他因事来晚了,找不到主席台。车光辉马上问明位置,赶去给领导引路。
爆炸声是正点响起的。十点十分,半秒都不差。
声音很小。一点也没人们预想的那么夸张。人们只觉脑子里“嗡”一声,就像一棵树倒地那么响,便看到一股浓尘哗一下舞起来,像一朵盛开的蘑菇,很壮观,很漂亮。当时所有人都双手捂着耳朵,害怕爆炸声震破耳膜。土尘一冒,人们心一下提紧,还想真正的爆炸在后头哩,便都齐齐等更大的声音响。
谁也没想到,灾难就在这一瞬间突然降临。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林山。他的摄像机正随伞状的土尘往下移,移着移着,他忽地发现了问题。因为那一声“嗡”响过后,他感觉整个大楼都在动,就像他小时烧山药垒的垒子,抽掉任何一块土疙瘩,垒子都会整体塌下来。可摄像机移到某个位置时,他忽然感觉那儿是静止的,怪怪的静止,顽固的静止。他多停了几秒钟,就发现整个大楼的秩序被这静止破坏了。他脑子里“轰”一声,扔了摄像机,冲手下人喊:“不好,逃命呀。”
几乎在林山喊出这声的同时,灾难从天而降。
大大小小的混凝土块以千钧之力从大楼上端某个部位飞出来。立时,天空就像有无数挺机枪狂扫,射出的不是子弹,而是比子弹厉害百倍、千倍的碎石,烂砖。它们尖啸着,狂舞着,砸向楼群,马路,车辆,人群……
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几秒啊!
人们完全被吓傻了,吓蒙了,吓呆了,吓木了!
据说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丁万寿。当时他正站在邸玉兰边上,他们的位置正好在主席台下方。邸玉兰站在自行车后座上,站得非常耀眼,像一朵灿然开放的喇叭花。乱石飞过来的一瞬,她展开双臂,做了个迎接的姿势。丁万寿双眼猛地一亮,他看见一块头大的石块斜刺里飞向邸玉兰,直直冲她脑门砸去。几乎在石块砸头的一瞬,他一个猛扑,撞翻自行车。邸玉兰妈呀一声尖叫,摔倒在丁万寿怀里。石块呼啸而过,重重地砸在后面一根电杆上。电杆立时断成两截。好险啊,如果不是丁万寿,邸玉兰的头这阵就没了。
邸玉兰的尖叫震醒了众人。立时,人们抱头鼠窜,乱作一团。呼啸声,尖叫声,凄嚎声响成一片,整个广场陷入了混乱……
乱石飞了只几秒钟,骚乱却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下午两点,奉命赶来清理现场的武警官兵开始往外抬血淋淋的尸体,大批受伤者被送往医院。
河阳城到处彻响哭嚎,凄绝震耳,裂人心肺。
天明时分停了的沙尘暴突然卷土重来,霎时,四野茫茫一片,凄风嚎叫,沙尘漫天,天地一片浑浊……
据事后公布的消息,这场巨大的灾难夺去河阳城十三条鲜活的生命,重伤二百余人,轻伤无数。毁坏楼房十余幢,车百余辆,直接经济损失五千余万元。
一个无比沉重的消息是,市长夏鸿远不幸遇难。噩耗传开,四野皆悲。
据主席台上的领导回忆,十点十分爆炸声响起时,夏市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大睁双眼,无比吃惊地盯住那楼,表情跟爆炸声响起前迥乎两样,眼里像是有两个巨大的问号。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或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才那样奇奇地盯住大楼。
还没等别的领导反应过来,天空中便哗啦啦飞来一串子石块。台上顿时乱作一团,人们纷纷往桌子底下、凳子底下钻,实在钻不进去,就把头抵在别人怀里。幸亏飞到主席台上的石头不多,就两块,一块砸在了桌子上,一块,不偏不倚就砸中了市长。
当时整个主席台上,唯有夏市长是站着的。他在正中间,两边被人挤得死死的,蹲都蹲不下,只好站着。
比之市长夏鸿远,包工头子车光辉死得更莫名其妙。
他在广场外围,人群外侧。按说石块不应该落这里,但他肩上分明有石块击中的痕迹。照伤痕推测,石块有拳头那么大,所以车光辉不应是石块砸死的,顶多击倒在地。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是被踩死的。他站的位置,正好是通往共和街的那条巷子。人们在混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