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风铃-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是父亲送你的。”白哉站在门口抱着双臂,说话的时候眼中掠过一丝黯淡,语气硬邦邦的。
我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颠颠地跑到窗台那去看这风铃,简单但是别致,而且蜡纸包里是风干的樱花瓣,因为很轻就一直随着风摆来摆去,还能飘出淡淡的香味。
“哦?那可要好好去道谢,这是苍纯先生系上去的么?是他做的?”今天才得知苍纯已经单身那么久了,我兴致勃勃地摸着风铃,内心擅自把它划为定情信物之类的,有点脑残地嘚瑟了。
“哼。”白哉转身出去了,我只看见他侧脸绷成很冷很硬的弧线。
管他的贵公子臭脾气,继续调戏我的风铃,啊~怎么看怎么喜欢,好像那光滑的玻璃罩子就是苍纯的皮肤一样。
然后迎面飞来的刀鞘把所有美好的气氛都破坏了,我护着风铃躲开,就看见白哉极臭的一张脸:“出来,今天还没有训练呢。”
训练?你不等我把海燕骗来么?——我难以置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结果只得到白哉不客气的白眼和杀气腾腾的千本樱,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身体某个重要部位突然疼起来。
海燕那里被刀尖顶着的画面就跳出来,我全身的汗毛都哆嗦了。
我正以龟速一步三回头地往院子里挪时,院外的小路上传来细微的争辩的声音,一男一女,男人声音低沉略有苍老,八成是朽木银铃,而那女声听起来却像夜一。
这女人来朽木家而没率先调戏白哉就足以说明有大事。
白哉显然也听见了,满是不耐烦的小脸循声转过去,眉心就狠狠皱了起来。
“哟!白哉小弟,市丸银!”夜一老远看见我们,踮着脚朝我们摆动手臂,不过总是大咧咧的脸上却有几分烦躁。
嗯?出了什么事能让天塌不惊的夜一露出这种表情?
我规矩地给她跟朽木银铃行礼打招呼,结果被夜一按着脑袋一顿乱揉,她笑道:“很乖嘛!我说市丸银,你可千万不要学白哉那小鬼任性的坏毛病哦!”
“是。”我偷眼去看,果然远远躲开避免遭殃的白哉脸黑了一层,有发作的趋势。
朽木银铃说:“市丸君,你的归队手续都办完了吧?”
“是的。”
“嗯,”老人总是波澜不惊的眼眸在白哉身上扫过,好像有种晦暗不明的光从里面闪过,随后他垂下眼睛轻轻说:“白哉已领悟斩魄刀,过不了多久就该进行死神测试了,他的训练还要拜托你,没有问题吧?”
死神测试?这么快?开什么玩笑!
我表面客气地应着,却听夜一嚷道:“银铃伯父,这太勉强了,还有那件事你也再考虑一下吧。”
不等朽木银铃说什么,白哉上前不悦地打断道:“有什么勉强的,我始终在为这个做准备,怪猫你不要随便置喙别人家的事。”
夜一对白哉的容忍程度处在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对他这样的态度向来是笑呵呵地回以暴力,于是二话不说把他勒在怀里,不顾白哉悲惨且愤怒的声音,按着脑袋使劲揉:“准备什么,你老爸都要去当副队长啦,哪有你凑热闹的份!”
“什么?”白哉和我同时问出来,不过白哉的声音完全把我盖住,调子几乎都走了音。
夜一丢开被蹂躏的脑袋,叹了口气说:“是真的啦,朽木伯父,以苍纯的身体实在不适合这么做,可他的性格……请你还是劝劝他吧。”
确实,以苍纯的身体状况,副队长的任务远比三席危险艰巨的多,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
“父亲……父亲他……”白哉愣愣地看着朽木银铃,连自己被弄得乱糟糟的头发和衣服都忘了整理。
“会议结束后他在一番队接受副队长交接仪式,现在应该在跟总队长谈话吧。”朽木银铃的脸上透出某种疲惫,走近白哉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两天前副队长在任务中被虚化细菌感染后牺牲了,十番队的薄暮队长推荐了苍纯,他本人也……同意了。”
“切!”夜一啐了口,看样子当时绝对是极力反对了的。
白哉的表情很僵硬,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对于贵族来说这该是种荣耀,照白哉的性格也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才对。可他无论是攥紧的双拳还是全身绷紧的肌肉,抑或苍白的脸,哪里也看不出半分高兴来。
正在这时,苍纯从那条小路的后面走了过来,他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肩膀上甚至落了几片樱花瓣。
“夜一,你怎么来了?”淡淡的笑容几乎能跟这片飘落的花舞融为一体般美好,苍纯对我眨眨眼睛弯起眸子,笑得一如既往那么温柔,说道:“你们该不会在想怎么为我庆祝吧?”
作者有话要说:关于人物的职位安排稍作改动,不然小银子刚出场就让喜叔夜一等人后台休息那多无趣!
然后是十番队的队长,名字是编的,但是下图为百度大神提供的出自漫画某画的图图,应该还算权威,所以当时的十番队队长应该还不是一心。剧情需要少有修改,98大神原谅咱吧!~~
于是对此图怨念中。。。居然把咱的海燕给剪了。。。#¥%&*……顺说,萌物很多啊。。
26第二十五章 副队长
显然苍纯的幽默没有得到理想回应,他本人也被夜一提着领子拽到别处做思想工作去了,我偷瞄了朽木银铃镇定的脸,推测他应该也是拿夜一没辙的。
浦原喜助快来把你家队长领走吧,别让这女人把我纯洁美好的苍纯大人往草丛里拖啊!
之后无视儿子贞操的朽木银铃也走了,白哉犹豫一下追了过去。我看着他的背影挺无语,带着那样慷慨激昂的必胜神色,白哉的目的不言而喻,只是大概不会成功。
这是闹哪样啊?刚热闹的院子瞬间只剩我一人,连我都觉得被小风吹着在我面前滚落的花瓣很凄凉。
不过我很快就伸着懒腰决定不掺和他们,这群人全都忽略了面前的美景,实在太浪费了。于是转到后院前我顺手取了包里的柿饼,在后院那棵大樱花树上找了个舒服的枝杈,坐在上面啃起来。
至于白哉那张看着就知道很舒服的藤椅,还是算了吧,乞丐的屁股如果总是去坐金马桶,也会拉不出屎的。
我只是个平民,流魂街的下层居民而已……住着贵族的大院,睡在继承人的床上,已经连金脚趾都开了,还想奢求什么呢?
蓝染说会留下白哉那时候的脸莫名其妙地浮出来,我从记忆里突然看懂了他当时的表情,眼睛里那么冷、那么讽刺,恐怕在他看来我对朽木家的执着既好笑又不可理喻。
白哉确实能算个值得炫耀的恋人,征服这么高傲的家伙来的要比得到某个追求者众多的女人还要有成就感,然而我当时却只是出自对苍纯的愧疚才想保住白哉,其他的……大概没有吧。
我挑了根很粗壮的树枝,盘腿坐在上面,靠着树干姿势很是懒散,这位置花香浓郁却不呛人,一波一波的总在你觉得它快充满周围空气时就消退了,等到我以为没有香气的时候又会忽然随风吹过一股夹着花粉的清香。
——就像朽木白哉那个人一样,当我觉得离他好像近了的时候,其实却很远。
干柿饼充分发挥了它坚硬的特长,被我放在嘴中无意识地咬着,半天了也没吃进去一口。
我不知道是我的性格改变了这个身体,还是市丸银残留的意志影响了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难琢磨了,有时我会对某些人和事很执着地想得到,有时又会忽然什么都不想要了。
也许正因如此,才会被蓝染相中吧?阴晴不定又摸不透喜好,总是能随时对任何东西产生兴趣,又像随时都能把那份兴趣割舍了。
就好比……我对苍纯晋升副队长的事没什么感觉一样,即便刚才看着他时我还移不开眼睛。
“市丸君?”
心里正想着的人的声音突然从院子里传来,这把我吓得不轻,差点从树上掉下去。
苍纯不知何时回来的,听见响动朝我看过来,微微笑着说:“市丸君,不介意聊两句吧。”
我跟苍纯坐在房顶,老实说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是这种能爬房子的人,心里的震惊久久没有平息,导致我们沉默很久都没人说话。
即使在房脊上,苍纯的坐姿依然很漂亮,他大概是觉得尴尬了,轻声问我:“白哉呢?又去训练了么?”
我摇头说:“刚才跟着朽木队长离开了。”
“是么,”苍纯微垂着眼眸,平静的侧脸和长大后的白哉非常相似,只是多了份柔和,不如白哉的线条那么坚硬。“我知道白哉不希望我成为副队长,可是……”
苍纯把眼睛轻轻闭起来,嘴唇的颜色变得很浅,过分清秀的脸也显得苍白。我没打断他,哪怕什么都不说单是看着就足够养眼了,我也比较能够自娱自乐。
他没沉默多久,便抛弃了之前的话题,转头问我:“跟白哉相处的还愉快吧?”
月色又伴着飘飞的花瓣什么的,这个背景下的美男爸爸让我差点就看得丢了魂儿,苍纯突然看过来时我险些丢脸地从房脊跌下去,手忙脚乱地坐正身子,敷衍地应了他一声。
苍纯笑起来,在我头上揉了两把说:“白哉的性格不像我,更多是像他的母亲,总是要强了些。”
“白哉的母亲?那不是……”我花痴地被他摸猫似的摸着脑袋,全无反感,倒是他的袖子带出股淡淡的熏香味道,似乎比樱花的香气更具有某种诱惑。
“嗯,她过世很久了。”苍纯收回手,把目光放在樱树那片茂密的花海上,“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最开始也是我拼命坚持才成为死神的,那时候白哉的母亲也很反对。”
苍纯的眼睛并不纯黑,有一点淡淡的紫色,平静时总显得幽深,可一旦融入微笑时就璀璨得仿佛是两块暗紫色的水晶。
他说:“所以我比谁都清楚我是做不了家主的,这些年来白哉也该明白这一点了,因此才总是比任何人都努力,总是要把压力放在自己的肩上……我是个笨拙的父亲,不知道怎么才能对他好一些,真是……”
看着那笑容中隐含的让人心疼的无奈与苦涩,我耸耸肩叹气道:“笨拙这点,白哉倒是很像您。”
“是吗?”苍纯怔了一下,随即笑道:“你是第一个这么评价他的人,大多数都会说他任性,其实我本来希望把性格遗传给他的。”
“啊,可惜您失败了,如此优秀的地方他可是一丁点都没拿走。”我毫不夸张地挑挑眉梢,如果白哉能有他老爸一半的温柔,想必抢着把女儿送到朽木家的人早就把门槛踩烂了。
苍纯忍不住笑得出了声,说道:“他是有些被宠坏了,长久以来也只有夜一算是跟他比较要好,不过现在不同了。”苍纯脸上浓浓的笑容还在,他却把弯起的眼睛睁得很大,认真地看着我说:“没想到你会跟他成为朋友,我倒希望以后也是,有哪一天我……嗯,那时候还有你还能帮助他。”
——他这算是把儿子卖了么?
直到苍纯已走了很久,我还坐在房顶暗暗吐槽。跟白哉要好这纯属意外吧,因为我的某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要是早个百八十年穿来,我会拼了老命让白哉喊我“爸爸的老公”的。
带着这不可言喻的悲哀,我坐到半夜才回卧房,白哉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不过我进来时他并没动,估计是睡着了。
我看着离他也就半米的距离,默默把自己的被褥拖到榻榻米的边缘,尽可能地拉远了距离。
然后躺下,在我盯着天花板足有五分钟还闭不上眼睛后,我更加悲哀地发现自己根
![[死灵]黑暗王座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6/679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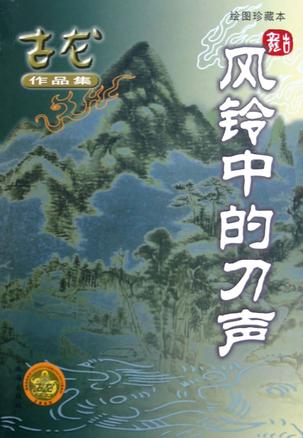
![033 [死神同人]爱要说出口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noimg.jpg)

![[野良神]捡到一只惠比寿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37/378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