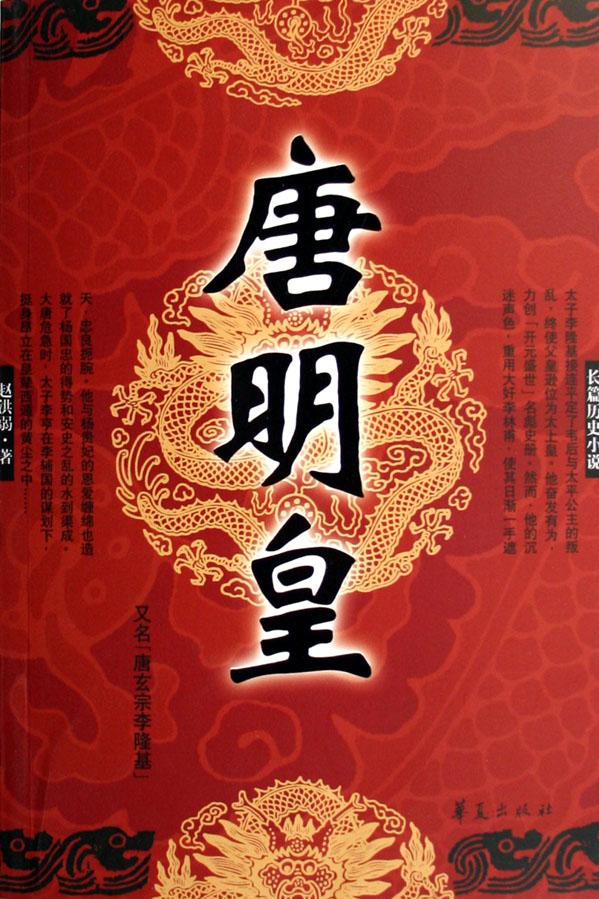明皇-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子祺煜高坐在太子位上,还想着刚才的事,怀疑着祺谧是不是在躲着他,放心不下。细想起来,这些年祺谧帮着他做了不少事,虽然受赏的总只有他一人,但他也不忘分一份儿给祺谧——尽管他从来也不曾收过。有时他在怀疑,要是没有祺谧,他还能不能那么出色的完成好皇上交待下来的事儿。所以,他早早就下了决心,等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他一定要给祺谧最显赫的地位。然而,刚才的事儿,他却没法儿释怀。
想到这里,他又不自觉地想起了祺瑾。他是和祺谧一样优秀的人,可是他却好像从来都看不起任何人。他会和他争起来的。
燕亲王祺瑾与七皇子祺珉和九皇子祺珞在同一席。七皇子祺珉是齐贵人所生,而九皇子祺珞是熹贵人所生。子凭母贵,两位皇子虽然尊贵,但远不及早已加官进爵的祺瑾。这三人在一起倒也难得——无论是皇上赐宴还是过去皇帝赐宴,都极少按众皇子齿序来设席,所以他们在一起不致于太热闹,也不致于太冷清。三人说着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你一杯我一杯,喝得也不少。
祺容和祺珊本来不在一席,但两人却换到了同一席,乐呵呵地吃菜喝酒。
祺璇和祺玫两人是一席,正好两人关系好,又成天在一起。但这两人却都不怎么喝酒,倒是茶,喝了不少。侍候他们这一席的宫女太监也乐得自在,泡好了一大壶茶也就完事了。
略往席下一看,太子祺煜便看见祺璇和祺玫两人在喝茶而不是在喝酒,他便端了酒杯往他们席上走去。
见太子过来,他俩人忙举了酒杯站了起来:“太子爷。”
太子祺煜一笑,看了看他们桌上的菜,故意板起脸:“怎么,嫌你们二哥这儿酒不好?我来了才肯举杯?”
“哪儿会呢?”祺璇忙道,“您这儿的酒自然是好酒。”
“那怎么要喝茶呢?”太子祺煜又道,“祺玫,二哥知道你酒量好着呢!怎么不喝酒?”
祺玫看了祺璇一眼,呵呵一笑:“这不是晚上还有事么,酒喝多了,多少有些误事儿。所以才不敢多喝。二哥,您就别见怪。我们在这儿罚三大杯就是。”
“是是。”祺璇忙帮腔,并一叠声儿叫人拿了大杯来,同祺玫一道连喝三大杯。祺璇和祺玫相视一眼,祺玫笑道:“这酒也罚了,哥哥还是饶过我们吧。”
祺煜一笑,正要说话,没想到一个柔宛的声音静静的从殿外就那么悠悠飘了进来:
“十六弟十七弟年纪尚小,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太子爷最是疼爱弟弟,怎么会与十六弟十七弟计较是喝茶还是喝酒呢?”
祺煜一愣,循声望去,却见着白婉带着洛姗婷婷站在那灯火阑珊的地方,大方得体地浅笑着。
白婉微微一笑,进了正厅,端正地向祺煜福下身去:“臣妾参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千岁。”
祺煜一笑,虚扶一下:“弟媳妇儿不必多礼。”
白婉就势起身又向三皇自康亲王祺月福下身去:“给三哥请安,三哥吉祥。”
祺月哈哈一笑,忙道:“快起来吧……”他的话没有说下去,见着太子祺煜略显阴沉的脸,也就知道其中必有些不知情的过往了。不过他心中还是暗自奇怪:白婉一向谨言慎行,说话做事那是滴水不漏,难不成得罪了太子?
白婉微微一笑,看了祺煜一眼,淡然起身。
见着白婉,五皇子、八皇子,还有十六、十七这些弟弟忙起身行礼:“见过四嫂,给四嫂请安。”
白婉一笑,温和道:“弟弟们快起来,都是一家人,何必拘礼呢?”说到这里,她看向祺煜,顺手拿起洛姗手中的礼盒:“这是王爷差我送来的礼物。王爷说:‘因生着病,刚才的事多有得罪,请太子爷见谅。太子爷的晚宴,臣弟不能参加,心中实在不安。’所以差臣妾送来上好的梨花白,给太子和各位爷助兴。”
“呵呵,还是四弟有心。”祺煜不自然地一笑,命人接过礼盒,“弟媳妇儿既然来了,就喝杯酒再走吧!”
“谢过太子爷美意。”白婉莞尔一笑,“臣妾不胜酒力,怕酒后失态,扫了太子爷兴致。臣妾这就告辞了。”她盈盈福下身去,转身向厅外走去。走到祺璇和祺玫席边,她停住了脚步,却淡淡看了祺煜一眼:“刚才父皇吩咐,叫我见着了你们,就告诉你们,明儿要亲自考察你俩的学业,叫你俩今晚好好准备。”说毕,她又看了祺煜一眼,却是冰冷得紧,出了正厅,很快就离去了。
有白婉的话在那儿搁着,祺璇和祺玫就有了正当的理由离席,而太子也不好说什么。在座的皇子都不以为意,唯有祺瑾盯住了他俩。打着方便的幌子,他出了大厅。在夜风的吹拂下,他的头脑分外清醒。招来自己亲醒的侍卫,低声叮嘱几句,侍卫迅速离开。祺瑾进了大厅。
星夜。
觥筹交错。
暗流涌动。
第三章 棋局(1)
清晨。
太子祺煜刚刚起床。昨夜侍寝的南妃云鬓松散,懒懒地倚在梳妆台边描眉涂粉,不时从镜中窥视着穿朝服的祺煜。
祺煜脸色不太好,他依旧在回想着昨夜与祺瑾的冲突恍忽间好像两人还动了手,是谁给劝开的,哦,是祺月和祺容,之后怎么样,他就记不清了。可他清楚地记得他和祺瑾的争吵:
“谁不知道您太子爷最妒贤能!”这是祺瑾说的,“要不是四哥病了,不知道您会怎样挤压他呢!太子爷,二哥,我没说错吧!”
他气得脸煞白,只觉得愤怒:“说什么浑话!这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我最敬贤能,这朝中多少贤士都是我推荐的……”
“你?”祺瑾大笑着打断了他的话,“天大的笑话!您,太子爷,二哥,您举荐的人有几个是贤士?笑话!不能谏,不懂言,只知道拍马阿谀,这叫贤士?笑话啊,天大的笑话!”
“住口!”一怒之下,他摔了酒杯,却又隐忍下来去维护太子的尊严,“八弟你喝醉了。来人送燕王回府。”
“不用人送。”祺瑾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又扫了一眼那些目瞪口呆的皇兄皇弟,他祺瑾清醒得很,没醉,但想借着这酒,把话挑明了,“多谢您了,太子爷,二哥。太子爷,二哥,您很愤怒吧,对不对?不用忍,在这儿,在东宫,您不用忍。父皇不在这儿,您不必装大度,装温良!太子爷,二哥,您是不是在盘算着怎么把我,您的八弟,不着痕迹地挤压出朝堂,甚至至于死地呢?户部是个很好的工具,对不对?毕竟管了户部三年的人是我,您不过接手三个月,我是主犯,您是从犯,再怎么着,您也没罪,干脆一古脑儿推给我,您就高枕无忧了……”
他的一个耳光让祺瑾闭了嘴:“你醉了八弟。来人,送燕王回府。”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祺瑾竟还了他结结实实的一耳光!祺瑾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你没资格打我,不自律何以律人!”
再然后,他们就打起来了,再后来,祺月和祺容拉开了他们。祺容和祺珊送了祺瑾回府,而他,叫人散了席。
想到这里,他下意识摸了摸脸,自失地笑了笑。南妃从镜中看着,娇滴滴地笑道:“太子爷,有什么好笑的,说给妾妃听听,成吗?”
祺煜看向她,一笑:“怎么,从镜中看我呢,是镜中的我好看,还是镜外的我好看,恩?”
“恩,当然是一样好看。”南妃极妩媚地对着镜子笑道。
祺煜一笑,正要说话,一个侍卫慌慌张张从门外进来,举着一个信封:“户部紧急调人。”
“什么?”祺煜顾不得南妃,一把夺过信封,急急拆开:昨夜皇上亲下手逾任命两名侍郎……怎么会这样?祺煜皱起眉头:信上没有两名新侍郎的名字,看来是没有人认识,会是谁呢?“备马。去户部衙门。”祺煜把信收好,匆匆出了门。
宁音宫
年太后倚在窗前对着光看着一本书。一个小宫女蹲在她脚边轻轻为她捶着腿。年太后看了会儿书,又放下,把目光投到了那个小宫女身上。她暖暖地一笑:“你叫什么名字?”
小宫女一惊,小声答道:“回太后的话,奴婢贱名丹雪。”
年太后暖暖地一笑,又问:“多大了?”
丹雪有些惶恐,依旧是小声答道:“回太后话,奴婢十四了。”
“到本宫这儿多久了?”年太后暖暖笑着,“抬起头来让本宫看看。”
丹雪依言抬头,怯怯地看着年太后,不敢出大气。
年太后暖暖地一笑,略一抬头,见贤皇进来了,便站了起来:“怎么今天有空过来。这么早,不用上朝么。”
贤皇一笑,快步来到年太后身边,扶着她坐下,自己也坐下了:“昨儿夜里就把事交代下去了,今天休朝一日,来陪陪母后。”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看见了丹雪,便肃起了面孔:“这是哪儿来的宫女,见到朕不知道行礼么。”
丹雪一听这话,吓得快要哭出来,更加忘记了该行礼,只是瑟瑟地跪在那里,不敢动,更不敢说话。
见此情景,年太后反而是一笑:“她还是个孩子,又没见过你,你这么一嚷,吓着她了。”说到这里,她和颜看向丹雪:“你下去吧,叫荷茗上茶。”
丹雪怯怯地向太后和皇上告退,什么都不敢多说,飞快地出了正殿。
看着丹雪的背影,年太后暖暖地笑着:“当年我进宫时也是这么大,也是被分在太后宫里。一晃六十多年都过去了,我都是太后了。看到这样的孩子总会有一中心疼的感觉。”她看向贤皇,笑得依旧温暖:“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贤皇一笑,道:“母后仁德。”
年太后一笑,淡淡看了他一眼:“今儿要没什么事,陪我下下棋吧。好久没碰棋了,还有些想念呢。”
“好啊。”贤皇满口答应,“难得母后有兴致,儿也好久没同母后下棋了。”
随侍的宫女听了他们的对话,忙取了棋来,放在茶几上,知趣地退了下去。
年太后的棋风和贤皇的棋风很是不同,,贤皇是激烈的,太后是柔婉的。不同于贤皇与雪德妃的对弈,太后的迟缓,让贤皇感到很急,有时,他甚至想代太后落子。白子连连被吃,丢城失地,这时,本该苦恼的太后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今儿早上我听说,昨儿祺煜和祺瑾打起来了是不是啊?”年太后淡淡一笑,看向贤皇。
“是。”贤皇奇怪的看向她,想不通她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你怎么看这事呢?”年太后笑得温暖。
贤皇一笑:“母后,儿不想多说那事。”
年太后一笑,道:“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多年,经过了那么多血雨腥风,有什么是我看不透的呢?这局棋,表面上你占尽上风,可如果你仔细看看,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胜算。我不是你的生母,但是我养你成人,扶你上皇位,助你掌得大权。我也老了,日子也不长了,只有一句话想告诉你,不要让景皇晚年的旧事重演。”说着,她颤颤地站了起来,依旧是暖暖地一笑:“年纪大了,容易乏。这棋看来是没法儿下完了。叫人原样收好,咱下次再下吧。”
户部衙门
太子祺煜高坐在大堂上,户部的大小官员整齐地站在堂内,唯独不见皇上新任命的两名侍郎。太子祺煜不免有些不满。
“新来的两位侍郎呢?”太子祺煜故意闲闲地问,“怎么不见人影啊?到任的第一天就不到,太嚣张了吧。是不是该罚呀?”他看向户部尚书骆武寅,把最后一句话又重复了一次:“是不是该罚呀?”
骆武寅恭敬地点了点头:“太子爷说的是,今日户部大小官吏都来,独缺他二人,分明是不把太子爷您放在眼里,受罚是理所当然。”
听着骆武寅的话,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