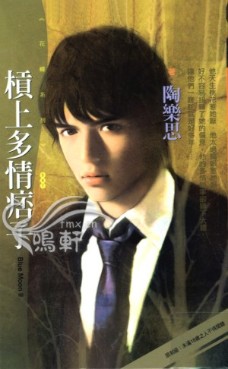侬本多情种-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本来就很单纯、没心思。”乔释谦不满地开口:“靖心,你很介意吗?”
介意?当然介意。一个妓女,那是她想都没有想过的事,多么航脏!亏她还一直跟那个女人交心,甚至要把她当自己的妹子,谁知……赵靖心转开身子,没让丈夫看到她充满厌恶的脸。
“我怎么会介意。”她低头咬牙切齿地说着,口气却一迳维持着温柔的语调。
夫妻多年,她太了解乔释谦了;就算真的讨厌白苇柔,她也不会笨到在他面前表现出来。
他是那样正直的一个人,凡事只求无愧于心;至于甚么人言可畏,他从来不放在心上。
“要是我没调她走,你想她跟着我来来去去,就算绣儿不说,其他人瞧见了,传回娘那儿,只怕她连待都待不下去。”赵靖心停顿了一会儿,见他没反应,才接着继续说:“倪家也是地方上的大户人家,这件事就算不明着摊开来谈,难道就阻止得了私底下别人的指指点点?你可以不理会,苇柔怎么办?她已经够难堪了。”
“是吗?”他不甚关注地回答,心里仍想着白苇柔。
“对方人这么多,你一个人势单力薄,要真吃了亏,那怎么办?看你的手,都划伤了。”她握住他的手:“我帮你上个药,忍耐一下就好了。”
翻开手掌的同时,他瞧见了那主姻缘的掌纹,是那样平滑而绝对,触目而刺心。乔释谦的手急急抽回,一颗心不自觉地疼了起来。
苇柔!他心里喃喃地喊着。他对不住她,也不如她。在倪振佳污蔑赵靖心的时候,白苇柔替他先有了反应,而事后他却连帮都没法帮她。
“呃……靖心,抱歉,是我太莽撞了。这点伤不碍事,你别担心。”
她仍然为他的举动错愕不已。
他长吁一声,握住她的肩。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最近总是心神不宁。”
“别这样,你做得已经太多了。只是乔家上上下下的事太杂,而我能帮的又有限。”赵靖心回神,手指柔柔地拂过他的脸:“有时侯我只怨自己做得不够多。”
“为甚么要这么说?”他起身揽住她,语气有浓浓的歉疚。
他不了解自己是怎么了,似乎有东西在心里渐渐侵蚀他对赵靖心的忠诚。他变得不再全然包容,就像方才,他不自觉地就对她放大音量,不自觉地跟她生气,甚至只是一条无关是非的掌纹,也能令他心神不定。天!那是他从来就不会做的事。
“你是我妻子啊,疼你、照顾你是我该做的。”他抚着她的颈背,语气掩不住心疼。
是吗?真是这样吗?赵靖心抚弄着他的头发,凄柔地想着。
当年倪家和乔家同时派人至赵家提亲,她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乔释谦。事实证明父亲并没有错,乔释谦也许沉默了些,但待她却是深情意恳的好。
后来她才知道,受洋派思想教育的他刚开始是抱持着抗拒的态度来面对这桩旧式婚约;但从她踏进乔家,却没见丈夫对她皱过眉头,更别说是大呼小叫。
赵靖心最感佩丈夫的,莫过于此。为此,她全心全意地爱他,但她的温柔却不能弥补她的缺憾。
她苦恼地软口气。爱是怎么样的东西,或者她从来就没懂过。她一直以为,上辈子她定是积了德,才会让她得到他;因为他的体贴、他的关怀,都是别的女人无能侵犯的。
而现在,随着白苇柔过去的揭穿,一切都不一样了。赵靖心握着方才被拒绝的手,一种从未有过的忿怒意识翻腾地涌上心头。
枉费她这么信任那女人!赵靖心转过身,仍一贯温柔她笑着。她不会再让那女人靠近乔释谦一步,那样难堪的过去,她不会让乔释谦沾上任何一点的。
对,她要保护乔释谦。
“苇柔!”
赵正清喘息着奔进来,倚在门边,两眼慌乱又不安。
她抬起头,勉强应了一声,而后垂头沉默地打包自己的东西。
“我……我才进门,便听到张妈说……她说……”赵正清语气有些结巴,口气震惊又质疑。“苇柔……”他呐呐地又喊了一声,却不知该如何接下去。“那些事……是真的吗?”他问得小心翼翼。
她没有回答,也始终不曾再抬头,赵正清无从得知她的表情。
“苇柔,那不是真的,是不是?你为甚么不替自己说点甚么?”赵正清抓住她问。“你说呀,哪怕是一句话我也信。那个倪振佳本来就不是甚么好东西,我自然是信你的。”
“我走了,赵少爷。”
不否认,那就是默认了?赵正清重挫似的呆站在原地。
“怎么会这样?”他喃喃自语。那么美好纯洁的一张脸,背后怎么会有这样的过去?“苇柔,其的是那样吗?”
白苇柔脚步没停,过去几个月辛苦建立起来的平静全被捣毁了。没人想过她的感觉,她难道不是最该哭的那个人吗?也罢,经过这一切,身后这个男人也可以清醒了。
正月新年。
月上柳梢头,小屋子里白苇柔打散了一头长发,仰首凝望着那弯单薄的月牙儿。
在这除夕夜,除了留守的、返乡的,所有的下人都聚到主屋守岁去了。
只有她,早在张妈的事先警告下,假托了身子不适,躲在无声的小屋里。
但这样的借口却引起乔释谦的关心。在欢喜热闹的新年里,他不知道为何怅然若失。
走来探她,却也只是站在门外,避至暗处不敢出声。
从她搬离主屋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他不曾再见过她一面,而今,他却不知该找甚么理由见她。手里的灯笼微微打颤着,彷佛就像他的心,但却无关寒冷。
他终于轻声叩窗,推门而进。
乍见他时,白苇柔一怔,随即想起自己仪容末整。还以为今天是不可能有人到这儿来的,没想到……她慌乱地将一头乱发朝后拨去,脸颊涨红,神色尴尬莫名。
“你……怎会到这儿来?”
“他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抖落衣上的雪,他收伞进屋。烘炉里的火光暖暖地扑面而来,他凝视着她,非但不觉得她失礼,反而那天井上的雪映着火花,衬得她黑黝黝的发丝在夜里更灼亮。
“你好吗?”
她轻轻应了声,就没下文。
“怎么不到主屋跟着大伙儿一起庆祝?我还记得中秋夜你玩得很开心。”
提到中秋,她更恻然了。显然那欢乐对她而言,似乎已很遥远了。才两天不是吗?她搬出主屋才两天,有关她过去的那段流言却随着张妈的有意无意传遍了乔家;除了乔贵和蒋婶待她依然,其余的全都跟她有了距离。
这样霜雪皑皑的新年,她哪里都不属于,连乔家都不是她的依归。
寂寞,才是她生命里永远挥不去的影子。
白苇柔叹了一声,起身走到后头起灶烧水。
“苇柔,在乔家你不开心?”
“没有的事。”她抬起头,突然像发现甚么,盯着他衣襟上一处裂缝。
在那一刻,她很想伸手拉住他,可是却没这么做。
“你衣服裂了。”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有些赧然她笑了起来。
“亏你说了,还是新衣服呢。我没注意,买衣服的下人也没留神,真糊涂。”
“我替您补上吧。”她口气淡淡地说,只是心里深刻地明白,在他面前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注意,所有事情都会失去原有的规律。
“那……麻烦你了。”乔释谦褪下衣衫,望着她穿针引线。依着烛光的银针随着她指间奔梭来去,静静缝缀着。
天井上的雪依旧无声地下着,在屋檐上一块块地冻结起来,静静的甚么声音都没有,乔释谦无法不注意他那愈来愈幸福又不安的心。
他默默地想着,在白苇柔身边总能轻易找到他一直冀望拥有的感觉;但这种心绪却让他变得事事无法拿捏、无法决定,这完全矛盾。
领着丫头回房的赵靖心在小屋院外停了下来,她无法不去注意房间里那熟悉的侧影──丈夫的脸庞尽收眼底。
温柔、怡悦,像是猝不及防被人揍了一拳。赵靖心猛然退了一步,背后的绣儿擎着伞撞上她,伞柄微微自肩上斜去,倾落了她半身碎雪。
绣儿在身后困惑地瞧着她,而赵靖心怔忡了一会儿,僵着身子又往前走去。
就在交还外衣的时候,乔释谦再度碰触了她的手。然而这次他却不假思索,紧紧握住了那双冰凉小手,口气中透出浓浓的忧悒。
“你的手总是这么冷。”他烦恼地说。
白苇柔蓦然引来一阵心酸。
“老毛病了,一直……都这样。”她不着痕迹地移开手,在唇边轻轻呵着,和着那壶水沸腾的雾气,在两人之间如烟般的飘起。
她小心自灶上提下水壶,替乔释谦冲了杯茶。
“你可以跟大伙儿一块到主屋守夜的。”
“不了。”她摇头低语,眉目黯然。“我想……一个人静静。”
“也好。谢谢你替我补衣裳。”知道她的犹豫,乔释谦也不再坚持。
“别这么说,苇柔应该的。”
“过完年,这天气还得冷一阵子呢。”乔释谦轻啜了一口茶,看看屋外,依然雪意未消;而茶入了喉,却有些苦涩。回头他又说:“没事多披件衫子,不管在哪儿可都得好好照顾自己,你答应过我的。”
“嗯。”她点头,唇边浮起柔顺的笑。但被握痛手的心酸仍持续着,令她更想流泪。
不管如何,都得好好活着。活着,才能好好爱人;活着,才能感受别人对你的爱。
这是她亲口对他说过的话呀,但是……但是……他感觉到了吗?白苇柔在心里哽咽地问。
“我回主屋了。如果……你改变心意的话,随时可以加入我们。”
“嗯。苇柔送少爷。”
是甚么原因她已无法追究了,白苇柔将手绢儿紧紧搁在胸前,彷若守护着自己一颗随时会崩裂开的心。他的影子在灯下愈拖愈长,让她不由自主想奔上前踩住他颀长的身影。
或者,她傻气地想像着,那便可以把他一部分的人偷偷留下,成为她永远的私藏。
也许这样能让她碎裂的心缝合一些些。
但是她始终没敢这么做,她只能握紧拳头,绞扭着不成形的帕子,拚命挤压着胸口,彷佛这么做就可以制住自己的不应该。
赵靖心拥有的那一部分,是她不敢想,也没资格拥有的;她只希望有个影子,就算是渺无实体,只要那是乔释谦的就够了。
被握住手时的心酸是为自己流的,因为再也没有人像乔释谦待她这样。白苇柔长吁一口气,眼中蓄满了泪。
天可怜见,她如此卑微,但却那么样……那么样地爱他!
所以,她无法自私,也不能自私。
寒意漫漫而起,拖曳着屋里残烬的烟灰。她仰首望着天空,想起初识他的那一天,也是失去孩子的那个夜晚;更无法避免地想起他曾不吝惜送出他的温暖,只为让她分享。
他的气息、他的呼吸、他的味道、他在沉默之中的温柔……
转头看着茶几上那只陶杯,她轻轻把杯子托捧而起,颤抖地将脸颊轻轻贴在乔释谦适才嘴唇沾过之处。
强风莫名袭来,彷佛把那雪花的寒意飘摇得更浓郁了。
如果我只能这样子爱你,只能这么拥有你、守候你,那么,就这样吧。
闭上眼睛,白苇柔感觉忍了许久的泪水,温热地在脸颊上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