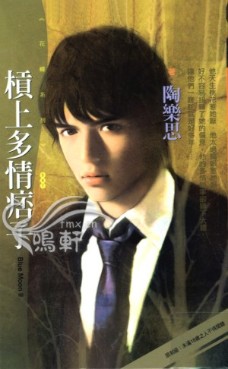侬本多情种-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苇柔仰起脸。“离开乔家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爱个人竟是这么盲目的。你嫌弃我吗,释谦?”
他回过神,苦涩地摇头。现在他生活上唯一一点卑微的快乐,就是来看白苇柔;然而,为了赵靖心,今日一见,他却要彻底说明白,从此不再见她。
“你不该这样,是我委屈你了。”
我不在乎,她心里喃喃地说着。失去你,跟过去的孤孤单单又有甚么两样呢?
是你,让我明白身上的寂寞并不可怕,那心里的孤独才是让人不能忍受的。
她垂下头,慎思了一会儿,紧接着抬起头,温柔的眼神带着坚定。“不管你怎么想,我不会再见你了。但请允许我看着你,因为,那是我这辈子想要走的路。”
他隔着层层细雨雾烟,疑愣地望着她。
“赶紧回去吧,小心着凉了。”她走近身替他拭净脸庞沾附的雨珠,约莫是气温过低,她的手触在他脸上,冰冰凉凉如雨水。
“我们只能这样吗?”他哑声问她,也问自己。
“这样就够了。”白苇柔倾身向前,轻轻地靠进他怀里。“我们谁都不去伤害,我不争甚么、不求甚么,就这样,能够这么近地看着你、靠着你就够了。就这一刻,当定是天长地久。”
“我……何德何能?”
“别再说这种话了,我会生气的。你没见过我生气吧?”她笑着,又替他拭掉几滴雨水。“我回去了,你就在这儿,看着我走,甚么都别说,也别不放心。有你的眼睛望着我,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回去的。”
乔释谦松开她的手,看她擎着伞,雨光在油伞下飞进飞出;白苇柔一身月牙白衫,透明地穿过那绵绵细雨,渐渐消失在人群里。白苇柔始终没有回头,好几次,他想出声唤住她,奈何她走得轻盈又坚定。要不是她方才才说过那番话,他会以为她是来向他告别的。
风势渐渐加大,雨丝顺着风斜斜打湿了屋檐,被白苇柔拭净的脸庞又萌生了雨花,在脸颊、在耳畔、在乔释谦每根发梢上。
因为,那就是我这辈子想走的路──
那何尝不是他想走的路?一路的风雨、山光、水色,都是他渴望拥有的;可是他身在另一方上,再也走不回来时路。
颓然坐倒在台阶上,乔释谦捧住脸,任由雨水湿透他的衣领。
听到隔壁大婶说有个大夫找她,白苇柔半猜半疑地走出来;看到赵正清站在路口,正左右张望着。
“赵大夫。”她有些局促不安地唤着;原以为的鄙视和怒气却没在他脸上瞧见。
“这些日子你就住在这儿?”赵正清掏出帕子揩汗,又探头说道。
“嗯,我就住在里面,最里边那间便是。”
“一切都还过得去吧?”
“我还想着……想着……”她仍不安地望着他。
“想甚么?你为甚么这样看我?”
她放松她笑了,语气有些忧愁:“我以为咱们俩不再是朋友了,你会因为那件事而恨我。”
赵正清一征,也笑了,只是他的笑容很苦涩。“没有的事。这些日子,我……我姐夫可有来看过你?”
空气中沉默了一分钟;她停了一会儿,在台阶上坐下来。
“有。昨天,他……是来结束这一切的,你相信吗?”
没等他开口,白苇柔抬起头,眼神很哀伤。
赵正清退了一步,那笑容极似乔泽谦,都是被爱折磨,为情神伤的容颜。来这儿要劝说她离开乔释谦的话,突然便在赵正清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
“我和你姐夫之间,真的是清白的;就算真有甚么开始,也都在我搬出乔家的时候就结束了。”她虚弱地开口:“我爱他,也只是我的选择。我没有心要伤害少奶奶,你姐夫明白,所以他才找我说清楚。”
他无言以对,只好问她将来有甚么打算。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法子的。再过一段时间,我会和杏雪姐离开这儿。”
提到江杏雪,赵正清的心顿了顿,蓦然忆起日前她离开时那含恨的眼神,歉疚感油然而生。
“杏……呃……江姑娘……那日我心急,言语中得罪了她,不晓得她是不是还记在心上?”
“杏雪姐都跟我说了。”白苇柔幽幽地开口:“唉,我也不知该怎么说。你同她相处过,该知道她的脾气和个性都很刚烈。真有羞耻心的女孩,若非逼不得已,是怎么样都不会往火坑里跳的。谁不想活得理直气壮、活得争气?但这世上,何曾让每个人如意过?赵大夫,待在怡香院的日子,我们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没有未来,日子过一天算一天,那滋味比在太阳下做一整天的苦力都还来得难受。你实在……实在不应该对杏雪姐说那些话,换作是我,也……不好受。”
“所以那时侯你在倪家,才会宁死不屈?”
“我不会再跳进去了。”她望着自己余晖下摊平的手掌,柔软的指甲因为捡拾柴火而沾上的污垢,还有虎口握斧劈柴磨出的厚茧。“就算真的没人帮我,我也要靠自己养活自己。”
“杏雪她也这么想吗?”
“当然。”白苇柔抿嘴一笑,站起来拍拍衣袖。“赵大夫,我得烧饭去了,失陪。”
“赵大夫、赵大夫!”远远地,张妈人未到,偌大的嗓门含混着焦急,吃力挪着小脚,一路跌跌撞撞地奔过来。
白苇柔亦回身,同赵正清困惑地望着张妈。
“苇……苇柔,你也在这儿?”张妈急急煞住脚步。
“张妈,您怎么匆匆忙忙?”赵正清扶住她。
“没时间说了!快!”张妈喘息着,额上全是豆大的汗水,气急败坏地拉住赵正清的手肘:“少爷……少爷出事了!快跟我回去看看。”
血色自白苇柔的脸上褪尽,她脚一软,及时抓住了张妈问:“怎么……会这样?”
“还不是那怡香院和倪家。”张妈狠狠朝地上吐了口痰渣子。“狗娘养的龟儿子,也不想想他们是甚么身份,竟敢动脑筋到这儿来!我跟阿贵说好了,回头少爷要真有个甚么,咱们一伙儿全杀上倪家去,非让他们以命抵命不可!”
“我也去!”
“你去甚么去?”张妈此时才发现她的存在,恼怒地推了她一把。“你还嫌给咱们乔家惹的麻烦不够多吗?你这小贱人,谁沾了你谁倒楣!要是少爷真出了事,你也是凶手!”张妈鼻一酸,恨恨地瞪着她。
白苇柔张口欲言,眼泪却先不听使唤她跌下来。“张妈,苇柔……苇柔怎么会害乔少爷?他是我的再造恩人,苇柔这条命也是他救下的,我对他只有感激,只有……”
“够了!谁听你这一套!”张妈不屑地撇过头去。
“别说了,这又不干苇柔的事!都甚么时候了,你还嚷嚷,还不赶紧跟我回去!”怕她愈说下去,白苇柔会愈难堪。赵正清扯住张妈的衣袖,频频朝外走去。白苇柔见步要跟,却被赵正清拦下。“乔家有老太太在,那儿你是不方便去的。苇柔,不如你留在这儿等消息,我再差人过来告诉你。”
“我……”
“别说这么多了,我们走了。”
乔释谦是在回乔家路上,傍晚时分在郊道上遇伏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他还来不及应变,头上便挨了一棍。虽然仍有反击,但寡不敌众,最后终被打倒在路旁,奄奄一息地躺着,还是被人认出而送回乔象的。
主子不明不白受创,乔家大小自是乱成一团。蒋婶匆匆走过川堂,到后院的井边打水。后院梧桐树下,孤零零站着一个身影。夜黑风高,蒋婶有些胆怯,但仍鼓起勇气问道:“谁?谁在那儿?”
“是我。”那身影移动了,待走近些,蒋婶看清楚来人的模样,不禁诧异。
“你在这儿待多久了?”一握白苇柔的手,竟是冰凉透心,蒋婶不禁心疼起来。
待多久了?她茫然地望着蒋婶,又呆滞地瞪着乔家已烧过大半夜的灯笼。待多久了?不知道情况如何,不知道结果如何,时间有甚么意义?
“我……”她盯着蒋婶,突然双膝一软,整个人重重地跪了下来。“蒋婶,苇柔这回给您跪下了。苇柔给您磕头,苇柔求求您,求求您帮帮我!让我看看少爷,让我确定少爷好不好?我真的没办法了,求求您!”白苇柔六神无主,双膝一弯,额头喀喀喀地在地上撞了好几下。
“你这是做甚么?起来、起来!”
见她这样,蒋婶哽咽了,忙把她扶起来。
“你这傻孩子,何苦介入这场是非呢?”看到她额上出现了几道血痕,蒋婶不禁老泪纵横:“见了人又能怎么地?老夫人要知道了,只怕你连这城里都待不下去了。
“苇柔不会让老夫人知道的,不会连累您老人家的,不会的……”白苇柔一个迳地猛摇头,泪眼汪汪地说。
“今晚阿九和我守夜,我想法子把人支开,你小心点,别让人给瞧见了。可是万一……要是少奶奶在,我就没法子了。”蒋婶为难地看着她。
白苇柔望着她,眼底浮现了绝望,但她还是点点头。
在这个家,如果还有人是她不想去面对的,那应该就是赵靖心了。
“我懂。谢谢您,蒋婶!”
赵正清帮乔释谦包扎伤口时他曾经惊醒过,然而那只是一下下,之后他使又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在极度疲倦之中,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再度张开眼睛时,他困难地侧过脸,好一会儿才从外头透进的光线中察觉有个人正伏在床边注视着他。
“甚么时候了?”他哑着声音问,才发觉身体的每一寸都沉重无比。
“你醒了!”那个女人带着笑轻喊,声音哽咽。
有一瞬间乔释谦以为是赵靖心,慢慢地,视力在瞳孔中渐渐被凝聚,对方的脸隐没在灯火未及的部分,他只能勉强看清女人整齐梳在耳后的发髻。
“靖……靖心?”他困难地试探,将被子推下一些些,对方并没有应答。
认出那压抑着的啜泣声并不是妻子,乔释谦心不能遏止地急剧跳动。
“苇柔?是苇柔吗?”
“是我、是我!”白苇柔紧紧握住他的手,手背贴着他微烫的脸。
她再也不挣开他的手了,再也不管这该与不该。谁规定爱一个人是罪大恶极?她加重力量抓着他的手,忍了许久的泪水跌了下来。不要不要!她拚命摇着头,她不放隍7d他,老天要罚,就罚她吧!罚她一辈子无依无靠,罚她一辈子劳劳碌碌,甚至罚她下辈子也这么命苦;但只求别对乔释谦太残忍,别让他为她再受任何伤害。
“你头还疼吗?昨天,他们说你吐了,高烧得厉害。我在院外一直等、一直等,不晓得你到底怎么样了?”她焦灼地说,又把他拉下的棉被覆上。
“你不该来的,咱们……说好的。”他无力,偏也无意挣开她的手。
“可你受伤了,我怎么样都放不开呀,是不是?”
“苇柔,那是我的事,别再说了。”
“我知道,但我会担心。我们可以约定……再世不碰面,可……可你没跟我约定要我连心都不能记挂着你,不是吗?就算你要跟我这样约定,我也……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她轻轻啜泣。
他为这些话深深撼动了,那不是甚么千古名句,也不是甚么浪漫诗词,但他就是这样被深深打动了。乔释谦的眼中,不知不觉地浮起泪光……
他猜那是因为手臂的伤口,才令他如此脆弱。
“苇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