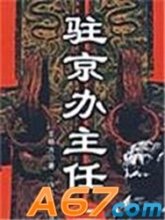驻京办主任(二)-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2、心灵庄园(4)
行刑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吸了最后一支香烟。他戴的眼镜还是在香港配的那副一万多港币的眼镜,他现在正戴着这副眼镜望着天边的火烧云。他本来是想用这副眼镜的镜片插入自己的喉管的,但是他实在是下不了手。他太留恋这个世界了,眼前的草坪就足以让自己体味活着的美好。一切就快结束了,院子里一丝风都没有,六七个人看着他,表情麻木,他们看得太多了,理解不了一个要死的人此时的平静。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平静有点豪迈,像个汉子,这大概是自己人生最后一次辉煌了。死对于他来说是幸运的,他是白山省首例被执行注射死亡的贪官。他坐在椅子上想,仅就这一点,自己是幸运的,起码比有些贪官幸运,自己贪了两千多万,执行的是注射死,而有些贪官只贪了几十万、几百万,却被枪崩了,法律真他妈的不公平。想到这儿,他越发平静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了,任凭自己尽情地发挥想象,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唉了一声,这是他行刑前最悲哀的表现,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在官场心不由己是错误的,其实人在官场命不由己呀!
昨夜妻子来看自己,他在妻儿面前长跪不起,儿子看见父亲带着脚镣穿着囚衣吓呆了,妻子和儿子也跪在他面前,还给他磕了头,哭嚎声泣鬼神惊天地,他内心感叹人之将死啊!他没有哭,他在看守所里考虑了两年多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只能叫负隅顽抗。这两年多来,他害了太多的亲友。与妻子生离死别后,妻子的下半生就要在牢狱中度过了,儿子怎么办?想到儿子,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不是哭,而是嚎,那种山野中野狼般的悲嚎……
烟头儿快烧到手了,他舍不得扔掉,他恨不得让烈火烧掉自己,毁灭是一种快感。火烧云越来越红了,他却有一种深深坠入黑洞的感觉,自己是黑洞的制造者,现在却要坠入深深的黑洞,这是多么可怕的归宿。
“时间到了!”行刑者说。
他浑身开始冰冷,脚镣沉重得抬不起脚,蓝色的囚衣箍在身上,仿佛束缚了灵魂。他还能感觉到是几个人把他架到行刑室的。
行刑室是一间单独的隔离室,室内有一张床。法医让他躺下来,结果他动作僵硬,腿弯不下来。
“别紧张,你身体怎么这么硬?”法医冷漠地说。
“我不紧张。”他答道。
“我先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法医又冷漠地说。
他没有回答。
镇静剂顺着血液流遍全身,他进入半梦半醒状态,紧接着法医用胶管帮他扎起左臂,向其静脉注入药物。三十五秒,他彻底睡去了,他的灵魂坠入了深深的黑洞……
这分明是在写贾朝轩被判死刑执行注射死的过程,丁能通惊叹于顾怀远的胆量,看来这小子是想开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辞职后反倒洒脱了。
丁能通接着往下读:
张国昌死后不久,李国藩也死了,他是死于肝癌。李国藩死的那天,天下起了小雨,私下里还去了一些领导为他送行,尽管他被判了死缓,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人说,害人先害己,李国藩遭了报应。有人说张国昌不去澳门豪赌谁也害不了他。我看着他们争斗了两年多,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两败俱死。
我一直试图总结点经验教训,在致命的漩涡中如何才能自拔,最后我发现秘书不过是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连哭都是无人察觉的,因为鱼在水里,即使哭也是无人能看到的。但是生活是水,水终于发现了鱼的眼泪。因为鱼不仅在水的心里,而且眼泪是咸的,水是淡的,眼泪增加了水的咸度。其实领导也是鱼,只不过比秘书这条小鱼大一些,是鱼就难免被卷入致命的漩涡。
我给张国昌做了两年的秘书,我发现秘书必须深谙政治的游戏规则,才能回避弄权的风险。不过,秘书与领导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秘书很难摆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窘境。
12、心灵庄园(5)
有人说我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庆幸自己牺牲了,当然,这种牺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用沉默和反思自我疗伤。人有多坚强就有多脆弱,这种脆弱让我看清了自己,人们很少看自己,只顾看别人,这是我痛苦的收获。我本来还想继续在办公厅干的,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官本位、学本位、还是商本位,最终都是人本位。人是群居的,人永远不会群而不党,我辞职了。我不想再成为市长秘书,那种听领导念自己写的材料,还得扮认真状做笔记的小人物,无聊透顶。当然,做出这种抉择是痛苦的。这其实是一个心境炼狱的过程。
过去,张国昌任东州市常务副市长时,经常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听起来我像是他的私人财产。现在我才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谁的人也不是。这个认识越来越透彻,能有这种认识得益于我一直是一个精神上独立的人,我懂得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我还有许多新的生路,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在《伤逝》中的一段话: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
我其实已经跨出了第一步,跨出这一步时是清醒的。“但是,这却更空虚于新的生路,现在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那一步。”
张国昌的注射死是在春天进行的,李国藩的死也是在春天,死神选择春天接纳他们,大概是希望他们的灵魂再生。灵魂真的能再生吗?……”
很显然,这里的张国昌就是贾朝轩,而李国藩就是肖鸿林,丁能通几乎一夜没合眼,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他掩卷长叹,看来顾怀远要重新选择另一种人生了。顾怀远虽然另类,但果然能成为一代文豪也不枉此生。想到这儿,丁能通心中生出几分羡慕之情,他连打几个哈欠,望了一眼窗外,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
13、盗矿(1)
就在丁能通酣畅淋漓地阅读顾怀远的长篇小说之时,十几个黑影扛着镐拎着锹,趁着夜色潜入了矿山,很显然,这十几个人对矿山的路线熟得很,即使没有灯光,他们也轻车熟路地摸到了早已被铁丝网封闭的坑口处。
他们撕开铁丝网跳下去,沿着一段三十多米的轨道来到第二道门,然后又扭断第二道门上的锁头。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说:“你们进去尽管挖,我和小六子在上面给你们放风,狗日的罗虎不给我们工资,我们天天晚上来挖。”
进入巷道的十几个人中有人回应:“大哥,你就瞧好吧!”
眼看着十几个人沿着巷道看不见了,大汉和小六子回到了坑口。
“来,小六子,抽根烟。” 大汉瓮声瓮气地说。
小六子赶紧给大汉点上火,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四处张望,山风吹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掩了掩衣襟。
“大哥,咱们得挖多少天才能卖出咱大半年的辛苦钱?” 小六子问。
大汉无所谓地说:“管他呢,小六子,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连市长的条子都不好使,咱只好自己动手了,我也想开了,只要咱们弟兄们心齐,够胆量,不怕不发财!”
小六子高兴地说:“大哥,要是真有了钱,你得帮我说上个媳妇!”
“没出息,娶什么媳妇,有了钱,城里的小姐都是你的。”
大汉把手中的烟头往地上一扔,然后踏上大脚,咬牙切齿地蹍了一脚。
早晨,群山环绕的前插镇掩映在一片雾霭之中,房舍古朴清朗,静谧幽深,早起的人们不紧不慢地走过街口,一份超然和闲适的心态跃然眼前。
昨夜罗小梅没睡好,早晨起来左眼皮一直在跳,老话讲,男左女右,女人左眼皮跳可不是什么好事,她惦记着昨晚喝多了的丁能通,一大早就开着驶进前插宾馆大院。她想陪丁能通吃完早餐,领他去矿山看看。
罗小梅敲门时,丁能通还在酣睡,正梦见远在加拿大的妻子衣雪挎着薪泽银的胳膊逛街,丁能通气坏了,要上前理论,可怎么也拔不动腿,眼看着衣雪与薪泽银有说有笑地进了一家咖啡馆,他想喊,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正在呻吟之际,被门铃声惊醒,他猛然坐起身,头上渗出些许细汗。
“谁呀?等等!” 丁能通睡眼惺忪地喊道。
怪梦让丁能通有些不祥之感。
“通哥,我是小梅!该起床了。”
丁能通赶紧穿好衣服开门说:“小梅,你先坐,我洗把脸。”
丁能通说完,走进洗手间。
罗小梅从床头拿起顾怀远的长篇小说《心灵庄园》,随便翻着问:“通哥,你好像把这本小说看完了?”
丁能通从洗手间走出来,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说:“昨天晚上酒醒后,看了一宿,天快亮才睡。”
“写得怎么样?”罗小梅妩媚地问。
“写得挺灵魂的,说不定顾怀远因祸得福,将来会成为大作家。”
“既然你看完了,我拿回去看看。”
“不过,看完替我还给张铁男。”
两个人正说着话,罗小梅的手机响了。“罗虎,一大早打电话有什么事?”罗小梅不耐烦地问。
“姐,不好了,出事了!”
“瞧你慌慌张张的,死人了?”
“可不是死人了!昨晚有人盗矿被毒死了!”
罗小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没想到自己的矿区居然有人敢盗矿,而且命丧矿井。
罗小梅挂断电话有些紧张地说:“通哥,你自己吃早餐吧,矿上出了点事,我得赶过去。”
丁能通从罗小梅断断续续的谈话中听出了些许端倪,他关切地问:“怎么矿上死人了?”
“具体怎么回事我还不太清楚,我得赶紧赶过去。”
13、盗矿(2)
“小梅,我和你一块去。”
丁能通毫不犹豫地说完,拿起外套就走。
路上,罗小梅一边开车一边与张铁男、牛禄山、黄跃文等人通了电话,然后,油门踩到底,奔驰车飞速向矿山驶去。
赶到天沟乡矿山时,罗虎带着几个人正等在山下。
“张书记、牛县长到了吗?”罗小梅下车就问。
“还没有,县公安局黄局长到了,在六号坑口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罗小梅厉声问道。
“前些日子领头闹事的魏国山,是这次盗矿的组织者。”
“人呢?”
“已经跑了。”
“谁发现的?”
“是一个叫魏小六子的盗矿分子报的案。姐,这位是谁?”
“是驻京办的丁主任。”
“你好!丁主任,经常听我姐说起你。”
丁能通客气地与罗虎握了握手。
这时,县委书记张铁男和县长牛禄山的车也赶到了,张铁男一下车就对丁能通说:“能通,实在对不起,本来想让小梅好好陪你转一转,没想到遇上这种事。”
“铁男,到底死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