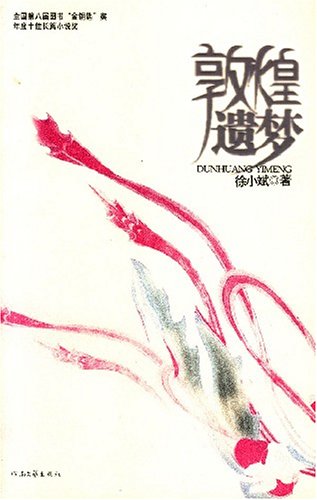敦煌遗梦-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天星星对张恕说:“其实我想成佛也未必有什么难。释迦牟尼不过是坐在菩提树下入禅定,有人说坐了七天,有人说是四十九天,究竟坐多少天我不管它,反正在成佛的那一夜是初夜得‘宿命通’,知善恶;中夜得‘天眼通’,知宇宙;后夜得‘漏尽通,,知生死;这种’禅定‘不就是现代气功么?气功不也有什么’开天眼‘,’开慧眼‘一说么?只不过现代人少了释迦的那种德行,虽有外部修持也难以成佛罢了。”
“你总有那么多奇思异想,”张恕笑一笑,“把这些都记下来吧。”
“而且,我发现凡是这类伟大少物的出生都是奇特的。耶稣是处女所生,释迦牟尼呢,干脆就是摩耶夫人从右胁下生出来的,照我看,大概这些人从小缺乏母爱,先天不足,不然不会在成年之后对异性有那么多的偏见和仇视。”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成为创立教派的一代宗师。”“但是我觉得耶稣·基督无论在智慧上还是在道德上都不能和释迦牟尼相提并论,甚至也远远不如我们的孔子、老子什么的。”张恕和星星坐在招待所后院的石凳上,当时正是下午四点,日照仍然强烈,有一片绿荫罩在他们的头顶上,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无哗远远地走过来。
“你的画像完成了?”无晔向张恕礼节性地笑笑,然后迅速转向星星。
“没有,今天休息。”星星把旅游帽从旁边的石凳上拿起来,但无晔并没坐,他靠在树干上。
“星星正在发表耶稣不如释迦牟尼的宏论。”张恕笑了笑。
“你真的这么认为?”无晔总是昏昏欲睡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不光是我。有很多伟大人物,包括罗素、尼采什么的,都这么认为。”
“谁这么认为,谁就错了。大错特错。”无哗的语调似乎很激愤。
“请问错在哪儿?”
“耶稣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些人,他不但是哲人,智者,还是个真正的社会改革家,你好好读读新约,就知道你们错在哪儿了!”
“我不但读过新约,旧约也读过。”星星立即反唇相讥,“不读还好。读完之后上帝的那点神圣感立刻化为乌有。基督教堂说什么‘神爱世人’,其实上帝的爱决不是无条件的,首先世人得爱他,得成为他的忠实奴仆、替罪羔羊,上帝才可能爱世人,而且这种爱还伴随着那么多残酷的考验,譬如说《约伯记》里那位虔诚地信奉上帝的约伯,仅仅因为上帝闲着没事和撒旦打赌,一下子就让约伯倾家荡产,并且杀死了他十个儿女,还让他患了麻风病,这种‘考验’也太可怕了吧?”
“可是后来耶和华赐约伯的比先前更多包括家产和儿女。”这简直是为了显示他的权威,拿人的尊严耍着玩儿!怎么补偿?财产不说它,死去的儿女能补偿么?!再说,这种‘赐’能和‘爱’相提并论么?所以说,耶和华爱世人分明是假的,不管惩罚还是恩赐,都是为了强调他是‘万能之主“这种身份罢了!佛教就不同佛教起码比基督教要真实得多。尼采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起码释迦牟尼确有其人,而上帝完全是被人造出来的!”
“怎么能这样说呢?”无哗的脸竟涨得通红,这是他头一次反驳星星,而且可以判断他那结结巴巴的论调完全是出自他的内心,“……上帝怎么是被人造出来的呢?上帝是存在的,托马斯·阿奎那已经证明了。第一,已知世界一切都在运动。而每一运动都由另一力量来推动,如此无穷,那……那么第一个推动者就是上帝;第二,世界上每件事都是结果同时又是原因,那……那么最早的原因是上帝;第三,世界上一切都具……具有相对性,为什么能有这种比较,是因为有绝……绝对的真善美存在,这……这就是上帝……”
“第四,偶然的存在不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必然的存在倒是不可思议的,”张恕竟然接着背了下去,无哗和星星都惊奇地望着他,“凡是事实都是偶然的,偶然性事实依赖于偶然性小一点、必然性大一点的事实,最早的必然就叫做上帝;第五,世界是一个奇妙的大机器很多东西都像天造地设一般相适应,不能不设想这是由高级的智慧和理性创造的——一这就叫做上帝。是这样么?”“是……是,是这样……”无哗得救了似的望着张恕,“其……其实很多现代科学的奠基人都是教……教士或神父,布……布鲁诺和罗杰尔·培根都是神父,帕斯卡是伟大的数学家也是虔……虔诚的教徒……可……可以说文艺复兴时代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基督徒……”
“那又怎么样?”星星拎起旅游帽猛烈地扇,“那又能说明什么?跟你说,真正与现代科学相通的是佛教,举个小小的例子,比如现代物理学中的‘真空’,包含着无数粒子,粒子不停地产生和淹没这很像佛教里的‘空’,这是粒子世界的所有形式但不是独立的物理实在,而是‘空’的瞬时表现,就像佛经所说:‘色即空,空即色’,‘知太虚即气,则无无’……”
“这……这太牵强附会……”
“你们这样吵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张恕慢吞吞地说,“你们俩的根本分歧,无非一个欣赏极权宗教,一个欣赏人文宗教,所谓极权宗教,就是承认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主宰着世界,人类对这种力量必须崇拜和敬畏,神全知全能,人则卑微渺小;人文宗教则强调人的力量,人要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应当去实现理想而不是盲从,人要去发挥力量而不是无能……我理解得对么?”
“我从……从来不欣赏什么极权宗教,而且我也不相信基督教是什么极权宗教,耶稣·基督本身就来……来自平民,他一直和最底层的百姓在一起,为他们治病,排……排忧解难……假……假如说旧约确实有一点‘极权’味道的话,那……那么新约里说:‘爱你们的仇敌’,又怎么解释呢?!难……难道耶稣·基督的血还……还不如释迦牟尼喝的鹿……鹿奶珍贵么?……”
在无哗说这番话的时候,张恕和星星的心里同时划过一个猜测:“他是基督徒!大概是的!”
“看来无晔是信奉基督教的。星星呢,虔诚地信仰佛教。”张恕懒洋洋地说。他想起今晚和陈清的约会,急于结束这番谈话了。“我根本不信仰什么佛教。”没想到星星和无哗一样执拗,没完没了地不愿下台阶,“再美好的信仰一旦变成了一种宗教,就肯定有它黑暗和丑恶的一面,我觉得可以把宗教看作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成为人类的一种自欺方式。这没什么不好。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只需要‘欺人’就行了,人可不行,除了‘欺人’之外还需要‘自欺’,于是就有了什么信仰、理想之类的玩艺儿,这说法你们同意么?”
张恕和无哗好像都打了个寒噤。
玉儿来了。在灰色的宗教理论争论中出现了一株明丽夺人的造物之花。
“这才是绝对的真善美的存在,上帝算什么?”星星得意洋洋地瞟了无晔一眼。
“你……你的结论未免太早了吧?”无晔也立即回敬了一眼。只是自这次始,星星才发现无晔心里着急的时候嘴上便要结巴,而且越是想说清的事便越说不清。这点可和晓军不一样。她想。
第三章 “俄那钵底”(07)
张恕和星星都猜错了。无晔一家都是基督徒,唯独他不是。但无晔信奉一种“基督精神”。在这点上,他的本性好像和一般男人相反。他乐于馈赠,给予,假若碰到他喜欢的人,他简直连自己的血肉也不吝惜。他的家庭其实是古老的望族。他的那个家族在江南一带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只要一提江南向家,没有人不知道的。向家出息了很多人。当政府官员的总共不到十人便有四人做到部长以上,从商的有三人已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大亨,搞自然科学和学医的更是人人出类拔萃,只是没有搞文学艺术的一一这是向家的缺憾。无哗觉得整个家族中没出息的只他一个。小时候他曾大逆不道地想学画画,结果遭到族中长辈们的一致反对,他只好放弃了。学医本不是他的心愿,除了气质不适合做医生之外,他还有自己的秘密考虑:他认为学医的女同学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认为她们像一群穿白大褂的木乃伊。或者,像“甲醇”——“假纯”的谐音。
不知为什么,他不喜欢同龄或比他小的女孩。他觉得这些女孩都像风一般轻得没什么分量,又像一堆廉价的、闪闪发光的装饰品,貌似漂亮,实则毫无价值。他应该是学美术的,他的审美趣味实在是比一般男人高上好几个等级。和一张美女的脸相比,他宁愿喜欢一张有特点的、无矫饰的脸。当他见到肖星星的时候,他被她那种生气勃勃的美给吸引住了。后来,他又发现了她的聪慧和达观。那一天,他给她扎针的时候,他注意到她身上那细如乳脂的雪白的皮肤和那被胸罩遮掩着的浑圆饱满的双乳,他的心一直在战栗着。后来他观察了她的手纹,发现她内部脏器是难以置信地年轻。他对她说了,以为她会大惊小怪,谁知她却很平淡地说,三危的住持大叶吉斯已经为她算过命了。
无哗摸不透她对于他的想法,只是发现,玩的时候她更愿意和他在一起,而聊天的时候则愿意找张恕。
“我发现你挺会照顾人的。”她说。
他想说:“我可不是什么人都愿意照顾的。”但是什么也没说。
第三章 “俄那钵底”(08)
星星做梦也想不到,玉儿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做她的肖像模特儿,完全是为了张恕。在那个神秘的鸣沙山之夜,玉儿一见到张恕便很中意。在那之后的几天里,她一直想去三危山招待所找他。玉儿早已不是处女。第一个和她好的是个卖黄面的后生,时间最长。后来又接二连三和男人有过一些交往,但都不中意。她没什么文化,人却极精明。她觉得像张恕那样的男人和其他男人不同。她第一不能急,第二也不能错过机会。因此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她立刻跟上了命运之神的脚步一一她知道肖星星就住在张恕隔壁。
果然,在星星这里她见了张恕几回,回回都向他投去深情的目光。无奈那张恕好像根本不解人意。他和肖星星谈的那些稀奇占怪的话题,她又根本插不上嘴。她觉得他们真是些奇怪的人。但恰恰是这种怪更增加了他的吸引力。她几乎每天换装,美丽的衣裳和首饰更加烘托出美丽的人儿。但她感觉到只要往那固定的位子上一坐,她这美丽的人儿便被并不美丽的肖星星的光辉笼罩了,像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动弹不得。
那天若不是星星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与无晔同去榆林窟的话,玉儿也许真会丧失与张恕的那一段缘分了。
那天张恕也回来得很晚,回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照例看一下那幅尉迟乙僧的真迹。关于吉祥天女其人,他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他已经开始觉得乏味,正在考虑要离开此地。
但是他没有拿到那幅画——藏画的地方是空的。他大惊失色,急忙又细细地找了一遍,如此三番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他呆坐窗前,看着星星在夜幕中慢慢沉落,最后就那么黑着灯,连脚也不洗便钻进被窝——这时他忽然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