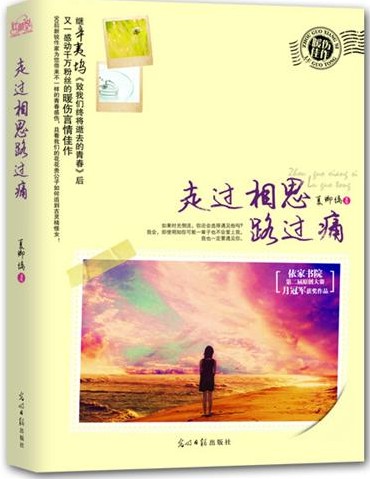走过西藏-第9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只在桑秋多吉和仁增曲珍这对老夫妇那里看到了那种超稳定心态。那是把自身完全融入至高、无限和永恒之中的人才拥有的宁静与欢悦,出于完全的依赖而拥有的安全感和归宿感。正如他们只用灵魂歌唱一样,他们甚至是以一种喜不自禁的心情来面对他们眼下艰辛粗糙的生活。我甚至相信,矛盾在他们那里消失了,世界经过他们观念的重组和谐单纯了。今生单纯了。一切为一。
我看到的是一个结局吗?
所以我与孙亮合计,在最近的几年里,一定要创造条件去罗布桑布的家乡,那个偏僻的山沟一趟,当然是带着摄像机去。看看罗布桑布,他的年轻的伙伴们的信仰和生活。无论他们改变了还是更加坚定了,都有意味。
最好是不要让感慨妨碍了叙述。让我们仍然返回主题,跟随着他们行进在朝圣之路上。
无论一生中有过多少祈愿,此行都将一次性地给以了结。就为了一个好于今生的来世,沧桑一世的老夫妻把家中十多头牦牛、五十多只山绵羊寄养在亲戚家,请一尼姑照看家室,就这样风霜雨雪地前往心目中的圣地。桑秋多吉每天都在为宇宙众生灵祈祷,每天都在祝福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们万寿无疆。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完成着磕头的每一程序,额头硬茧每天都被蹭出新鲜的血。在他每天的强调提醒下,年轻的僧尼们严格遵守规范,在无人监督的场合,磕头也从不取巧。
这种磕法名叫三步一身,意指走三步磕一个等身长头。以往我和一些作家都曾介绍过具体磕法,怎样合掌于胸前,怎样举至鼻尖、额头,前扑,五体投地,等等,但却没有人认真地介绍过磕头朝圣的规矩。这一次我才了解到并亲眼看见了磕头的讲究。每天自上路起,只准念经,不能讲话,遇到非讲不可的时候,要先念经以求宽恕。途中遇河,要目测河距,涉水而过后补磕。下山时因有惯性,也不能占便宜,下了山要补磕相应距离。在雪深过膝的色杂波拉雪山,实在无法磕头,就拿绳子丈量过,到拉萨后,每人补磕了四千八百个头。严守规矩使他们一路受到称赞。这使他们引以为自豪。当他们在协拉山一带遇到另一群朝圣的人,见他们每磕一头抬腿走上十多步时,就觉得那些人心不诚。这件事他们说了几次,每说起就老大不高兴,因为这有关磕头朝圣总体行为的名誉问题。
每天的磕头有一定程序。早饭后步行到昨晚做了记号的地方,站一横排,合掌齐诵祈祷经。傍晚结束时,要向东南西北四方磕头,意即拜见此地诸神灵,今晚我将暂栖于此,请求保护;向来的方向磕三个头,答谢一路诸神灵与万物,为我所提供的生活必需水与火;向前方再磕三个头,告示我明天将要打扰的地方神;最后向前方唯唯鞠躬三次,不尽的感激与祝福尽在其中。但结束时的向四方磕头的仪式,我们只见到桑秋多吉一个人始终坚持着。
等我们熟悉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这群年轻人中有趣的事。例如,小个子僧人多丹是个食肉类,不吃肉就迈不动步。有一回遇到意外之喜:猎人射杀了公鹿,取了鹿茸就走了。多丹背回了冻硬的死鹿回营地美餐了几顿。但有一回,他差一点儿成了狗熊的美餐。在一条山沟里,他突然撞上了一头狗熊,掉头便跑,狗熊紧追不舍。多丹急中生智,藏身于石缝,笨蛋狗熊居然没能发现他。我们还知道了胖尼姑不雅的外号叫“猪八戒”;还知道昌都人西热邦久得了奇怪的眼病,凡是他看准了的放脚的水中石头,一脚下去必定踩进水里。还有从小在家乡长大的外甥,到拉萨不认妈妈了,总是随了舅舅罗布桑布喊妈妈为“姐姐”。
当然,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更多。
尤其是,我曾一次再次地想过,这十多位二十几岁的僧尼,日复一日地朝夕相处,能不产生一些感情方面的纠葛?如果有过,是对戒行的破坏;没有,则是人性某些方面的缺失。
我们的拍摄计划安排得很满,又增添了朝圣部落这个计划外内容,格外的疲于奔命,愈加频繁地穿行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两岸。而无论我们留了多么宽松的余地按每天前进一两公里计算,他们也总是拖了又拖。江羊文色去山里走亲戚去了,还邀上嘎玛西珠同去,大家只好等他俩,一等四五天;仁钦罗布病重了,一群人送往拉萨急救,大家又都等着。总之每回去营地,都不免抱怨唠叨,你们的速度可真慢呵,你们的纪律真松弛呵,不,你们简直就没什么纪律;你看我们已在山南又拍过些什么,在拉萨又做了些什么。冬天来临了,你们的朝圣和我们的拍摄都该结束了,咳,你们怎么不着急呢?
罗布桑布真的不着急,他们没有一个人着急,我的藏族朋友们都不会着急。我的亲爱的嘉措和德珍两夫妇永远都是好脾气。这是一个不着急的民族。有人提醒过说,你看见过哪个藏族人因为着急打过孩子呢?
要是你相信一大劫是十三亿年,一个灵魂无穷尽地转世需历经无穷尽的这样的大劫,如果你拥有无穷尽的时间,你着急着干吗去呢?
当我着起急来的时候,罗布桑布就笑着解释说,人多事多病多。
现在我想起来还不免好笑。我们就仿佛一个著名的故事中的人物一样。
桑秋多吉说,早晨起来到山上捡牛粪,够烧一天的就行。故事中的那位自我实现者得到海滩上晒太阳的外国渔夫的同样答复:昨天多捞了一条鱼,够今天吃的就行了。自我实现者对这种懒散惰性很不赞同,就说我拥有这些时间的话,就绝不荒废它,就如何地多打鱼,敛财聚富,如何建立合资企业,跨国集团,进行远洋贸易,发行股票,如何在几十年里成为世界首富之一。
然后呢?
然后,自我实现者就说,当我功成名就后,我就皈依佛门,或者到海滩上来晒太阳。
桑秋多吉和外国渔夫睿智地微笑了。
一年一月零三天,算一算,整整三百九十九个昼夜,把沿途每天所做所为简要成一句话记在长条的藏历上。罗布桑布心平气和地翻阅,慢条斯理地讲解。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不过就记了今天到了何处,见过何人,遇到何事,某人病了,某牛死了或卖了之类琐屑事务。我们就这样领略到他们所经历过的云和月,风和霜,雨雪和阳光,一条长长的、穿越了岁月和荒野的足迹——是身迹,和心迹。
一九九一年藏历十月初四、公历十一月十日,出发。
两天后到达囊谦古国遗址,文成公主玛尼石处。
十二月四日,嘎玛洛萨病危,尼姑们都哭了。为他念经并打针。嘎玛洛萨右肋下剧痛。当时所有磕头人都两肋剧痛。估计不是肌肉严重拉伤,就是内脏错位。
一九九二年元月一日,翻越青海与西藏交界的色杂波拉雪山。雪深无法磕头,只得膛雪而过。翻过山,已是深夜。找到当地百姓,请求牛粪和住宿。人家说,过往香客有好人也有坏人,坏人又偷又抢,我不知你们是好是坏!说着骂着,还是给了些牛粪。用牛粪火慢慢烘烤双手,才把冻住的手板套脱下。
一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化缘(讨饭)。
一月二十四日,第二次化缘。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心爱的小青马掉进冰河里去了。但没受伤。后来用这匹马换了一匹红马,红马的主人看上了家乡的良种马,宁可贴四百五十元钱央求着成了交。此后的记载中,多有换马、卖牛之类内容,有时赚了,有时亏了。
一月二十八日到达了青县农村,住父亲舅舅的儿子家。次日为主人家念经。由于挽留殷切,一住十二天。
二月九日启程,路遇囊谦朝圣者七人。后同行一月,分手。
二月二十日路遇四川八人磕头,不是三步一磕而是走十多步一磕。
三月一日,磕到了青境内大雪山协拉山顶。
三月三日,尼姑才仁、英索的牛失足掉进协拉山雪窟中。因牦牛体格硕大,无法将它拖出。直到三月五日藏历年这一天,四川朝圣八人到达,央求这群汉子帮助,把已冻残了腿脚的牦牛半抬半拉地拖下山。四川人说,磕十天头也没这样累呵!意思是想向我们讨些吃的,我们没有。随后的几天是为安置这头残牛而奔波:到附近村庄乞讨饲草,找汽车把牛运到道班,委托道班班长照料残废了的牛。行前,将讨来的十五麻袋饲草都堆放在瘫卧的牛身边——生死由之。为此,才仁英索母女伤心欲绝。因为她们认为这头注定要死的牛是为她们而死的。
另一头牦牛死得更惨。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那一晚,表姐次珍玉珍的牦牛独自离开了牛群。人们四处寻找,第三天才在一条水沟旁找到了它。它已奄奄一息。人们看到它似乎在哭,并发现它尾巴之下豁然洞开,黑黢黢有如一口山洞,内中狼藉。原来是卑鄙残忍的豺狗从肛门钻了进去将牛的肠子吞吃一空。根据一路血迹分析,那牛独自离开人群和牛群后,就失去了保护。当它疼痛难忍时为时已晚。它漫山狂奔也甩不掉吸盘一样粘在后尾的可憎的魔鬼,直到它逃进水沟,或许是那豺狗饱餐后自动离开。那庞然大物受尽了磨难直到第三天才咽气。表姐痛不欲生。全体僧尼为死去的牛作了超度仪式。
六月六日,昌都四姐弟赶到。
六月九日,九头牛中的七头病了。等待了十六天后才痊愈。
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二十五日,从嘉黎步行往返于墨竹工卡,参加“直鲁噶举”仪式。后将仅剩的五头牛寄放于嘉黎百姓家。
九月十日,在嘉黎境内丢失五匹马,多丹寻马被狗熊追赶。
十月十五日,朝拜直贡堤寺。丢失六匹马。
十月十六日,没找到马,碰到电视(摄制组)。
在随后的记录中,频频出现“电视”字样。也频频提示仁钦罗布病倒、病重、急送拉萨医院抢救等情况。接近拉萨的最后几十公里,是多事之旅,断断续续行进了一个月,仁钦罗布佝偻着日趋瘦小的身子,险些一命归西。久患肠胃病,加之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我们摄制组的车也多番往返于医院和营地之间。在朝拜过大昭寺后,仁钦罗布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曾想过就这样死去了,能带走人世间的全部苦难该有多好!
按照一个说法,谁要是死在了朝圣路上,不是不幸而是有幸。人们会说,他是死在朝圣路上的呀!
英索也是。二十六岁的尼姑英索几个月来低烧不退,总是跟不上磕头的伙伴们,只能早出晚归,形单影只地匍匐在青黑的沥青路面上。常常是很久很久了还没有爬起来。她已经到了极限。
幸好,拉萨在望了。
在拉萨以东几十公里外的达孜县境内就可以隐约望见坐落在拉萨市中心红山上的布达拉宫。藏族人说,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当他第一眼望见布达拉宫的金顶时,如果金顶有光芒闪耀,那他就有福了。我不知道神明是否慷慨过一回。
终于,罗布桑布记下了旅程的最后一笔——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藏历十月十五日,朝圣大昭寺。
藏历十月十五日,是隆重的宗教吉日。为等待这一吉日,他们在东郊的二姐家休整了几天,补磕了差不多一年前翻越色杂波拉雪山时欠下的四千八百个等身长头。还做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