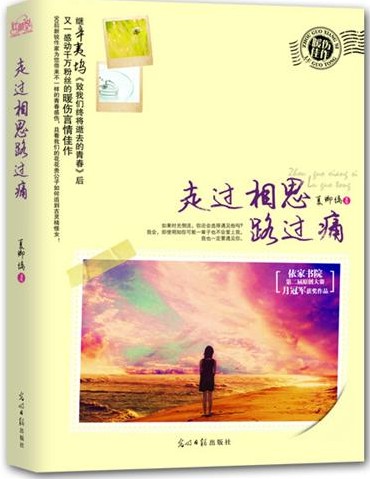走过西藏-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次我在成都——拉萨的民航班机上,碰巧与一位水电专家邻座,他对那曲的困境很了解,他认为那曲的地热和水能都大有可为,不幸却陷入了通常可见的恶性循环:因为贫困,拿不出资金来开发能源,而正因能源不能被利用,才造成贫困。
多年以前我就常往返于拉萨与那曲之间,自从一九八四年以来越发频繁。那曲成为我精神的伊甸园,现实生活中的乌托邦。在这里结识了一大群优秀的人。无论物质生活多么贫乏,还要买菜。做饭,但我在那曲期间工作效率是高的,日子过得快快活活。
一九八四年二月间的那场大风刮了一周还多,让我永远、永远记住了那曲风。飓风呼啸中还夹杂着喊里咔嚓的铁皮屋顶的惨叫——一幢幢房子给揭了盖,白亮的铁皮成了一张绢纸。平时用粗铁丝捆着巨石坠在房前屋后成为那曲一项景观,如今也失败在骤烈的风中。人们日复一日地被迫关在房子里,一切工作和交往都停止了。我当时住在老群艺馆。根据飓风日出而作,日入即息的特点,我稍稍控制了饮水,练就一整天不上厕所的本领。和藏北文学音乐美术界人士的嘉措、双焰、发斌、黄绵瑾几位男士们海阔天空地胡聊。到晚上风停时,地区文工团团长多吉才旦他们就来了,一伙人吹拉弹唱,把所会的歌统统唱过一遍,从《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到《喀秋莎》,忘乎所以地娱乐一番。
后来在东南方的沼泽地上新建起文化局大院,又盖起新的群艺馆,就是由成都的青年建筑设计师刘家琨创作的“鹤立鸡群”的那一座。老群艺馆被遗弃在路旁,冷冷清清,只有我记住了那一段风暴中的难得的快乐时光。
藏北的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既坚强、又细心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的男子汉。我认识的这群人似乎无所不能。大至搞某项事业,设计盖房,管基建,小至修理拉链、锁、电筒和打火机,同时人人都是烹调家,美食家。
在那曲工作的汉族干部中,李彬是藏化了的最典型的例子。四十七岁的李彬是胖胖的大块头,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宽厚耐心得像个老牧民。他在索县乡间生活了多年,藏语娴熟。在那曲市场上,牧民出售牦牛蹄子两毛钱一个,李彬用流利的藏话聊上一会儿,就可以降价到五分。牧民最喜欢讲藏话的汉人,更何况他的藏语如此地道。他的生活用品和习惯一概是藏式的,亲手做了藏柜,又漆画成藏式图案,鲜艳夺目。据说休假回上海大都市的家时,还需背上一袋糌粑。多年来他搜集了数量可观的藏北民歌、民间故事、格萨尔轶事及谜语。最近他已整理出版《西藏谜语》一千条,藏汉文对照,很精彩——
草坪上一头母牛,
百条绳子拴住它,
嘴里吃人肚里说话。
(打一用物)
十五圆月臀上挂,
六谷麦穗胸前插。
(打一动物)
五个人力量大,
抓住两个灰兔子甩地下。
(打一动作)
下面是海子,
上面是雪峰,
峰上飞来五只鹰。
(打一动作)
怎么样,猜不出来吧?藏族谜语非常形象化,但对藏族生活不太熟悉的人是难以猜中的。以上四个谜底依次为:帐篷、黄羊、擤鼻涕、抓糌粑。
去年初夏,若曦一行数位美籍华人作家来访西藏,取道青藏线。我专程来那曲镇守候并安排参观事宜。自然想到应该向国外来宾展示藏北最土风的歌舞,由此又自然想到应该去请教藏北老艺人叶甸。更何况此前若曦女士来信要求我为她录制一盘藏北民歌的磁带。
叶甸五十九岁了,形容精瘦,动作迅捷,门牙脱落,声音沙哑,现在那曲地区群艺馆供职。当我在他家的大大的庭院里找到他,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格拉(先生),把你的歌声带到美国去怎么样?叶甸诺诺连声,干枯的脸笑成一朵菊花。
几天后叶甸拿来了录好的磁带,赶紧试放了一下,可那歌声和乐器伴奏都是干涩嘶哑的。叶甸自豪而不无遗憾地说,少年叶甸和青年叶甸是藏北有名的歌手,歌喉清亮悠扬,舞姿优美奔放。叶甸的家是歌舞世家,祖上原籍是著名的巴塘弦子的故乡巴塘。叶甸那位有出息的哥哥在北京,已任国家民族歌舞团副团长多年。
嗜酒毁坏了众多的歌喉,据说这是藏族男歌星之所以罕见的缘故。叶甸也是。大约二十几岁时坏了嗓。但他的牛角胡还是响着,他的舞步还是跳着,他仍是藏北数十万平方公里上的有名的艺人。
叶甸口述歌词大意:
夏天五六月的时候
草原上开满美丽的花朵
冬天十一二月的时候
花儿和草原就要分别
请不要为我们的分别难过吧
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
“这是送别朋友的歌,巴塘弦子,”叶甸说。我迷惑地“唔”了一声。
绸子缎子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俩去拉萨街上转一圈儿
丝线棉线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俩去康定城里转一圈儿
海棠桃子李子你喜欢的话
我俩去怒江边上转一圈儿
大葱大蒜韭菜你喜欢的话
我俩去菜地里面转一圈儿
“这叫《热穷阿尼》—一两个小热巴(艺人),是昌都民歌。”叶甸说。我越发疑惑。后面几首分别是云南藏区民歌,巴塘东区民歌等等。
有没有藏北牧区民歌,地道的土风牧歌呢?
叶甸的磁带里一首也没有。当今藏北歌舞最活跃的地段是边缘的半农半牧区。在东部的索县和嘉黎,人们声称他们的歌舞来自昌都;而西南侧的文部等地,人们则说他们的歌舞来自日喀则。在藏北腹地班戈县纯牧区,据称是地道的牧民舞,腿脚上的功夫果然很棒。只是歌词为“文革”遗风,大都语录之类,老歌词青年牧人无从知晓。而在草原深处,传统歌舞近乎绝迹,有的只是大大简化了动作,唯有围成一圈,缓缓地一举手一投足而已。在海拔接近六千米的牧场,牧人干脆答复说,他们既不唱歌也不跳舞。重要的问题在于呼吸,他们全力以赴于基本生存。在高度分散和封闭的高海拔牧区,文化几乎消失。安多县北部牧区的牧人,每年在冬季历时数十天往返于多玛区所在地一次,出卖毛皮等畜产品,换回茶叶和白糖。
我一般地认为,民歌大抵是生活的镜子,当生存方式凝固时也必然趋向凝固化,因而民歌不可免地具有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又由于群体的人生观的缘故,难以向人生深处开掘。由此大约可以解释众多民族民间的歌舞何以行之不远,何以不及迪斯科、摇滚乐等可以风行世界。
但是藏族民歌时常记述历史典故。叶甸讲解《加嘎喇嘛》的歌词和故事。
山阴处有一百匹马聚在一起
可惜百匹马中只有一匹马驹
而且马驹很快要离开马群了
小马呀请你不必为离别难过
我送金鞍子伴你去远行千里
“加嘎”是汉人之意。巴塘地方有座卓瓦寺,百多年前寺庙活佛是汉人,人称“加嘎喇嘛”。因他年少又是外族人,卓瓦寺的百多位僧人不信服他,加嘎喇嘛忍无可忍,便打定一个主意。这一天他召集起全寺僧众唱了这首自编的歌。僧人们不解其意,待到第二天这位少年喇嘛携带寺宝不辞而别后,人们方才醒悟他是以小马自喻,“金鞍子”则是寺宝。加嘎喇嘛西行数千里到达拉萨,在甘丹寺做了高僧。大约中老年时才重返巴塘东区的卓瓦寺。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藏族中就数“康巴汉子”猛悍异常,康巴即川西藏东一带藏民。本世纪初期,巴塘东区和卓瓦寺僧众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藏军发生冲突,藏军力不能支,求助于四川的国民党军队(或军阀),方才平息战乱。时年八十五岁的加嘎喇嘛也被捉去砍了脑袋,叶甸的祖父前往刑场围观。之后,叶甸的祖父和许多战败的巴塘人一道流落到拉萨。又不知怎样北上去了藏北,把巴塘弦子也带到藏北。叶甸娶了一位牧女,后来他们的女儿也成了牧女。
事情仍未了结,卓瓦寺寻找加嘎喇嘛的转世灵童的工作旷日持久,大费周折。若干年后,终于确凿无误地寻到了加嘎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位出世时脖颈上便带了一圈刀疤的男婴。这位活佛尚未成年,适逢一九五九年叛乱,他被一群康巴人带到瑞士,之后他还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瑞士姑娘。“文革”结束时,这位中年活佛来北京观光,叶甸的哥哥还有幸见过他哩。
一首民歌引出一段传奇。西藏民歌所吟唱的,往往果有其人果有其事。在文字难以普及的民间,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
在欢迎美国来宾的晚会上,热心的叶甸不顾六旬高龄表演起高难度的《孔雀舞》,那是需要后折腰一躬到地的,叶甸确实有些力不从心。那晚叶甸一身热巴艺人着装:腰间一圈彩绳垂到膝下。拉起牛角胡且歌且舞,旋转起来时,绳的流苏飞舞得像一把彩伞。来宾中有人用“拍立得”相机抢了一张即刻交给刚下场的叶甸,叶甸望着翩飞如蝴蝶的自己,大喜过望,又笑成了一朵菊花。
为了演出,叶甸弄坏了心爱的牛角胡。琴轴是北京的哥哥送的,雕饰着龙的图案,叶甸为这琴轴配上野牛角的琴筒和羊皮的琴蒙子,并为琴弓和琴弦选择了上好的马尾。牛角胡是西藏特有的乐器,属二胡一类,但因就地取材的局限,音量很小,吱吱唔唔;音域也窄,差不多只有一个八度。本来他想使这把琴更响亮些,便放在牛粪火炉边烤,谁知竟把羊皮烤焦了。演出时只好借了地区副专员次仁玉珠那把来应急。次仁玉珠学拉琴是叶甸的徒弟。
我把录制好的磁带交给若曦女士,歉意地说明并非藏北牧歌。她说那不重要。叶甸的热诚之心是领受了的,叶甸的歌儿也乘上国际航班,远走高飞了的。
在那曲镇我还有一群藏族朋友:加央西热、格桑次仁、多吉才旦、小花……通过这些朋友又认识了更大一群他们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每逢赛马会,人们在体育场搭起帐篷城,我便东家走走,西家串串,从这顶帐篷钻进那顶帐篷。吃酸奶,喝酥油茶。几年来,在那曲镇我参加了好几对藏族青年人的婚礼,不过这些婚礼已不是正规的传统婚礼,而是藏汉结合,只剩下献哈达、喝青稞酒、聚会的规矩了。这是“文革”时破旧俗,多年来提倡节俭办婚事的结果。在藏北,其实许多本土文化及习俗都渐渐归于湮灭,比如上文所述驮盐之类。
传统婚礼却在某些地区有重新复兴的势头,班戈县就是。县领导人占扎热心于民俗,他女儿的婚礼就是按照牧区习俗,经他一手操办的。占扎曾详详细细、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地从头到尾向我描述了一番。
结婚仪式,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的传统中,都表现为程式化和戏剧化的繁文得节,是地方文化的精彩点缀。如今国内的都市和乡村,婚仪已大大简化,婚礼的戏剧色彩也相应减退以至消失。人情味十足的牧区婚仪近些年来在班戈县方兴未艾。占扎说,其实本地的婚礼程序,很多中年人都不清楚,原因是从前的时代里,能举行奢侈婚礼的只是少数贵族头人,平民百姓连参加头人婚礼的资格都没有。六十年代以来,又作为旧风俗旧习惯给革除了。只是在近几年,过日子心盛的人们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