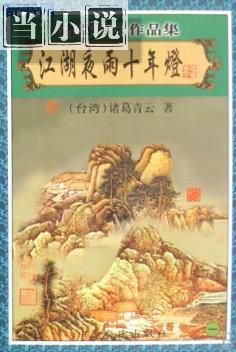点一盏心灯-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要知道,人到了生死交关的时候,常只顾自己逃命,溪水一下子淹进洞里,哪里还会想到伸手等着下面的人来抓?所以这进坑采砚的事,都是一家人,通常做匀亲的在最前面寻找矿脉,弟弟和孩子们则长幼有序地跟在后头,愈年轻的愈接近洞口,也愈安全,女人们则在外面守着。
据说有一个采砚几十年的老人,带着一家儿孙下坑,老人突然挖到一块他从没见过的好砚石,那虽然是块石头,但温润柔腻得如同婴儿的皮肤,摸起来好像有弹性、能呼吸一般,砚工们管这种石头叫端溪石精,就像古灵精怪,是吸收天地寒泉千万年的灵气,才孕育出来的,传说在矿坑里,只要一松手,这处石精就会不见了。当老人挖到这块多少砚工梦想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的石精时,兴奋地交给身边的兄弟,一个人、一个人地传出去,并叮瞩着每个人绝不能松手。哪里知道,这时溪水突然暴涨:一下子冲进了狭窄的砚坑,靠近坑口不远的一个初入坑的孩子,瞬间慌乱了,只记得祖父一路传话出来,这是百年难遇的石精,半辈子可以不愁生活的无价之宝,正犹豫着,一只手已经被外面的人拉住,狠狠地拖了出去。而当他脱离洞口时,另一只手仍然紧紧地抓住石精,只见如排山倒海般直泻而下的洪流,已经淹没了整个砚坑,而他的爷爷、爸爸、叔叔、哥哥们,全留在了洞中。”
每次父亲准备练字,他总是要求父亲重复这个早已会背的故事,看着缓缓研磨的墨,散出淡淡的幽香,原先的清水,逐渐泛出油油的紫光,他觉得那块砚石,正是端溪的岩壁,而那一泓墨,则是壁上深邃的山洞,里面一晃一晃、一闪一闪的,是盏盏的猪油灯,和仰面凿石的工人。而每当父亲说到山洪暴发那一段,他则在心里喊:快逃哟!快逃哟!丢掉石精,保命最重要!
只是故事的结局并没有改,悲剧还是一幕幕地发生了。
“咱们这块端砚是不是石精啊?如果是,我就不要,因为它害死了砚工的一家人!”他对父亲说。
“不是石精害死人,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舍不得扔掉石精,所以害死了洞里面的家人!”父亲说:“你放心!这不是石精,只是一块端砚。虽然如此,这么细、这么紫的砚石,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它同样是工人们手手相传,从阴冷湿黑的坑里采来!”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常偷愉打开紫檀木的盖子,细细端详那块神妙的石头。砚面大约有他三个手掌的幅度,和一个拳头高,靠近砚他的一侧,浮雕着云龙的图案,从龙口向外吐出一道气,里面包含着一个绿色的龙珠,父亲说那叫鹦鸽眼,只有在好的端石上面,才找得那种圆眼。那云的图案一直延伸到砚田的两侧。砚田是暗紫色的,略略横过两三条绿色的石纹,据说是石眼的尾巴。靠近砚田的另一角,则又有着三个绿眼,每个眼的中心,且带着一个黄点,父亲说这叫莲叶田田,池中有水,可灌砚田,田侧有莲,池畔见正,天上有龙,兴云致雨,为降甘霖。
他轻拂砚面,立刻留下小手印,赶紧使劲地搓,却搓出一条条的老泥,像是从久不洗澡的身上搓下来的一般,令他难解的是,这砚石说明总是“洗澡”,为什么每次搓,都会出现老泥?
父亲洗砚,是不假他人之手的。而且既不用肥皂,也不用丝瓜瓤,而是专托朋友找来已经变黄的老莲蓬,磨拭砚上的黑垢,洗完之后,除了底部和侧面用布擦干,对于砚面是绝不碰触的,说是留一些水,正可以润砚,而且如果用布擦拭,难免留下棉屑,磨出来的墨质就不够细了。父亲甚至总要保持砚池里的水,说是用来滋养石头,免得枯干。那哪里是一块砚台,根本就是父亲案头的山水,一片可以灌、可以耕、云蒸水起的土地。
只是父亲故后,那块田便难有人耕了,母亲不准他用,说是小孩不懂事,容易弄坏了,但是母亲还总是为那砚台注水,且说着与父亲一样的话:砚台要滋养,免得枯干,每次看母亲缓缓地收拾收房,见到砚台,像是吃一惊,赶紧冲出去倒半杯水进来,突然欣开檀木盖,将水注下去,又匆匆地盖上,走了出去,他心中就对那砚台升起一种特殊的感觉,甚至是一种敌意。
初中一年级的早春,家里失了火:当他焦着头发跑出大门,熊熊的火苗已经冲破了屋顶,第二天的清晨、母亲带他回到废墟上,走进断垣,只见许多人,一哄而散地跳出墙去,劫后残余的一点东西,全被捡走了。母亲跨过一堆堆烧焦的衣物,算着位置找到书房的残碟,将破瓦和发着炭酸味的断粱小心的抬开,风乍起,未烧尽的书页随着烟灰飞扬,就在那层层的焦土间,露出一块深紫……。
“因为它倒扣着,看来是块烧得半焦的砖,所以没让外人捡去。”在废墟上;临时搭建的草案中,他的母亲又为那方端砚注上清水:“全赖这云龙啊!所以没烧坏,恐怕这石头也有灵,合该跟着咱们!”
当年秋天,他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
“把这块砚台带去磨墨!”母亲居然说出这样令他有些吃惊的话:“你现在大了,应该知道珍惜,而且参加比赛也应该有件利器。”
果然他的砚台一进场就吸引了同学的注意,唯一的缺点,是占据太大的空间。学校的桌子,本就个大,剩下的地方,勉强摆得下竞赛用的毛边纸。
依照记忆中父亲研墨的方式,他将水从研池里移上砚田,再遵守“磨墨如病夫”的原则缓缓研磨,问题是,前后左右的同学早已开始写,他们多半使用现成的墨汁,再不然则用带着墨膏的塑胶盒,即使是和普通砚台的同学。由于从来不洗,砚面上积了一层厚厚的墨垢,没有磨几下,也就可以开动了。
他心里有些着慌,急着动笔,第一笔才下去,就晕开了一大块。豆大的汗珠突然从额头冒了出来,轰轰然,他不记得是怎么写完,只觉得缴上去时、跟别人的作品放在一块,自己的墨色特别淡,仿佛孱弱苍白的病人,站在许多黝黑的壮汉之间。
“父亲不是说这砚台特别发墨吗?它让我丢人丢够!”
他一进门,就把砚台扔在床上,剩下呆立着的母亲,他觉得不仅是自己受了骗,母亲也同样被骗了儿十年:
“我还在磨墨,别人早已经开动。等别的同学都走了,我却还在洗砚台!”他生平第一次愤怒地吼叫。
母亲一声不响地抱起砚台,又从床底下掏出一块火场拾回的破布包了起来。
再见那方端砚,已是许久之后的事。婚礼前夕,母亲捧了一件沉重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书桌上:“你成家了,十年前的那场大火,什么都没留下,只有这块砚台交给你,我知道你并不喜欢,但好歹也是你父亲心爱的东西,就收着吧!”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觉得母亲已经不是记忆中的强者,如同那方端砚、过去是神圣不可碰触的,而今却像是乞求他的收留。
新婚之夜,他喝了不少;却毫无睡意,坐在桌前,突然有要画几笔的冲动,新婚妻子为白瓷的笔洗盛满水,他又要求再倒一杯清水过去,并将那方端砚推到面前,缓缓地将水注下去。
十年了!一个曾经数十载不曾断过供养的石砚,竟然裹在那半焦的破布中,一待就是10年。不知是不是因为过度地干渴,小小的一个砚他,居然用去了大半杯的清水。起初水的声音是暗哑的,随着水位升高,那水声竟泠泠地悠扬起来,像是小河倘水、春凌解冻;又好似古老庭院中,在太湖石间流下的一冽清泉,不是单音的水声,而是由四周的石蝉,做为共鸣箱的回响。为什么过去不曾注意,难道只有像父亲一样,将石砚正正地放在眼前:让砚池另一侧的凹陷处朝向自己,才能因为回响,而听到这么美妙的声音?
“是父亲留下来的唯一一件东西!”他用手指从砚池中眯了些水到砚田上,轻轻地揉搓,仿佛幼时的动作。却觉得身边的妻,恍如父亲高大的身影,而那纤纤柔荑,则成为了父亲温暖的大手,抓着他的手一笔一笔描去……
以后每晚练字,他就都用这块端砚了,即使忙得没有空动笔,他也喜欢用手指沾水,在砚面轻拭,他尤其爱摩裟那田田的莲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绿色的石眼,和其间黄、黑的圆晕,有着软硬高低的不同。在书里他已经读过不少有关端砚的文章,知道那应当是麻子坑的作品。端石原是地球泥盆纪,由地下细腻的泥浆,经过亿万年的高压所形成,在它还是泥浆的时候,或许有些不同成份的泥泡浮动,凝固之后,就成为了这种珍贵的石眼。
但他的妻子说石眼令她觉得有些可怕,好像石头成了精,瞪着绿色的眼珠,和黄色的瞳孔,他便转述小时候要讲的故事给妻听,但把内容改成年轻的孩子丢下手中的石精,使一家人逃脱,却再也找不到石精的结局,他觉得原来的故事太残酷了,使他用这一方端砚,都有些不安。
虽不怎么爱砚台,他的妻却总担任清洗的工作,女人力气小,缩胸挺腹地捧着,有时练字后看见妻子更衣,胸前犹留一道红印,加上妻说在清洗时,不知觉中总会磨伤了手,使他终将端砚置人柜中。
出国前,他的母亲说:“这一去不知道就是多少年,以前人出远门,总要装一瓶故园的土,到异乡不适的时候,就撒些在水里服下,你说美国海关不准带泥土,那么就把你爸爸的那块砚台带去吧!本土是石变的,身体不对劲,摸摸石头也管用!
他觉得有些好笑,但还是顺从了老人的意思,而且唯恐在行李中摔坏了,便放在随身的旅行袋里。从维州跑到纽约,又转到田纳西、北卡、佛罗里达、饿亥俄和加州,每一次搬动,都觉得端砚又加重了几分。
不过他确实常摸那方石头,尤其是在不舒服的时候,他总是揉搓砚面,也如同孩提时所发现的,每回都能搓出许多老泥。他发觉那老泥不是由砚里产生,而是磨损了自己手指的皮肤。好砚台就妙在这卫,看来柔软,像是玉肌腻理、拊不留手,却能在不知觉中磨蚀与它接触的东西。
也就因此,这端砚实在是发黑的,别的砚台需要一百下磨浓,它则只要五六十下,不解的是,为什么初中书法比赛时,却让他出了丑呢?
随着艺术造诣的加深,他渐渐领悟其中的道理。原来愈是佳砚磨出的墨汁,质愈细,也愈容易晕,反不如瓶装墨汁,有时写下去的墨不浸,笔画旁边却见一圈水渍。可以说:差的墨像是水和黑灰相调,墨灰不晕,而水晕。好的墨,则是水墨一体,水动墨也动。正因此,画那飘渺的云烟,必须用好墨佳砚,才能表现得轻灵。
他尤其领悟到,人持墨研磨,但是砚磨墨,更是研磨人,心浮气躁的人,是不堪磨的。
问题是在这个功利为尚的时代,有几人能不浮躁,又有谁不希望能像用瓶装墨汁般立即奏功呢?
这端溪佳砚或是一个时代的瑰宝;甚至更上许多时代,足以让米南宫惹得一身墨,忙不迭揣人怀中的东西,却不一定能被这个时代所接受啊!
所以作大画,或示范挥毫时,他宁愿选择可以快速研磨,而且容量特大的“墨海”砚。他以一种躁切的方式,任凭墨渣崩溅,顷刻磨就一滩墨,再神妙地挥洒出几幅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