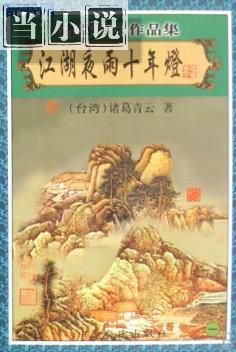点一盏心灯-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下面有块大石头,而我未察;如果那是最贫的黄土地,或没有阳光的死角,就算这种于是最好的,又如何呢?当别人在阳光中茁壮,展开如盖的青绿、开花、结果的时候,它却可能永远像侏儒一样瑟缩在角落,而后或是在怨骂声中,被拔除。或在一个寒流的夜晚,悄悄地死亡。
这样想来,我就觉得自己更伟大了,因为在桃花开的时候,我会特别去摸摸每一朵花蕊,帮助它们受孕;在紫藤攀爬时,我会帮着它们找正确的途径,将那贴在地面的升高,转进铁丝栏的拉出来,使它们不致在往后的日子,因为环境的阻碍而影响了发展。
至于百合、郁金香,这些球根的花,我更在暮秋时,为它们分家,免得在地下不断繁殖,因为挤在一起,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
当然施肥更是不可少的,想想这样“见缝扎针”,一作接着一作,一棵连着一棵,如果没有足够的养分供应,怎么可能长得好呢?我的肥料来源从来不虞缺乏,因为一面除草,也就一面积了肥。我在院角总是挖有一个大坑,将那清除的杂草、朽叶全往里倾,倒满了,则盖上土,经常喷水,使草叶快速地分解,如此一坑一坑地替换,自然总有黑褐色的腐殖肥料供应。有时甚至直接将花果种在这些坑上,长得更是茂盛。
每当我把那些肥料洒在田间时,总是嘀嘀咕咕他说:“来!用你兄弟们的尸骨滋养你吧!”
至于将花果种在肥料坑上时,则讲:“在千人家上建立你的凯旋门吧!”
这时,似乎又觉得自己由这园中伟大的家长,一下子变成了有虐待狂的刽子手,青面撩牙地发出阴阴的冷笑。看世间的繁荣与萧条、生育与杀戮、伟大与卑微,全成为自己导演的一出戏,且沾沾自喜……。
母亲的耳机
母亲配了助听器,家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过去总是听见她在厨房用力地关柜门,将锅盆撞击得锵锵震耳;餐桌上每当她放下碗时,大家更极力地忍耐那碗底与玻璃桌面的强力撞击。尤其使人受不了的是她推电锅,如同粉笔滑过滞塞黑板时令人汗毛耸立的锐利音响。
可是,一下子全不见了!甚至她忙碌地在厨房工作,都令人难以觉察,反倒是,当她刚配上助听器,走出医院时,第一句话就是:这里的车子怎么那样吵?
回到家,更是麻烦了!老人家开始抱怨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太大,又说鹦鹉鬼叫得令她想过去把它掐死,甚至电话铃响和别人打喷嚏,都能把她吓一大跳。
于是过去唯恐铃声不够大,甚至得将无线电话放在她枕边的事情,全做了180度大转变,亲友未进门,更得早早叮嘱:别再对着老人家的耳朵猛喊。
尤其妙的是,她自己的嗓门也突然降下了一大半,过去如洪钟的声音,顿时变成了低语,好像说的都是秘密,她说不敢大声,因为怕炸了自己的耳朵。
跟着老人家便有些得意了起来,笑着警告家里每一员,以后别想再背地里说她坏话,因为连我们关着门讲话,她都可能听得见。指着自己的耳机,老人家说:“我的耳朵比你们强,可大,可小,碰到你们讲悄悄话,只要我把耳机调大声一些,就成了顺风耳!”
老人家果然厉害得有些可怕,走在街上,邻居老太太正跟媳妇聊天,我们年轻人尚且没有听见说什么,老人家却老远地搭上了话,敢情她全听到了,原来是因为过去耳朵不好时,她是半听半猜,日久几乎能从对方嘴唇的移动,来猜想内容,如今听力增进几倍;加上“看”的功夫,自然有了过人之能。
老人更发奇想了,居然要去烫发店,改那20多年未曾变过的发型,原本的巴巴头,换成垂向四周的卷发。原因是助听器虽然是植入耳壳的“隐藏式”,旁人注意,还是看得出来,老人家神气他说:
“要是用头发遮上,回大陆探亲,人家只当我是老少年,听力不让年轻人,多有面子!”
我说:“老小孩!老小孩!人年岁大了,就像小孩儿!您就算梳个马尾巴,我也不管!”
当然助听器也有缺点,就是只戴在右耳,声音即或发生在左边,她也觉得从右边传来,过去大声讲话,她的裸耳还能听见,现在右耳变得敏锐,左耳就完全没有用了。在花园里,只见她一面种菜,一边不断地转头四顾,寻找碉瞅的小鸟和鸣蝉;行在街上,后面有车驶近,老人家总是做成要躲避的样子,正如她所说:前10年,不知是怎么过的,倒没让车撞上,只是也没觉得世界这么吵。
于是我想:这世界真有这么吵吗?对于不觉得吵的人,会不会正像是母亲未戴助听器前,自己反而是噪音的最大制造者?
同样的,作画时用强烈色彩的艺术家,吃饭时要大咸大辣的老餐,只怕实际上,对色彩和味道的感觉,反而比一般人来得迟钝。至于那些一天到晚觉得生活太单调的人,恐怕不是真单调,而该怨自己体味生活情趣的能力太差。
只是身处在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中,正像耳科医生所说,是有许多困扰的,有时候前一个病人是听力障碍者,才大声他说了再见;接着进来的,却是个戴了耳机的,忘记收束自己声音,才开口,便见病人一惊,怨医生说话的声音炸耳,造成医生看病人,未开口,第一件事就是观察对方有没有戴耳机。
这样地推想,才发觉原来世人是那么不相同,我们就得以这不相同的了解,给予不相同的对待,当自己觉得别人的声音太小,而还报以较大的嗓门时,一心只以为是善待了对方,岂知却缘于自己的听力已经衰退。
写到这儿,突见老人家蹑人书房,比了个吃饭的手势,过去她总是站在楼梯口大喊一声,怎么而今有了恁大的改变。
敢情听力太好的人,只怕自己大声说话会伤了自己耳朵,竟要变成哑巴了吗?
风筝之歌
每一次看到孩子放风筝,就使我想起大学刚毕业,在成功高中教书的日子。放学之后,我沿着林森南路,穿过交通频繁的忠孝东路,再向北行,走过火车道上的高架桥,回我位于长安东路的家。
或许因为当时还没有铁路电气化,华山车站前的空地又大,每次行过高架桥,总看到许多孩子站在上面放风筝,有时候火车正轰轰地驶过,孩子反而大胆地开始松线,让小小的纸鸯,乘着那一阵火车带来的风,倏地飞上天际。
连我,也常跟着一块儿叫好,日久了,与孩子都熟念起来。
那些孩子,多半都住在铁道边的违章建筑里,贫寒的环境,使他们买不起风筝,只好自己糊,有些孩子手艺好,风筝一脱手,就能直上云霄;手艺差的,则任他牵着线,沿铁道边的小路跑上百公尺,风筝还是又扭又转地;最后栽下来。
跟他们相处近一年的日子里,最令我难忘的,倒不是放风筝这件事,而是孩子们天真的对话。记得某日傍晚,虽然天色已经沉下来,有个孩子仍然兀自站在桥头,舍不得收线,因为他的心已经随着风筝飞上了天际,他放出了有生以来,最远的一只风筝,我则是唯一陪着他的人,分享他的骄傲。
突然从巷子里闪出一个人影,尖着嗓子喊:
“这么晚了,野到哪里去了?还不回家,小心挨揍!”
孩子一下慌了,手忙脚乱地收线,却愈是心慌,手愈不听使唤,几次把线绞成一团,又几次让已收好的线溜了出去。孩子急了,虽然在阴暗的暮色中,仍然可以看到他急得泛红的双颊,他气急败坏喃喃地说:
“回家!回家!当然可以回家,可是我要回家,它(凤筝)不要回家,我怎么回得了家?是它野!不是我野,口家打它!”
孩子天真的话语,却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人生境界。以后的日子,我先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诗,又引申为哲理,放在“萤窗小语”之中,而一直到今天,每次在异国的郊野,看到孩子们放风筝,更总是把我带回那一刻:“我要回家,它不要回家,我怎么回得了家?”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只有两样玩具,一直不曾褪色。一个是我收藏成堆的香烟罐,一个是我的老鹰风筝。
香烟罐并不能算是我最喜爱的,之所以能记忆这么清楚,大概是因为搬家时全忘在旧房子里,由于心疼、吵闹而变得深刻。老鹰风筝则是我真正喜爱的东西,因为它是父亲买的,再加以组合,帮我放上天去,且将线的一头交入我的手中。
那是一个午后,想必正逢假日,父亲带我到家附近的龙安国小玩,才走出巷口,就看到天上有一只老鹰在盘旋,可以很清楚地认出头和身体,还有那抖动的翅膀。
“老鹰!老鹰!”5岁的我,大声叫着。
父亲抬头看了一阵,说:“大概不是真的,是个风筝!”
那时候似乎放风筝的人不多,最少这是我所听到的一个新名词——风筝。
我们走入龙安国小,果然操场中央,正有位老先生在放风筝,几个孩子指手画脚地围在四周。
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也忘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专卖风筝的,只晓得那风筝后来到了父亲手中。
对于凤筝的印象却是极深刻的,那是以细竹条编成骨架,再缝上灰色的绸子制成;绸子上还画着眼睛和羽毛的图纹。但如果仅仅是这样,还不能给人那么逼真的感觉,它妙在不但有老鹰长长的身体,而且还有个弯弯的弧度,看来就像是立体的身躯,头上更带着尖尖的啄,加上圆睁的双目,真是威风凛凛;至于翅膀,一半有着竹架的支撑,一半则任那轻绸虚挂着,放上天去,风一振,翅膀就扑扑抖动,活像是展翅翱翔的座隼。尤其神妙的是,那双翅膀居然可以装卸,不用时将翅膀抽下,只占小小的空间;要玩时,则只需将翅膀近身一侧的两支长竹片,插入身体上的插座中,就顿时成为了足有三尺宽的风筝。
往后好长一段日子,每当父亲有空,又天气晴和,我们都是伴着风筝度过的。父亲先将风筝装好,放上天空,再把线圈交到我手上。
“小心拿着,这风筝老鹰一飞上天,就成真的了!真老鹰力量可大极了!抓不紧,它就会飞不见的。”
听了这话,我的小手是抓得更紧了,只觉得长线的那一头,有着不断的震动传过来,那是一种挣扎!它想飞跑。因为凤筝老鹰的家是在天上,所以一上天,它就活了!只是为什么一落地,它的翅膀又跟身体分开,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抽屉里呢?
第一个自己做的凤筝,根本没能上得了天,才起飞,就栽到地上,岂像我那坏了的老鹰风筝,只要一只手,迎着风,轻轻地松线,自己就能展翅而去。
但我还是捡回了那只不会飞的风筝,重新绑,重新糊纸,又重新在苍茫的暮色里,冲出门去,加入那群犹未散去的小朋友中,请一个孩子抓住风筝的下端,在高喊松手时,抓着线圈猛跑。
只是依然掉了下来。
渐渐地,我做的风筝有了进步,虽然还飞不高,且猛打转,但总是飞了起来。
我把风筝拆开,将小竹条削得更平均,又拿另一支竹子撑着,量度出重心,画上记号,再把垂的那根绑上去,且斜着加上两支小竹片。由于左右力量非常平均,相信绝不会再打转了。
只是放上天,它虽不转,却仍左右摇摆个不停,我又丢了脸,直到有一天,为它装上了好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