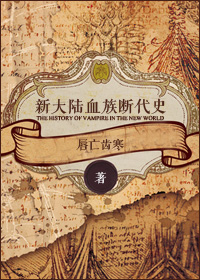新中国近代史-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和梦兰七月认识,十月结婚,也算是快的了——因为我要去日本留学,梅家又没有什么亲人,婚礼以外的形式就都简化了。
湖北武备学堂的学制为三年,分为学科和术科。我迅速的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学科,及大部分术科的考试,其余的术科也低空掠过了。为了能留学,我是花了大价钱的——我的时间比钱重要,钱能解决的问题,对我就不是问题。湖广总督张之洞接见留学生时,知道我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作者,欲去日本留学,不由大笑问我为何?我朗声道:“西洋藏真知,求真知,当人往西洋。”张之洞奇道:“那你为何要往东洋?”
我笑而不语,张也漫不在意,遂成行。
PS:后人读史至此,对曰:“东灜通权场,行大道,须手持权柄。”
我给弟弟去信说,我要结婚了,你嫂子姓是名谁,家庭情况等等,介绍一遍,并告诉他不用回来了,一来一回,得折腾大半年,把礼物捎回来就行了。然后,我开始关心阿庭的感情生活——难道我也老了,现在就想这么多。不过,阿庭也该有个女朋友了。
1899年年底,华源基金在国内开始资助书院兴办新学。通常,华源基金选择有一定名望的,热心公益,关心教育,品行较好的人士创办学校,华源基金对具体的课程和课时,及学生待遇有一定要求。
目前来说,创办的新学多是小学,课程分为识字、算数、体育、历史、自然和礼仪等。其中,识字是《千字文》等简单的经史和名篇欣赏;算数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体育以武术和军训为主;历史以古代史为主,《史记》为课外读物;自然是关于世界的一些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礼仪是将传统礼仪的具体简化——由于没有一定的标准,多半各搞一套。一年以后,由华源基金牵头,组织编写了一套《礼仪》,作为礼仪课本。《礼仪》主要从思想、礼节、言谈、举止等几方面,对礼仪作了具体的描述,区分了公共道德、私人交往、言谈举止,等等。
学生待遇,就是免费午餐,奖学金和低廉的学费等等。
首批受到资助的书院有五所,包括梅溪书院、龙门书院和静海书院——霍元甲办的那所。资助双方签订一份文书,约定书院提供给就学学子哪些条件,如,免费午餐、课间餐及伙食标准等,课程和课时有什么要求。此文书将抄写公示,书院的帐目要公开,以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华源基金的审核。华源基金的审核每年一次,也有不定期的审核,审核过程和结果公开。
99年冬,我带着妻子岳母,东渡日本,先入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接受为期16个月的预备教育,受毕预备教育后,被分配到各连队,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接受一年的正式教育,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一年的后期教育,修毕士官课程,再入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最后取得士官资格。
来日本上军校,我是有考虑的。以后在中国各地掌握新军的将是什么人?90%都是日本军校毕业的,基本没有欧美军校毕业生。二十世纪初,正是中日的“蜜月期”。日俄战争后,无论是康、梁、谭等改良主义君主立宪的新政人士,还是孙、黄等革命党人,无不选择向日本学习,以为更适合中国。华源基金的早期留学生,通常是家境不好;后期的留学生,则多是因为华源基金的声望和对欧美的了解所致。但那是民间舆论,清政府还是倾向于日本。
相对而言,日本陆军的军事思想很落后,但怎么也比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我强。日本的军校分为陆军XX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很多学生都是从陆军XX幼年学校毕业的,军事素质比我强,然我并不在意,只是努力学习。“难道还能落后于小日本吗?”尽管我从来没有说过此话,但我就是这么想的。1903年11月,我以多科第一,总分第一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
我满心欢喜的YY着日本天皇的赐刀。10月22日,校方突然通知我,我将作为清國學生单独毕业授衔,以后,这会成为制度。我靠!我们一直和日本人一起上课考核,现在却来个单独毕业授衔。小日本也真能做的出来!一把破刀都舍不得。然,此事已成定局,一切争执全无意义。我看着洋洋自得的永野教官,很恭谨地鞠了个躬,道:“知道了。我对贵国的武士道精神深表敬意。”永野的油脸涨得通红,喃嗫了几句,就飞快地离开了。
毕业典礼那天,窪津義雄手持日本天皇的赐刀,得意洋洋。我毫不在意的冲他点点头,那东西本来也没什么用处,不过是个唬头。将来,我还不知要缴获多少把呢?!而且,我现在仍然可以用这来炒作,比如说,我成绩多么多么出色,所有科目名列第一,日本人迫不得已,将我和日本学生分开授衔。我说的基本是事实,到时候,让别人一宣传,仍可谋到我想要的职位。
我通过卫兵的检查,将论文交给伏见宫亲王,请他转交给日本天皇。自然说话要有礼貌,我来自礼仪之邦,自己的素质不能因为外界因素而降低。
论文很简单,大致有三个问题:一,中日之间的战争、战争进程和战争胜负;二,世界局势及世界中心的西移;三,中日同盟。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段论,傻瓜都知道。这样的东西在十几年后给日本,绝对是个叛国行为。日本军方可以在行动前据此来进一步完善它的侵略行动。然而,此时中国与日本相比差距不大。只是在原来历史上,日本在此后二十年间快速发展,而我国却停滞不前。如今自然不会再有此事,也就是说,此三段论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它有几个好处:一,它反映了我的战略眼光——想骗人总得有点儿真东西;二,它满足了日本的自大心理,目前,中日差距不大,如果在甲午战争时,中国迁都再战,奖励善战,尽斩逃官,日本的国力根本不可能支持到胜利,然帝后之争决定中国必然失败;三,在明智的人眼里,会将我看得低一点儿——认为我言过其实。
我在这个问题的最后写道:“……日本的失败是注定的。退一万步讲,日本惨胜,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十年以内,消化掉胜利果实,在内部的抵抗和外部的干涉下,将日本军力消耗在这广袤的土地上。
无论如何,中日之战,两者都不会胜利。
……”
然后,我分析了世界局势及世界中心的西移。世界局势就不细说了,大家自己看资料。“……
欧洲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这里的决定影响全世界,这里的局势决定全世界。谁掌握了欧洲,谁就掌握了世界,成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无可辩驳,现在的世界是一个西方的世界,一切规则都由西方国家制定,也必有利于西方国家。
无论中日之战的胜利者是谁,他都将是东方文明的继承者,西方世界的挑战者。难道西方国家会坐视不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大家不要鄙视我,适当的马屁是必要滴)
……(这里我谈了一下干涉的各种手段。)
中日结盟,首先,它必然是个秘密同盟——这是东西力量对比决定的。
……(我在这里预测了未来的欧洲主导权争夺战——世界大战的本质就是如此。)
中日同盟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将具备挑战西方世界的实力。退一步讲,也可以统治亚洲,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
……
中日同盟的领导者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实力是唯一的标准。但无论哪一个国家成为这个领导者,都无法忽视另一国家的利益。也就是说,两国都将成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都将成为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几个国家之一,都将成为世界性强国。”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在日本高层引起的轰动。在毕业典礼的当天晚上,我已乘坐美国邮轮离开了日本,连授衔仪式都没有参加——我事先已向校方说明家中有事不能参加。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谁知道日本鬼子会干出什么事来——日本人的道德之差,我听得太多了。但有些儿风险是不得不冒的,我也是在为将来做铺垫。将来,一旦我掌握权势,以日本人的习惯,这篇文章必然会反复研究。不但加强了我在日本的影响,也使结盟成为日本更希望的选择。日本的先天不足,决定它只能成为某一强国的看门狗。但是,养疯狗去咬人和被别人养的疯狗咬,是人都知道怎么选择。
别跟我说,灭了日本,你还能把日本杀光吗?杀不光,你灭个屁!而且,灭日、灭俄、灭欧、灭美,横扫全世界,这样的故事纯是YY无极限。美国现在那么牛,也不敢如此吹。任何一国都不可能与全世界为敌——除了慈禧那个白痴!(我的野心是很大滴!)
中国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也就很难彻底解决日本。既然如此,就只好结盟了。而且,中国的命脉在陆地,日本的命脉在海洋,双方很有互补性。
我在军校与其他留学生不很熟悉,一来我挟妻子来日本留学,大家活动时间不一致;再者,我为人沉默寡言,不太喜欢说话。最多《浙江潮》缺钱时赞助一点儿,从不参与他们的活动——如1903年的“拒俄运动”,我觉得那意义不大,不解决实际问题——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即便我来日本较早,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帮助,但大家只是对我印象不错,并不很熟悉。这几年实在是中国极屈辱的年代,八国联军两万人就打进了北京后,中国已经完全没有国际地位而言——我对弟弟能够在此种境况下保护美国华人的部分利益,极感欣慰。每每有消息传来,中国留学生多痛哭流涕,我也极为愤怒,然我有太多的话不能与人言,只好沉默寡言。
我上学时,历史书上都说,八国联军如何如何。然,现在一看,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满清实在是自取其辱——在自己极度虚弱的时候,却主动挑起事端。当你连一个国家都打不过时,却向11个国家宣战。那不是勇敢,也不是革命主义,那是智商低于八十的具体表现。中日甲午战争刚过没几年,满清伤疤未好,就忘了痛,居然向十一国宣战。我听说此事时,实在是无话可说——中国还要在这样白痴的统治者统治好些年,我可以说什么呢?
至于义和团,我不想多作评价,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义和团有十几万人。其中,有大刀王五这样慷慨激昂的英雄,但更多的还是浑水摸鱼者。未经训练,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纲领,义和团在迅速扩张后,军纪还不如满清的绿营兵。这样庞大的一个组织,失去控制会导致什么后果,不必霍元甲来信,我也能够想像——霍到北京给王五收尸。
我显然不能批评这样政府支持的爱国运动,只能保持沉默。
旅日留学生中,我只与后来被称为“中国三杰”中的蒋百里略有交往,蒋在《浙江潮》没钱了偶尔去我那里拿。我从来没有二话,百里开口,多少钱我都没有回绝过。只是蒋是个极有分寸的人,开始是迫不得已,求助于我。后来熟悉了,时常出入我在东京的住所,仍然只是没有办法了,偶尔向我开口。就是在几年里,我养成了沉默寡言,深思熟虑的的习惯。蒋百里常说我“沉默寡言,言出必中”,这自然是他夸赞我,但多少也有点儿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