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机会叫趁虚而入-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难免的,又问到她男朋友的事情。她拿筷子的手明显的顿了一下,何清抬眼看她,细长的眉眼里看不清情绪。她明显的脸上僵硬了一下,最后还是说道:“老师放心,宁真交了一个男朋友,他人还不错——以后肯定带回来给老师看看——”
最后,何清送她回家。已是明月当空。何清说:“小真,城西河边改建的很不错,我带你去逛逛,怎么样?”两个身影并肩而走,她的眼里涌上了难言的痛楚,眼前这个人,是她从初中听到旁的女生说暗恋开始,就无法自拔的把一腔少女的心投了进去。那些年,她为他写了多少诗歌,那样的思慕在午夜梦回让她酸楚难当。
她的心,一直孤独的漂浮在空中,只有月光可以取暖。
她本以为此生就这样算了,奈何遇到了许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去了解她进入她的灵魂,可是许斌偏偏成了例外。她那么多年的孤独,倾盆而泻,也正是如此,那些夜晚许斌电话里的温情脉脉让她上了瘾。
她想,如果此生,还能有一场爱情,那个人,只能是许斌。
她飞蛾扑火的赶过去,为这一生唯一的爱情,他们抵死缠绵一夜疯狂。开的太美,也凋零的太快。她接受这样的命运,所以,她不仅不怪许斌。反而,她感激他。
一路无语,城西的河蜿蜒流长,两边都是高耸的乔木,在路灯下,把她和何清的影子投成斑斓。那些影子,就仿佛是他们的过去,白日里看不见,夜晚却婆娑寂寥。是什么时候,她和何清变得这般疏远了?其实,她,真的想牵着他的手。
她曾经是一个孤僻的少女,总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想着眼前这个人,为他写下数不清的诗歌。她曾经也是一个问题别扭少女,看尼采和叔本华,寻找生命的意义。而她,最终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件最出格的事情。
大学录取通知已经下来。而她心里的思慕和魔障也无法遏制。那个盛夏,他坐在她的房间的窗边,打开数学课本,耐心指点着她高考的失误之处。最后他叹息:“小真,还好你选的是外语系,你果真不是学数学的料。”那年,她十八岁,他二十八岁,她穿着红色的连衣裙,痴迷的看着穿着白衬衫的他。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轻轻的唤了一声:“哥哥。”
他站起身,走到她的旁边,揉着她的头发,责怪道:“一提到数学,你就不认真听——”那个时候的她就是觉得他细长的眉眼里都是星光。那些光,陪伴她多年,却再也不属于她。她情难自抑,紧紧的抱住了他的腰。她踮起脚,波光粼粼的眼睛看向他:“哥哥,我喜欢你。喜欢你好多年了。”
那个午后的他们,或许都已经疯狂。他熟练的吻着她,手便伸进了她的裙子,两人倒在了床上。终究在最后一步,他清醒了过来,临阵脱逃。后来,她上了大学,去了苏州,偶尔回来,两人在林老师面前依然若无其事。
很多时候,那些过往,那些执念,构成了抵达幸福的藩篱。
两人在河边的石凳上坐着,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皱了下眉头,号码是+44开头的。周六不可能是德国客户来电,除非是,郁嘉平。电话响个不停,她不愿接,想挂断又怕惹到郁嘉平。
郁嘉平,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她无奈的接了,语气平淡无波:“郁嘉平,有事吗?”
“宁真,在做些什么呢?花喜欢吗?”郁嘉平是特地挑这个点打来的,他可不希望这个点她在陪着别人!郁嘉平的声音很大,旁边的何清自然也听见了。
“没做什么,花收到了,谢谢。没事的话,我挂电话了。”她无意多说。
郁嘉平何许人也,他立刻便嗅到了不对劲的苗头,语气也凌厉了起来:“宁真,你在跟谁一起?郑易云?”
她头疼不止,对上何清的眼睛,脸上浮上了尴尬之色。她委婉的说道:“我在老家,现在在和哥哥一起。”
“哥哥?”郁嘉平的声音微扬:“刚好我跟你的哥哥聊聊——”
“郁嘉平,你有完没完?”她咬牙切齿。倒是何清做个接手机的手势。电话里,郁嘉平威胁道:“宁真,你给不给?”她无奈的把手机给了何清。
“你好,我是小真的哥哥,何清。”
“我是宁真的男朋友,郁嘉平。”
“很高兴认识你,小真是个好女孩,可能性格上有点古怪,你要多担待一些。”
“何止是古怪——简直是——不过你放心,我有这个风度——”
章节目录 第18章 初识(十八)
有的时候,天空也明白人的心情吗?
只在家住了一晚,周日下午宁真便回了苏州。下了高铁的时候,天空已经淅淅沥沥的下起了雨。她在公交站牌上等车的时候,寥寥无几的行人,白墙黑瓦的古典院墙和一辆接一辆的车子,形成微妙的对比。旁边有个同是等车的人,手机里正播放着一首歌。
今天晚上,趁着月光
离开这个地方
……
而我始终只是匆匆过客
命运谁又能够改变
……
我们总是爱的太早又放弃太快
……
她感觉到寂寞,在整个尘世之间,孤立行走,没有可以取暖的人。愁绪还来不及下去,公交车已经到了。她坐上车的时候,手机便响了起来。
“有事吗?”她直接连名字都省去了。
“苏州下雨了,你有没有带伞?我让人过去接你。”郁嘉平的声音里面都是理所当然,昨晚他逼着她说出今天的回程车次,又查到苏州已经下雨,这个点德国正是早上,他洗簌好正准备去公司。他不介意对她上了心,他想做什么,谁又能阻挡?
“不必了,已经坐上车了。”她的声音有了些说不清的情绪,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水模糊了玻璃窗,手中握着的手机仿佛有了暖意。
“你自己多注意,别淋了雨。”说着便挂断了电话。
宁真还是淋了雨,这一场雨后,十一月的苏州已有了冬天的气息,她理所当然的感冒了,纸巾用了一卷还不见好,感冒灵也不知喝了多少,还是这副鼻塞流涕时而咳嗽不死不活的样子。郁嘉平开始每天给她电话,倒没说什么,就为了听下她的声音,问下她有没有好些。
还好这周开始宁真只要带新人就可以了,工作上轻松很多,基本就是一边用纸巾捂着鼻子一边指手画脚就行,她总算也是体会了一把当小领导的感觉。难怪这人都爱做领导,感觉确实不错。
周五总算放晴了,下班的时候,郑易云送她回去。她坐在郑易云的车上,原先摆着的很花俏的餐巾盒被换成了一个简洁大方的,她一边抽着纸巾擦鼻涕,一边说道:“易云,等我感冒好了请你吃饭。”郑易云打趣道:“等你感冒好,冬天还不都过去了,明天我们去吃刷羊肉,这辣一下说不准你这感冒就好了!”
她捂着鼻子刻意往旁边侧了侧,笑着说:“我这样子,把你传染到就不好了。”
这个时候,刚好到了小区门口,郑易云停下车,俊秀的脸便凑到了她的脸边,深吸了一口气,调侃的笑道:“放心吧,我是百毒不侵的,这点毒,还伤不了我。”她的脸腾的红了,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脸,他温情脉脉的眼神一下子就像被许斌附了体,她立刻怔住了。郑易云的手支在她的身侧,整个人以一个包裹的姿势把她揽在怀中,他清晰的看到她嫣红的耳朵,将她如花盛开的脸和洁白的脖颈尽收眼底。他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男人,自与女朋友分手后便没再动欲,如今近在眼前的美色,加上他确实对这个坚强自立的女孩有了好感,他便吻上了她的脸。
他的舌头细致的吻着她的脸,一手揉着她的发丝引导她的脸扬起,从脸一路吻到她的脖颈。她闭上了眼睛,这样的缠绵缱绻仿佛就让她回到了与许斌的那一晚。如果这个世间,谁还能代替许斌,只有郑易云。
郑易云白净细腻的手指灵活的解开她的风衣的领口,舌头依然在她的脖子上啃噬着,直到她气喘吁吁才辗转而下。郑易云还是有着理智的,他压抑着自己的欲|火放开了她,气息不稳的说道:“宁真,去我家。我们再继续。”
她这才惊醒过来,她究竟在做什么,慌张的扣好风衣,打开车门,拎着包仓皇的就下了车。郑易云眼神莫测了一番,便开车走了。她感觉这个冬天好冷,冷入骨髓,低着头泪水便落了下来。
一个声音阴测测的响起:“果真是香艳的一幕啊!”
她浑身打了个颤,面前的郁嘉平双手抱胸,闲闲的站着,直直的看着她,黝黑的伏犀眼闪烁着凌厉不明的光芒。她还未收拾掉眼里的泪水,便转身要走。她可不能回家,郁嘉平不是她能惹得起的。郁嘉平长臂一伸,扯住了她的胳膊,他的手指发狠的掐着她的手臂,把她往电梯方向拖。她挣扎着,已是一脸泪水,无力的说道:“郁嘉平,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放开?让你跟姓郑的一度春宵?宁真,你还要不要脸!”
好在电梯口都没有人,他直接把她拖进电梯里,电梯门一合上,他一手掐着她的胳膊,看着这张梨花带雨的脸,一手便扬了起来。他咬牙切齿:“好你个宁真!不识好歹的东西!我这么久没碰女人,就想好好跟你来一场,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一巴掌就要打下来,却最终没下得了手。“哼,本少爷才不会打女人!”
自那晚他说出要追她的话,他是真的下定了决心,要和宁真好好的来一场。他何曾对一个女人如此费尽心机,以前的那些女人,他从来都是直奔目的,最后一拍两散,他不介意花点钱打发她们,他郁大少爷,对女人可从来都是大方的很。
电梯停下的时候,他拖着她出来的时候,一对男女正在门口,怪异的看了他们一眼便进了电梯,楼道里有老奶奶推着婴儿车走过来。她头发披散一脸是泪,狼狈不堪。她歇斯底里的哽咽着:“郁嘉平,我不要回家。”
他用力的拖着她,眉目间都是冷气:“宁真,你跟我回去再说。”
她蹲了下来死活不走,把手中的包狠狠的砸向他,泪流满面的看着他,眼神里面都是破碎的哀戚:“郁嘉平,你给我滚,给我滚。”
老奶奶推着婴儿车停了下来,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不走。他不耐烦的说:“我们回家再说,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郁嘉平,我受够了,什么面子不面子,我的心都碎了,活不下去了,还要面子有什么用?”她摇着头,痛楚的抱着头,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谁能告诉她,该怎么活下去。从小时候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像一只流浪狗躲在林老师的家里,这个时候何清出现了,她的眼里她的心里便种下了这一腔思慕。可是何清有了女朋友,再后来又结婚了,她从大学便开始了一场逃亡,逃了多少年,好不容易出现了许斌,许斌夺走了她的心,又把她丢弃在这个空旷的世界。
为什么她的人生,从来就只有一个人,活的这般空旷这般寂寥。
他一把抱起她,把她抗在肩上,文质彬彬的对老奶奶说道:“我老婆在跟我闹性子呢。”
进了房间,他直接把她扔到了床上,嫌弃的脱下西装,西装上都沾上了她的鼻涕和眼泪。他捋高衬衫的袖子,以压迫式的姿势走向床上的她,她还在哭的死去活来,蜷缩在那里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他抚摸着她的头发,粗粝的手指便擦上她的泪水。
“乖,不要哭了。宁真,我们该好好谈谈。”既然决定追她,他对她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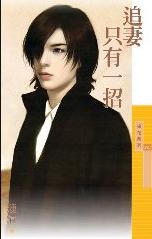



![[重生穿书]总有一款总裁被掰弯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16/1653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