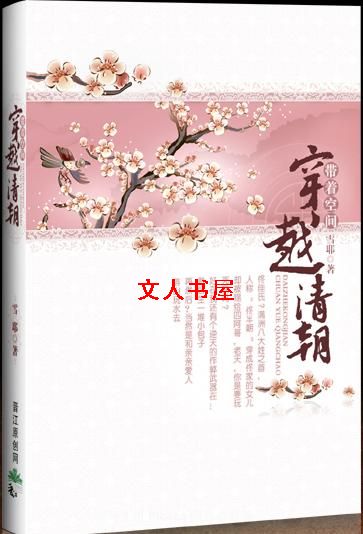穿到清朝当戏子-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茗这才晓得自己如今在西祠楼。
西祠楼,白茗是听说过的,据说这西祠楼的老板原先是春沁园的台柱,离开春沁园之后便开了这西祠楼,那苏老板平日并不过来,这西祠楼上下全由花老板打点。
商老爷做寿的时候,苏倾池去商府唱堂会,白茗那时见过他一面,只记得是个长相俊美,形容清淡的男子,再无别的印象。
原先白茗就听苏宝儿说他哥如何如何,竟不知他口中的哥哥便是京城名角儿苏老板。
“你见着了吧,花老板身边的小厮?”小僮给白茗喂了一口白粥,“性子又烈又野,脾气坏得不得了,咱们楼里上下没人敢惹,前儿个柳官儿,,就是咱翡翠班的小戏子,他喜欢咱们花老板,这事儿谁都晓得,偏花老板立了规矩,不碰班子里的人,他心里便怨上了花老板身边的小厮,那小厮不晓得叫陈俊还是程俊,反正柳官儿就和他对上了,前儿个当着陈俊的面骂了句狐狸精,你猜怎么着?”
白茗才醒没多久,并不晓得那什么小厮,听小僮说得起劲,他便也没打搅。
小僮瞧瞧左右,压低声音说,“那陈俊立马就赏了柳官儿一个大嘴巴子,啧啧,如今柳官儿还在屋里躺着呢,脸肿得不成模样,花老板去看了他,哄了半天呢。”
白茗心里有些怕,想着日后遇到这陈俊,定要饶着走。
小僮又在房里同他说了些话,让他好生养着,要什么只管叫他,便收拾了碗筷走了。
连着几日的汤药,白茗身子已好了许多,苏宝儿隔三差五便过来瞧他,给他带些汤汁的小吃食,又经常买些小玩意儿送他,白茗心里欢喜,想着,若是能一直如此该多好,但他终究得回商府,这般一想,白茗眉间便多了几分忧郁。
苏宝儿自是瞧出来了,便去同花景昭讲,问他能不能想法子将白茗弄出商府。花景昭倒是没说话,从柜子里的匣子中取了份东西给他,苏宝儿一瞧,竟是白茗的卖身契。
“虽说白茗原先是质贝勒府上的人,商府不能将白茗转手与人,但若质贝勒亲自出面,这事就容易得多。”
“那白茗在商府伤成这样,商老爷如何跟质贝勒交代?”
“你当这些日子大夫开的那些好药哪里来的,商府自然隐瞒了白茗受伤的消息,只跟质贝勒说白茗随商承恩出门了,过些日子就将人与卖身契送去。那质贝勒与你哥,与我都有些交情,我同他讨一个下人,这点面子他不会不给。”
白茗得知此事时,愣了半晌,将那卖身契看了一遍又一遍,随后便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苏宝儿手足无措,只拼命拿袖子给他擦眼泪,“哎哎哎,你别哭啊,哭得我心都乱了。”
白茗抽抽噎噎,终于止了眼泪,看着苏宝儿慌乱的模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苏宝儿被他这一哭一笑弄得愣愣,见他笑了,也跟着笑起来。
心里多年的郁结终于结了,白茗的身子好得更快了,没出几日便能下床走动了。
白茗虽不是好动之人,但这般在床上躺了大半月,多少也有些憋得慌,等大夫点头说无碍了,他便迫不及待地披了衣裳出了房间。
外头依旧冰天雪地,一阵风夹杂着雪花吹过来,让白茗打了个寒颤,心情却愈加好了。
这半个多月的疗养,非但没有让白茗消瘦半分,反倒让整个人气色更加红润,他这般皓齿朱唇,站在垂冰的花廊下,越发显得清丽可人了。
一双眼眸痴痴地望着走廊转角口,多少小心思清清楚楚地写在眸中。
听见楼梯口有些动响,白茗难掩心中欢喜,迫不及待地奔过去,然而上来的人并不是苏宝儿,却是一个长相丑陋的男子。
白茗的身子僵在原地。
那人冰冷的目光何其熟悉,像是一条吐着鲜红信子的毒蛇,正眯着眼睛靠近。
凭着记忆,寻到了这条巷子,巷子枕河而眠,旁边便是一条河。
这里水道纵横,三步两桥,位置偏僻,却也别有一番水巷滋味,同巷口的老翁问了路,终于找到了三年前的这栋宅子。
然而苏倾池有些失望,这宅子已经落了锁,而且从锁上的斑斑锈迹来看,这宅子早就空了。
“这位大嫂,请问这宅子里的人去了何处?”
“也亏得你问我,若是问旁人,怕还不知到这事儿,这宅子里的人前些年就应征入伍,听说是编入绿营兵了,去年倒是回来过一次,不过如今四川那边正在打仗,他来得也匆忙,单人匹马,瞧模样像是回来找人的,大约是没寻到人,隔天便又回去了。”
终究是来晚了。
别过那妇人,苏倾池在宅子门前又站了一会儿。
罢了,日后若是还能再见着,再交还与他。
这般想着,苏倾池便携了一分失落而归,本想这日头已落山,商承德该回来了,哪知客栈里依旧没个人影儿,倒是店伙计上来给他带了句话儿,说是叠翠楼有人传话来说有位姓商的公子在等他,说着店伙计取了一块玉石交给他。
那玉石正是商承德平日随身佩戴之物。
“叠翠楼?”
苏倾池略一思索,并不记得这什么叠翠楼。
莫怪苏倾池没有印象,这叠翠楼并不是什么茶馆酒肆,却是这扬州城数一数二的青楼妓馆。
缘,执念
“扬州,胜地也。每至城向西,娼楼之上常有纱灯无数,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又有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或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沉醉在这温柔乡,钟情于青楼有了,肆意放纵,享尽尘世之娱,男女之欢。
可见这扬州城之酒色风流,并非妄言。这扬州城自古便是个声色酒香之地,渡钞关过去半里,有百来条小巷,巷口狭窄深邃,却是明|妓暗|娼云集。
往来之中,青楼林立,粉黛无数,越往里去,胭脂香粉味道越浓。
苏倾池于脂粉香气云袖中走过,不由低头凝思,商承德并不是那等风流之人,也非好色浪徒,如今却约了他青楼相见,苏倾池虽疑惑,却也未作耽搁,径自向那叠翠楼走去。
叠翠楼小厮引了苏倾池去楼上雅间儿,远远地便听到最里间的轻吟小调,又有吴侬软语调笑,倒是热闹。小厮在门上轻敲两下,随即推开门,将苏倾池让进去。
酒气脂粉扑面而至,险些叫苏倾池退开一步,房间之内一位修身少年以丝绢蒙眼,正同几位衣着轻薄的女子嬉闹,房间中央的雕花圆台,酒菜杂陈,桌上两个男子,一个歪歪倒倒地趴在台子上,看样子是醉得厉害,另一个倒是正襟端坐,除却面颊绯红,并无半分凌乱之态,模样瞧着甚是清醒。
苏倾池扫了一圈,那少年摘下丝绢,露出一张清俊的脸庞,苏倾池认出他是程砚秋的胞弟程砚卿,此时那少年早瘫在脂粉堆里,正嬉笑着与她们抢酒吃。
见苏倾池来了,那端坐之人冲他一笑,“你来了?”
随后挥手让几个陪酒的女子退下,又招来小厮将程氏兄弟安顿了,那程砚卿孩子心性,胡闹撒泼一番,倒也叫人哄下去了。
等人散尽了,这屋里只剩苏倾池和商承德两人,苏倾池暗叹一声,正待说什么,下一刻,商承德却靠了过来,附耳低语道,“我醉得厉害,你且让我靠一会。”
商承德酒量素来不错,从不轻易醉酒,如今竟露出这般醉态。
人已醉了,况且这里不是久留的地方,苏倾池半撑半扶,将商承德扶下了楼,又招了顶轿子。
轿子缓缓摇晃,商承德靠着苏倾池,温热的鼻息拂在苏倾池颈侧,带着浅浅的酒气。
商承德神色虽无异,面上却渐渐泛了红晕,大约是酒劲上来了,语速缓慢停顿,“你若是……不来,我今天怕是得待那儿了,我知你不喜脂粉味,如今却沾得这一身,你……”
他难受地皱了下眉,接着道,“你定要生气。”
苏倾池顺了顺他的背,却是没说话。
商承德眼神已难掩迷离,只抓着苏倾池的手一番地胡言乱语,苏倾池挑出几句来听,倒也明白了事情的缘由经过,见商承德精神恹恹,便扶了他枕在自己身上,由他抱着自己的手睡下。
苏倾池原先在扬州落脚之时,倒也听闻过程家兄弟俩的事,程家长子程砚秋在诗书画之上颇有造诣,因看不惯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阴谋算计,每日只管关在房内舞文弄墨,独占一方逍遥自在,为此,程老爷颇为头疼。
程家二子程砚卿生得灵秀异常,性子讨喜,原先最得程老爷疼爱,程家上下视为珍宝,然在程砚卿十二岁那年,忽而传出程家二子得了失心疯的消息,不知是真是假,但程老爷却不再亲近这个儿子。
又有传言说程砚卿身上流的不是程老爷的血,种种流言,不辨真伪。
吩咐陆青提一壶水来,苏倾池将商承德扶入房中。
人已睡了,手上却攥着他的衣裳,苏倾池几番哄说,那人倒耍了无赖,一把抱住他的腰,两人就势倒在了床榻之上。
陆青进来一愣,放下水壶便要替二人关门。
“你出去做什么,还不快扶了你家少爷起来。”苏倾池又急又气。
“啊?”陆青一时呆愣,瞧见苏倾池责怪的眼神,立马上前,同苏倾池一道将商承德扶起来。
两人几番折腾,终于让床上那醉汉安睡了。
至此,外头早入夜了,苏倾池觉得身上粘腻,便欲回房洗个澡歇息。
“苏老板,我替你打些热水来。”
“也好。”
满室水气缭绕,如烟似雾,苏倾池仰靠在木桶中,泡了一会澡。
外头如今冰天雪地,屋内却无一丝凉意,苏倾池畏寒,商承德早些时候便在他屋里支了两个暖炉,每日炉火旺盛,不叫他感到一点凉意,如今又满室热气,倒让苏倾池有些燥热。
匆匆洗了身,取了干净亵衣穿上,这时听得外头有人拍门。
苏倾池只当是陆青,便披了外衣去开门,谁想,门一开,一个人就压了下来。
定了心神,苏倾池瞧见来人,不由道,“你怎么醒了?先进来吧。”
商承德压在苏倾池身上,胡乱地唤着他的名字,这模样哪里是清醒了,根本就是还在醉梦中。
原想喊了陆青来伺候,又想想,如今这个时辰陆青怕是早睡了,也是了,若是陆青还醒着,如何放着他家少爷一个人跑来他门前胡闹。
醉酒后的商承德与婴孩无异,虽老实,却也无赖。
“倾池……倾池……”
苏倾池无奈,扯了被子将人盖好,“睡吧,你如今可折腾够了?”
商承德还喃喃地唤着,循着暖香,将头枕在苏倾池大腿上,许是舒服了,鼻子还不时地蹭两下,弄得苏倾池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只得任他抱着,在床头坐了一夜。
夜色沉静,月色如水般倾泻而来。
苏倾池靠坐在床头,有一下没一下地抚着商承德的头发,低头看一眼枕在自己腿上睡得安详的男人,苏倾池嘴边溢出一丝满足的笑容。
苏宝儿原先问过他,为何独独待商承德不同。
他当时没有回答,不是他不清楚,只是他说了,旁人也无法明白。
苏倾池不否认,当初他确实存了一分引惑商承德的念头,不为别的,只为让自己在那人眼中多停留片刻。
苏倾池从不信缘,然而当他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商承德,他便不由地怀疑,他算不算是上天对他的一种补偿,抑或是上天给他的一次赎罪机会。
补偿什么,又赎的什么罪,从来没人知道,便是他自己也说不清。
但是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