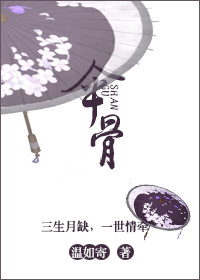伞骨 温如寄-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钟檐想,果然是一家子,都那么爱演。胡老板闹腾了一场,出牢门的步伐却没有慢半步,一溜烟儿就没影了。
安静下来,大把大把的时间空着,钟檐也想通了许多的事。从扣下那批货,到抓捕胡老板,再到赵世桓的死,恐怕都是彻头彻尾的圈套罢了。
而他,胡老板,秦了了,甚至赵世桓,都是这局棋中的棋子。
——不!这局棋,恐怕从申屠衍找到了他,就开始了。
他忽然想起了申屠衍,衣襟上已经布满了汗滴,冷而稠密的感觉紧紧抓住他的背。
***************
兖州缺水,到了冬天一瓢水便更是稀罕,兖州城十里外便有这样一处地,荒地黄沙,只有突兀的一口口枯井。
水面干涸,一口枯井便是这大地的一个疮疤。
在钟檐在牢中蹲着的时候,申屠衍正盯着一口又一口的枯井,看了约莫有半个时辰。
——他为什么在此处?
他是尾随了官府的衙役而来的,他为什么会尾随衙役呢?还要从昨晚说起,那晚上,他思前想后,将这件事情也重新想了一遍,觉得整件事情实在蹊跷,赵世桓在席上问钟檐这样一句话,那么他肯定也应该认出了钟檐,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是在席间才看出钟檐的身份,说明他事先是不知情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引钟檐来云宣呢?
他想了许久,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年头,或许不是钟檐,任何人都可以……或许,事情的源头……是那一堆忽然冒出来的兵器?
他这样想着,便连夜潜入了看守兵器的库房,说巧不巧,正好遇上了这监守自盗的衙役了。
申屠衍想,这群衙役不穿官府,黑衣蒙面的装束,定然是要做不好的事情去了。于是他一路跟踪,看见那些黑衣人青骑出城停在这里,纷纷将兵刃扔入了一口又一口的枯井。
天已经大亮了起来,他低头朝枯井望去,深不见底,黑漆漆的一片。申屠衍不能肯定,这口井到底有多深,没有把握自己下了井,有没有活命上来的机会。
烈日当空,他却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忽然,他看到了土堆枯井之间有几个人影闪过,他怀疑是那群人去而复返,加快了脚步,追了上去。
一直到了进城的城门中,那些人影却失去了踪影。
*************************
而此时,钟檐正坐在牢底闭目养身。
他虽然闭着眼,却没有睡着,闭了眼,种种声音都朝耳边而来,谩骂的,啜泣的,咬耳朵嘀咕的,地面上蚊虫爬行的,都没有转弯没有分别的入了耳。
“咱们老爷可真是……大半辈子的官儿,什么酒色财气没见过,偏偏被一个小姑娘迷得没了命,啧啧啧……色字头上一把刀呀。”
“可不是,听说小姐和姑爷正从京城里往这边赶。你看……那个人……多半是死人了。”
“可不是……姑爷是萧相跟前的红人,指定不会放过他……不过那妹子可真是个美人啊,水捏的冰砌的,等她阿哥一死,不是红姑娘的命啊,就是当外室的。”
钟檐听着他们议论,他忽然想起来,就在他被赵家拒绝的几日后,赵小姐终于桃杏有期,敲锣打鼓风光满面的出嫁,嫁的正是林翰林家的公子。
仔细想来,他竟然想不起那赵小姐究竟长得什么样了……原来一切都是命啊,命运正是个爱赶趟儿的主儿,要么什么也没有发生,要么全部赶到了一块儿。
那一年儿,莫约钟檐出的最大的一场丑,便还是与赵小姐的婚事。
永熙十年的初春,有燕剪新柳,有杳杳细雨。
当然,还有院中隐蔽处一日紧过一日夜猫的叫春声。
钟檐将自己裹在被窝里头,觉得猫这种恼人的生物跟自己脑海里叫嚷着“我稀罕”,“我稀罕”的雀儿着实可恨地相似,被烦躁得不行,起了身,抓起桌子上砚台就往院中的草丛中扔去。
一声沉闷的钝响,那草丛中的小东西似乎受了惊,几声窸窣声后又恢复了宁静。钟檐没好气的咒骂了几声以后,揽了被子继续睡。
朦朦胧胧中他恍惚听见隔着街飘飘渺渺的传来吹吹打大的声音,那声音,高亢繁杂,纷至沓来,好像流传佳话中龙凤呈祥锦瑟合鸣的喜庆之音,又好像是稗闻话本里男子得势另娶后下堂之妻的悲戚,可是,不管是哪一样故事,都与他无关。。
几番春眠不觉晓,转眼又是一日。
钟母看见自己的儿子已在被子里闷了好几日,唯恐好端端的一个少年就这样憋坏了,亲自熬了一碗莲子羹,叩开了门,坐在了钟檐的床边。
她摸摸儿子的额头,有些烫人,似乎是低烧,“大夫开的药可吃了?”她看着儿子面色被病气沾染,是不正常的潮红,心里想着他这场相思生得着实不轻,便暗自叹了口气,“孩子呐,你听我说,都说这姻缘天定,其实有七分还是要靠人事的……赵家那样的门第,看不上我们家,也是常事。”
钟檐被自家母亲说得有些懵,只听得母亲继续说了一句,“我知道遇上一个可心的人不易,可强扭的姻缘也不是善缘,你伤心过了也便好了……”
“娘,我不伤心。”钟檐诚恳道。
钟母见少年这样说,也不拆穿,想着孩子面皮薄,便顺着孩子的话往下说,想着能宽慰他几分也是好的,“这件事情,你和你父亲虽然没有怪我,但是我这几天想想,也是做娘的错了,我原本想着这桩婚事能够帮衬着你父亲的仕途,对于你,也算得上一桩锦绣良缘,两全其美。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感情扯上了政治,又怎么会干净得起来,我甚至从来没有问过你,这桩婚,你欢不欢喜?”
少年靠在床沿上,露出被子的脊背有些发凉,被母亲紧紧握着的手却是温热得伸出了细小的汗液,他看着自己端持的母亲说出了那样的一番话来,“我的儿,娘前些时候也许是错了,我的儿媳妇,门第,容貌都不重要,只要那个人,能够心甘情愿的一辈子陪着你,娘便许了。”
少年一怔,回答了一声好。
到底是少年人,一场风寒,捂几日,几副药下去,便好得七七八八了。钟檐虽然仍然有些烧,请假已经有些时候了,再不回去,那些老学究们该有愠怒之意了,是时候重新回国子监了。可他一回去,便觉得众人看他的眼神有些异常,他想着自己在京城中闹出这样大的笑话,受些奚落也是应该了。
到了黄昏时分,才有人告知他,那赵家小姐与林乾一在前几日大婚。
钟檐一记闷雷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他的头顶上,两眼发昏,他也只能打落牙齿合血吞了。“无事。倒是不曾参加林兄的婚礼,真是失礼。”
他走出门时,觉得白花花一片,春日的太阳,忒毒。一转头,就上了须尽欢。
岂料借着情绪,多喝了几杯,却酿出另外一场祸事来。
、第四支伞骨·起(下)
还是少年时期的钟檐性子远没有现在来得圆滑通透,凡是文人,读过几年书,总是要读书人的风骨与坚持的,和所有士族公子一样,即使没落,也不愿意和生活和解。
是以,这场婚事,原本不过是一桩风月,被牵扯出这么多利益来,他觉得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其实有那么一瞬间,他是真心想要把她当做自己未来的妻子的,很小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娶一位像母亲一样的娴静妻子……可是后来,因缘际会,无论是娴静还是妻子这些都通通没有实现。
他才知道,白发齐眉,谈何容易。
钟檐将一杯又一杯灼烈的液体灌入喉,真他妈的……酸涩。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钟情于这样一只酸涩的液体,酒气灌入脑壳,甩开一室红旎,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起来。
申屠衍走过少爷的房间的时候,在门外驻足了一会儿,钟檐房里的灯一夜都没有亮起来过,他不确定人是否在,他知道钟檐的脾气,扰了他睡觉少不得一顿口舌,却还是慢慢推开了门。
隔壁昏暗的光线照射进来,屋里空无一人,却是衣柜翻倒,凌乱不堪的样子。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蜡烛,却没有找到,索性借着漏进来的光收拾屋子。
那人摔进房门的时候,浑身已经湿透,水滴还顺着发丝衣襟不住的往下淌,申屠衍觉得奇怪,外面明明没有雨,怎么湿成了这副模样,问了才在钟檐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的言语中了解,他在过桥的时候,落了水。
钟檐说完了这些经历之后,自顾自的笑了,仿佛连自己也觉得好笑滑稽,他因为醉酒,身体没有支撑,整个人附在申屠衍的身上,原本又湿又冷的身体已经贴在申屠衍身上,仿佛瞬间变成了足以灼伤他身体的巨大热源。
他无奈,低头喊了一声少爷,钟檐迷迷瞪瞪应了一声,立即闭了眼没了声。他用手抚了抚他的额头,火烧似的温度,像是落了水着了凉,又起了高烧,这温度,甚至比之前还要高。
申屠衍终于在暗处的角落里寻到了快燃尽的煤油灯,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寻了钟檐的里衣,剥开他湿哒哒的衣服,少年不老实,又哭又笑,一会儿喊着娘,一会儿喊着须尽欢里的霜儿姑娘,一会儿又说申屠牲畜,你娘给你取这个名字可真有趣。
申屠衍黑脸,少年还没有完全发育白花花的身体在眼前乱晃,他喉头一紧,背过脸去不看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个和自己一般的少年存在着男女之间的欲念,以前在奴隶场里的时候,他也见过那些蛮狠的胡狄人将汉人十五六岁的少年扛进大帐里,然后大帐里传来那些暧昧的喘息声和少年歇斯底里的叫声。
可是这种情况显然是与他不同的,他单单恋着这个少年而已,这个给了他命运的少年而已。
好不容易擦干了钟檐的身体,把人塞进被窝里,申屠衍已经是呼吸粗重,可是钟檐并不打算放过他,他抓着他的手说,“我冷,你上床来。”
他和钟檐躺同一个被子也是常事,冬日寒冷的夜里,两个少年互相依偎着互相取暖,也是在同一张床上,钟檐说瓦片呀,我以后要当游侠白衣瘦马快意江湖,到时候你还替我牵马吗?申屠衍说好;稍长些,钟檐说瓦片瓦片,我终于要听父亲的话去考科举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有骨气?申屠衍说没有,这样我也陪着你;再后来,钟檐说瓦片你知道吗我要娶媳妇了,是赵家的小姐,这一次申屠衍却再也说不下去,他再也不能说陪着他这样的话……
很多个夜里,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不一样的心情,说着不一样的故事。等到申屠衍渐渐意识到自己那违背伦理的情感,他尽量避免和他躺同一个被窝子,现在,少年怕是真伤心了,不想弗了他的意,答了一声好,脱了靴,与他并排躺下。
静谧的时光,狭小的空间,与无数个日日夜夜无异。
半夜里,钟檐忽然咯咯的笑了起来,他问他笑什么?钟檐原本的酒有些醒了,却依旧不清明,半夜里少年喊了很多人的名字,申屠衍一直没有睡,所以听得明明白白。
钟檐想起了以前老人们说过的俚语,他们都说狗与主人上一辈子一定是欠债的和债主的关系,前世欠了债,这一辈子就拿着肉骨头,却怎么也不给他,事必要狗守个不离不弃。
他说,瓦片呀,你会不会,就是那条狗呢?
——不然,为什么,艰难困苦,狼狈落魄,我的身边就只有你呢?
申屠衍听不懂,少年却伸手挠他的眉毛,鼻子,嘴巴,笑着喊着狗眉毛,狗鼻子,狗嘴巴……还有狗尾巴,钟檐神智不分明,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正常的人,两股之间哪里会有什么尾巴,那硬邦邦灼热的物什分明是……
忽然,温热的嘴唇迫不及待的压下来,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