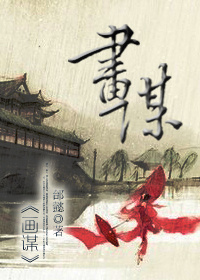丞相谋-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是些简单小菜,却让我狠狠馋了一馋,不由食指大动,吃了几口又凑过去道:“什么地方?”
白棠不语,青白的光线站在他的侧脸,眉如修竹,鼻梁挺直,清润英邪,却听他道:“自然是找得到媳妇儿的地方。”
这回话颇有水准,我顿了顿,又道:“团子与你都来这曰国一两月了,你就不怕有人趁机篡位谋权?”
唔,篡的是临子梨的位,谋的却是他的权。
他看我半晌,须臾,道:“嗯,等我找到媳妇儿也不迟。”
我讪讪笑笑,埋头捻菜,又到了杯桌上的酒,入口甘冽清醇。据我这活了十几载的听闻来看,这斐国乃泱泱大国,风景大好,却是连曰国也比不上,自那安卿帝继了尚贤帝的位后,表面风平浪静,四海升平,朝堂之上却颇不宁静。
说起这尚贤帝,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十六驻军,十八归位,二十及冠,稍稍篡了个位便身居高位,不仅如此,据说这江湖之远也与他脱不了干系,但被许多人广为流传的却是他与姬媳皇后之间的伉俪情深。
自立她后之后,尚贤帝便再未纳妃,直至姬媳皇后与年仅七岁的皇子双双葬身火海,过了七载,百官上书请纳宫妃,这才有了临子梨,如今的安卿帝。
临子梨继位之时,乱党谋权,当时的镇国大将军宋祈意欲夺权,却未料到白棠这厮已占了先,失败之余亦是被白棠这披着丞相外衣的衣冠禽兽打压得不成样子,都说白衣卿相,权当摄政,在我看来,却是他一肚子算计人的坏水给闹腾的。
我恍了恍神,便听白棠问道:“公主可有想去的地方?”
我点头,道:“隽州。听说斐国一都九州,隽州景致富如江南,烟雨如丝,胜过碧瑶仙境。我活了这么久,倒真没见过那般情景,倒真想去见识一番。”
“听说姬皇后便是隽州人。”我顿顿,望了望空空入也的菜碟,白棠招来老叟,又要了些吃食与我,我继续道:“可我现在,却想去余镇看看。”
他淡淡挑眉,我望他一眼,道:“杜白笉说我六岁以前都在那儿过,我估摸着,我现下却是半点渣子都想不起来,若是去看看,也是好的。”
语毕,我又拿酒饮了几口,才发觉我这心里忒藏不住事,下意识抬眼看他,好在他兀自拿了杯子饮了口酒,倒是没有在意。
彼时,春日清晖,白棠侧眼看我,眉形修长,眸如润玉,与我道:“嗯。改日带你去看看。”
恍然间,我仿佛记起梦中景象,有桃枝满山,有潺潺流水,有人与我道,我媳妇儿,谁也不能抢。转眼间,眼前一黑,竟直直向桌上扑去,只觉一双手稳稳扶住我,有人敲敲我眉心,低声唤我,我兀自皱眉不理,而后便是一片沉静。
我醒来时,头疼欲裂,晏儿过来扶住我,道:“公主醒了。”说完递了杯浓茶与我。
我揉了揉眼角,道:“回了?”
晏儿点头,笑道:“夫人也回了,正和白相在外堂里。”
我愣了愣,旋即踢着鞋子起了身,道:“我去看看。”
娘坐在桌旁,听见声响,抬头淡淡看我一眼,欲言又止,一副风中凌乱的模样,我呆了呆,又望向摇着扇子的白棠。
白棠看我一眼,笑道:“醒了?”
我伸了个懒腰,兀自找了个位子坐下,道:“嗯,谢……谢谢。”
他愣愣,旋即笑得开怀,娘面色有些不自在,不料白棠那厮笑盈盈道:“公主既是无事,在下便先告辞。”说完转身出了门。
我颇为奇怪的忘了娘一眼,心觉这般安静委实有些奇怪,不料娘朝我看一眼,撇了撇嘴,拿起手边一幅画,画卷展开,真真是……何处不相逢啊……
想起那幅画先经易昭之手到了我这,又被白棠那厮拿去,现下又转而到了娘这,颇有……缘分啊……
我低眼瞅了瞅,却听娘开了口。
我顿觉世事真它令堂的无常……
那副画上的人,我先前眼间这熟悉,现下便有了万分的肯定,便是我娘没错,只不过这执笔之人却是那斐国的尚贤帝,便又觉着浑浑噩噩。
我惊异,道:“莫不是娘以前与尚贤帝有过交结?”
娘点头。
我心肝儿扑腾了两下,又死而复生,凑过身子颤颤巍巍道:“莫不是我是他的亲子?”
娘瞪我一眼,我咳了咳,道:“随意说说,随意说说,嘿嘿。”
想来我再名不见经传也是这曰国公主,和那斐国尚贤帝八竿子达不到一块,况,这画上人物和娘这些年来与我相与的气质太过出入,若不是那日在东门之外见着了娘身着布衣的样子,我就算把脑袋渣子都搅了出来,也不会大胆想到这画上便是她本人。
娘突然笑笑,望着我笑眯眯道:“你不是他亲子,却是他儿媳妇儿。”
我生生打了个冷颤,抖着眼角看她,娘望了我一眼,再开口,却让我把曾十几载未经过的霹雳把我自个儿给弄了个里焦外嫩。
我既不是尚贤帝的亲子,却也不是吾皇的亲子。
我爹名叫苏涣之,前斐国的国师大人,身居高位,自是羡煞了许多人,却为了一人不惜辞去官衔,摒弃荣华,独处江湖之远。
那人便是我娘。
当年爹辞官后与我娘找了处边境小镇住下,到过了些安生日子,哪想正逢斐曰两国小战不断,宋祈起兵作乱,阴差阳错之下,却是发现我爹的踪迹。
当朝国师,声名赫赫,即使江湖之远,却依旧让人颇为忌惮。
我爹被人所害,只留我娘带着年岁尚小的我,彼时,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与往日四海升平之景大相庭径。
我娘就是在那时被一人所救,那人不才,正是当初御驾亲征的吾皇,而今我认了十八年的爹,却没想是认错了人。
我呆了呆,半响没有回神,待我能恢复五感,已是一盏茶的时刻。
我心下奇怪为何吾皇会生生收留一个带着孩子的妇人,却蓦地想起一件事,道:“莫不是我六岁以前,进过斐国皇宫?”
娘点头,不可否置。
我继续问道:“莫不是还小住过一段时日?”
娘看我一眼,神色莫测,继而点头。
我抖了一抖,又继续缩着脖子道:“莫不是……还踹过什么人进了池子?”
那段记忆委实有些不美好,我只晓得以我九哥的性子来看,若是被我踹了一脚大约会闹腾的鸡飞狗跳,想来,我估摸着,也许,那次踹人之时,我踹的不是曰国人,而是在千里之外,斐国帝都里的人。
我想是这些天来经历的事情太过跌宕起伏,与我这平日里与世无争的淡泊心境颇为不像,脑子里一团混沌,翌日一早,我估摸着快要下了早朝,便想拉着杜白笉那厮一同喝上几杯,也算慰藉慰藉我被打击的不堪一击的心肝儿。
石阶白玉,我找了个地方,等了半晌,有官员陆陆续续从重华殿里出来,又待了半盏茶的时刻,便见杜白笉一身玄色官服从里出来,身边也围着两三个官员,我上前与他摆了摆手,那厮很是默契的过来,我却见又有一人从重华殿里出来,啧啧,那周围却是被那些个官员围个水泄不通,远远看去,只余一个束发的金色鹿冠,我心下讪讪,倒是没料到他一个斐国卿相此番来了曰国,与我曰国官员感情甚笃,我替吾皇甚感欣慰,深感欣慰啊……
杜白笉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面上却颇有些感慨之色。我以为,身为与他算得上半个青梅竹马,。便很是关心的凑过去问道:“怎的了,可有郁结?”
杜白笉叹了声,道了几句白相年少有为,将将及冠之龄已身居要职云云。
得,我撇他一眼,深觉杜白笉此生估计与那精忠报国的念想还有很大差距,看来此生也就那们点门路,对他所说的十分不屑。嗯,其实曰国易卿,也是不错的……
我正兀自晃神,却听杜白笉那厮却沉了沉声,道:“我爹说白棠此人来曰过不过一月之余,却将朝中上下关系脉络打理了却得差不多,其中世故圆滑,城府颇深,若此人有心拉拢,培养势力,便是回天乏力。”
此刻清风袅袅,杜白笉独自说得浑然忘我,我却对这朝中复杂脉络,其间为官之道闹得我深恶痛绝,昏昏欲睡,直到杜白笉陡然止了话头,扯了扯我的衣袖,与我道:“十三,我这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不那么坏的消息,你先听哪个?”才让我消却了点睡意,抬头望天。
第十八章
我想了想,道:“我都不愿听。”
杜白笉阴测测看我一眼,冷笑出声:“莫要后悔。”
我不语,却见白棠那厮笑得春风得意,走过来道:“公主可是来找易御史?”
我愣愣,摇头道:“不是。”
白棠笑笑,晨露沾衣,衣袖上绣着的云纹无不章显着幸灾乐祸:“嗯。易御史都告假三日,现下想必正呆在福府里养病,想必公主也见不找他。”
我惊异道:“易昭病了?”
杜白笉面上一副波澜不惊,道:“我方才想与你说这事,你不听。”说完,很是奇异的往我一眼,掩不住得意之色。
我想了想,对他道:“唔。说好了去你家喝酒,时候不早,走罢。”
杜白笉望望天,道:“辰时三刻。”
我随他的动作望了望这青天白日,讪讪道:“我去换身衣裳。”
吾皇品味很是独特,恨不得每到一处都能见这些常年不败的树木,却让我着实吃不消,等我晕晕乎乎的到了南门,日头已高高挂在半空中。
我望着对面二人讪讪笑笑,又望望不远处南门把守着的侍卫,道:“走罢。”
这一番出宫委实顺利,我在离宫门是十尺之外的地方站住了步子,对白棠点头道:“白相忧国忧民日理万机,我出宫之事还请白相莫要向他人提起,嗯,本宫自会感激不尽。”
白棠缓缓出声,点头又上前走了几步,道:“好说好说。”
我心喜,道:“到时若是用的上我的地方,只管说。”遂又觉着这一句话恐不能让他安心,又抬手拍了拍他的肩。
他微微侧脸,目光落在肩上,挑了挑眉,又与我和杜白笉一同走了半刻,却是到了将军府。
我停下步子,白棠转身道:“公主不进去?”
我指了指匾牌,又看向他,他恍然大悟道:“忘了与公主说,杜将军前几日送了帖子来,我今日前来赴约。”
我疑惑不信,却见他从袖中拿出一个镶金的小帖子,望向杜白笉,后者一脸疑惑,却见白棠道:“上次少将军与我说想以身报国,我倒是想了个法子,可以一试。”
或一说完,便见杜白笉那丫两眼放光,一副狼崽子的模样,道:“是么,请请。”又甚为快意的把他往府中领,对此,我甚为不屑。
罢了,大不了晚些时刻再去看易昭便是。
半柱香的功夫,杜越与白棠《文》相谈甚欢,一口一《人》句贤侄,沾亲《书》带故,杜白笉那《屋》厮却是插不上话,颇为郁结,却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我在一旁耷拉着眼皮数着香漏上多出的时刻,最后以一句“贤侄留下吃饭罢”,顿时精神抖擞。
我起身告辞,杜越摆摆手,招呼身旁小厮送我出府,我受宠若惊。
杜白笉叫住我,疑惑道:“不喝酒了?”
我连连摆手,道:“改天改天。”
白棠那厮却是起身告辞,又转头与我道:“正好,我与公主顺路。”
杜越愣愣,转而笑道:“今日与贤侄相谈甚欢,老夫很是欢喜。”却是不再挽留。
我梗着脖子与白棠出了府,皇宫在左,易府却在右。
我这厢正绞尽脑汁琢磨这找个法子支开那厮,又想到小金子日